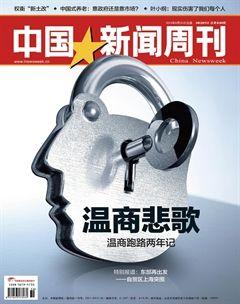溫州信用模式危局
龐清輝
“很是氣憤,我的信用卡信用額度從50萬下調到30萬,又下調到20萬了。” 2013年9月初,武思南,溫州市龍灣區一家男裝企業的負責人,見到《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時抱怨道。武思南明白,溫州跑路風潮以來,銀行擔心溫州的商人透支信用卡太多,最后還不上。
3個月前,2013年6月初,溫州市甌海區人民政府發文,要求全區范圍內租用他人用房、場地的企業繳納職工工資保證金,數額為5萬~150萬元不等。此文件一發布,武思南的朋友就和他抱怨:“這是政府防止企業跑路的政策。”
自2011年爆發的跑路潮以來,溫州的上空一直彌漫著不信任的空氣。“政府不信老百姓,老百姓不信政府,銀行不信企業,企業不信銀行。企業說銀行是騙子,銀行說企業是小偷。以前企業互保,彼此拍下腦袋就決定了,現在企業會擔心自己被拖垮,連親兄弟企業都不敢互保了。”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
而不久前,周德文遠赴美國,去聽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的演講,這兩個人都提到了溫州的跑路風波。“壞事傳千里,一旦對溫州不誠信傳聞過于妖魔化,對溫州信用的重建影響就很大。”
像以往發生在溫州的那些風波一樣,每一次都是以重新樹立起溫州信用結束,這次也不例外。“不怕財產損失,最怕信用體系失去。”中國民主建國會溫州市委員會常委金利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民建里商人居多,金利泰這兩年聽了太多商人跑路、經營不善的故事。每言及此,大家最擔心的是整個溫州信用體系的崩壞和商人創業精神的削弱。
建立信用城市也正成為溫州市委和市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這次危機對溫州企業的誠信,是一個重創。政府和企業家都認識到,溫州要建立包括政府、企業、個人多方面的全社會的信用體制。”溫州市市長陳金彪在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說,溫州已經建立信用建設領導小組,目前整個中國從農村社會向城鎮化社會轉變,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溫州必須在陌生人社會中謀求現代誠信的建立。
信用如山倒
在溫州借錢一直很容易,口頭協議,不用字據,信用基石是其根本。
高度的信用空間曾造就了溫州一個特有的現象,就是溫州人做事喜歡抱團。改革開放初期,溫州人涌向全國創業,只有老鄉靠得住。在全國各地,溫州企業經常組成“生意圈聯保”“老鄉聯保”和“同行聯保”,互相擔保向銀行申請貸款,共同獲利共擔風險。彼此都是溫州人,雖素不相識亦可成事。
這是溫州的傳統。即便溫州人在海外,手頭一時拮據,想向一個并不相識的溫州人借錢周轉,只要兩人共同認識一位溫商,“中間人”甚至不用出面,借貸雙方聊上幾句,一切就OK。
“溫州的文化是熟人文化。要是不擔保,就連兄弟老婆出門都會被人罵。”溫州開元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躍勝說。2009年,武思南讓一個在杭州的溫州朋友,幫他在杭州買總計1200萬的幾套房子,戶型由朋友看著定。一個電話,朋友就幫他支付了1200萬,朋友說不要利息,但武思南在還錢的時候,還是給他多打了100萬。
到2011年,形勢突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基石開始瓦解。2011年底,武思南身邊兩個人跑路,他損失近千萬。其中有一位是他的表親,在臨跑路前的頭一個晚上又和他借了200萬。此前,武思南已經將300萬放在她手用來放貸收利息。第二天,表親一家人神秘消失。
而武思南公司急需周轉資金500萬,再打電話給朋友時,朋友讓都他自己想辦法。而這兩年經常主動上門詢問要不要貸款、不需要擔保的擔保公司,開始要嚴格抵押,而且要付高息。并且,每隔幾天就來催款。
從2010年開始,武思南公司經營越來越難,勞動力成本至少上漲了30%,原材料平均上漲20%。但和2008年金融風暴時不一樣。2008年利潤雖少但“可以活”,而現在是“有訂單卻沒辦法做”。
主要原因是很多企業對溫州人不再信任。企業訂單并不少,但購買原材料時,對方要求只要是溫州企業必須付現金,這使武思南不敢輕易接單,他要在這個緊要關頭保護好自己的現金流。他另一個做電子產品銷售的朋友同樣碰到這樣的問題。以前外地供貨商對溫州企業很信任,可以貨到再付款,或者推遲一段時間結算都沒問題,但現在,很多供貨商的要求是款到再發貨,而且要全款。
供貨商板起面孔亦屬不得已。2011年,溫州眼鏡巨頭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跑路,對上游供應商大量欠款。而在他跑路背后,其貸款互保模式,關聯企業和互保企業起碼有上百家,也都將面臨無力償還債務的危機。記者采訪時,距離胡福林跑路已經有兩年時間,2013年初另一家溫州大型眼鏡企業董事長離世,亦與和信泰聯保有關。
“即使朋友、兄弟之間都開始懷疑,‘你到底行不行啊。”溫州市擔保行業協會會長郭炳鈔說。《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蒼南龍港的親兄弟企業出現困難已不再互保。
最不喜歡存錢的溫州人開始到銀行存錢,不再投資,不再借貸。據溫州市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當地存款總額已經超過“房地產投資”和“民間借貸”,用于存款排在第一位。截至2013年6月,溫州市銀行業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達8282億元,比年初增加了536億元,同比多增加270億元。銀行存款節節上升,創下溫州歷史紀錄。
2013年3月底,溫州金融改革一周年,最大的亮點就是成立了民間借貸服務登記中心等融資平臺,“但是8000億的民間資本市場只有5個億的成交額。”周德文說,這其中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溫州民間借貸的信用體系瓦解,沒人敢再往外借錢了。
當問到武思南以后還會不會借錢給別人時,他停頓了一下:“要看借錢做什么,如果是治病,就可以借;做別的,那肯定是不會了。”
病去如抽絲
互信不再,企業家的自信也受到了嚴重的打擊。武思南覺得,跳樓了,跑路了,說明溫商精神沒那么堅強了。周德文也認為這是溫州商人的自信心被削弱的表現。
但是,也有溫商在砸巨資想維護這已經命懸一線的信任紐帶。黃作興是江南控股集團董事長,他的侄子,溫州最大的皮革老板、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長黃鶴,2011年4月丟下經營近10年的企業跑路,引起過不少恐慌,被溫州人叫做“黃鶴一去不復返”。
江南皮革是江南控股集團的子公司,黃鶴一直下落不明。“天要下雨,娘要改嫁,他不爭氣就隨他去了。”黃作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給他擔保的1個億,1分錢不少還掉了,將2600萬利息也還掉了。1000多工人、400多萬的工資和失業金都付掉了。”黃作興說,他知道這些錢,“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2013年4月,溫州泰順的兩個老人,兩個兒子都是企業家,都離世了。當兩位老人知道兒子還有80多萬欠債時,振作精神,撿垃圾也要賺錢還債,“這才是溫州精神。”武思南說。
以前黃作興這代溫商有很強的自信心:別人做不起來的事,我能做得起來。溫州模式并沒有什么神秘、深奧的地方,最為關鍵的就是讓企業家精神、市場力量得到發揮。在溫州人均識字率,交通條件,基礎設施,經濟資源,溫州底子之薄,幾同乞丐。但是老一代溫州人有“三板精神”“四千精神”:就是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還有看黑板,走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吃了千辛萬苦,說了千言萬語,也要達到目標。
只是,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不少像黃作興一樣歲數較大的商人,或多或少賣了部分工廠。黃作興承認,“做事越來越難,休息了,沒有斗志了。” 黃作興經常會比較:很多企業原來做500萬的利潤日子很好過,天天快快樂樂,全家無慮無憂,無牽無掛,沒有任何債務的外部壓力;現在利潤做到一個億了,反而是債務累累,面對銀行的追債、社會的追債,過年都沒辦法安寧。“都是過眼煙云,一下子就會沒了。”
如今,信用體系遭受重創,本就看中血緣地緣關系的溫州人,更加重視家族的力量。一個平陽的商人這樣論述家族之于他的重要:他的企業管理職位只用親人,只會在本家族或者妻子的家族中挑選。用外人會跳槽,帶走商業機密和技術機密,還有訂單。如果親人這樣做,他會面對整個家族的拋棄。做生意難免會要融資,家族成員的借款比錢莊要利息小得多,展期也容易。“就是我徹底敗了,我有經營經驗,也會被親戚的企業雇傭。”
記者在采訪中遇到這次危機中倒下的商人,幾乎無一例外尋求自己在國外和國內親戚的幫助,幫忙銷售親戚企業的產品,還有暫時為親屬當司機,每個月賺幾千塊錢。
在重建溫州商人輝煌的今天,溫商過于倚重家族和熟人之間的誠信,曾經為他們帶來輝煌,如今似乎正在成為他們的阻礙,也讓溫商持續在低谷徘徊。危機過后,溫州企業越來越保持保持封閉式家族企業的形態,既不讓外人進入,也不想與其他企業聯合和合并,更不愿被其他企業收購和兼并,以致溫州平均企業規模依然很小,少有股份有限公司。
“傳統的‘溫州模式已經變成現實的包袱,這十年來,溫州的區域經濟發展沒有很好地從初級市場經濟到現代市場經濟轉型。”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史晉川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早在2004年,他就斷言“溫州模式”將在25至30年后消失。
目前,溫州信用體系正在告別“熟人社會”,建立“規則溫州”。不過,如果事事都循規蹈矩,溫州還會是原來那個活力四射的溫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