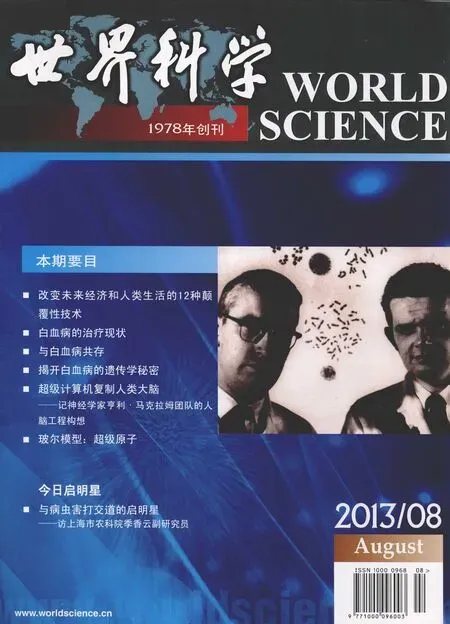揭開白血病的遺傳學秘密
陳軼翔/編譯

彼得·諾維爾 (左)和大衛·亨格福德發現了費城染色體(ph染色體)
●能夠快速進行DNA(脫氧核糖核酸)測序的技術深刻地揭示了,無論是白血病患者自身,還是各個白血病患者之間,都存在著遺傳基因的多樣性。
1959年,美國費城追狐癌癥治療中心的大衛·亨格福德(David Hungerford)和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的彼得·諾維爾(Peter Nowell),在顯微鏡下觀察取自兩位慢性粒細胞白血病(CML)患者的血細胞,發現其存在著驚人的異常狀況:這些血細胞中的22號染色體有很大一部分缺失。
這是人們首次關注白血病與遺傳基因的關系,實際上這是第一個被發現的與癌癥相關的遺傳基因異常。現證實,95%的慢性粒細胞白血病(CML)患者的血細胞中均存在粗短的費城染色體(因首先在美國費城發現而得名)。
當部分9號染色體和22號染色體發生易位時,就形成了費城染色體。該易位使得BCR和ABL兩種基因匯聚融合,形成一個異常的實體,被稱為一個融合基因,使細胞變為惡性的。
盡管這種融合基因很早就已被識別,然而單基因變化如何就會導致白血病,人們對這一問題的了解進度緩慢。“很久以前,我們就已經了解這些染色體的變化,但除此之外,我們知之甚少。”倫敦癌癥研究所從事兒童白血病研究的梅爾·格里夫斯(Mel Greaves)說。
但在過去10年左右的時間里,上述狀況開始有所改觀,快速DNA測序技術,向我們傳達了大量的關于各種類白血病基因變異方面的信息。這些基因的鑒別,有助于研發新的治療白血病和其他癌癥的方法。
研究表明,慢性粒細胞白血病與單個基因變異之間的直接關系,是一種異常現象。大多數類型的白血病都是由一組基因變異而引起的,無論是白血病患者自身,還是各個白血病患者之間,基因變異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總的來說,有數百個基因,包括幾十個融合基因,牽涉到不同種類的白血病。但個體病例只是涉及到少數可能的基因變異。
這與實體瘤形成了鮮明對比,例如,乳腺癌或結腸癌,在個體病例中,通常會有幾十個基因變異。實體瘤病例也顯示出,基因組不穩定性是普遍存在的,有DNA的復制、缺失或是大量的互換,而這些在白血病的病例中則是罕見的。
每個腫瘤的基因變異數量相對較小,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某些類型的白血病很容易就能治愈。比如,大約95%的被診斷為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的患者,由于服用專門對抗BCR-ABL融合蛋白的藥物,5年后仍然活著。
基因的變異
根據引發白血病的血細胞前體的類型,白血病可以分為淋巴細胞白血病和粒細胞白血病兩種。根據發病的急緩,上述兩種白血病又有急性、慢性之分。每一類型的疾病,所牽涉到的基因列表都是不同的,但是彼此之間存在大量的重疊部分。

9號染色體(正中)的一部分與22號染色體的易位,產生了費城染色體
例如,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中的費城染色體所具有的特征,也同樣存在于5%的患有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即ALL,最為常見的兒童期癌癥)的兒童病例中。大約有25%的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患兒,都存在著不同的染色體易位,從而導致了ETV6和RUNX1兩種基因的融合。RUNX1的變異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例(AML)中也很常見,該病患者主要為老年人,發病速度很快。
為了找出導致疾病的基因變異,研究人員努力尋找那些經常出現的、或是存在于很多患者病例中的基因變異。蒂莫西·萊伊(Timothy Ley)是來自密蘇里州圣路易斯市華盛頓大學的一位癌癥遺傳學家,他所領導的研究團隊進行了一項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白血病基因測序研究,分析了取自于200例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的細胞。 萊伊和他的同事們對其中150例患者的細胞的外顯子組(即基因組的蛋白質編碼部分)進行了解碼測序,同時對其余50例患者的全部基因組進行完整測序。
他們發現了非常有價值的信息。在被研究的急性髓系白血病例中,99.5%的患者至少有一種基因類別(共9種)發生了變異,包括腫瘤抑制基因,神經信號基因和那些調節控制髓細胞發展的基因,而正是髓細胞的發展會導致癌癥的出現。萊伊透露說,“幾乎對于每一位病人,我們都已經能夠確定其發生變異的基因組,或是其變異的途徑。”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發現,3/4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其牽涉到表現遺傳學的基因都發生了變異,表現遺傳學是指在不改變基因序列的前提下對DNA進行化學修飾,影響DNA的作用功能。
位于紐約,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的腫瘤學家羅爾思·萊文(Ross Levine)認為,表現遺傳學的化學修飾作用在白血病治療中的重要性,已經成為擺脫測序研究的、最令人驚異的深刻見解之一。他說,“那些基因在3年或5年前,沒有人會特別關注的;但是現在它們會經常性地反復出現。”
白血病患者體內另一類常見的變異基因,涉及到各種類型血細胞的發育與分化。根據引發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血細胞前體類型的不同(B或T是兩種主要的淋巴細胞),出現變異的基因亦有所不同。B細胞路徑出現在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兒童病例中的比率為85%到90%,出現在成年人病例中的比率為75%。通常牽涉到基因的變異,例如PAX5或IKZF1,這兩種基因控制著B細胞的發育。另一方面,由T細胞的變異所引發的病例,一般牽涉到以神經信號為途徑的基因,被稱作是Notch,在T細胞發育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白血病的復發
在4種主要類型的白血病中,發生變異的基因構成最為分散的是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測序研究表明,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可能牽涉到大量的基因,每一種變異基因出現在病例中的比率都很小。例如,以Notch為途徑的基因變異,被稱作是NOTCH1,在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例中出現的比率為12%,POT1的基因變異出現的比率為3.5%(POT1的基因變異在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例中出現的比率為9%)。
POT1基因在端粒與DNA綁定,而端粒位于染色體的末端,作用是保護染色體不被損害。很久以來一直認為端粒和癌癥是有關聯的,但據《自然遺傳學》雜志于2013年3月的報道,此項發現是首個實例,展示了一種受到端粒保護的蛋白質,與癌癥是有牽涉的。
將白血病中可能出現變異的基因進行匯集羅列,這僅僅是了解其基因特征的開始。即使在一個腫瘤內部,都存在巨大的可變性,細胞亞群往往帶有不同的變異集合。
“每一位患者體內,都會發現癌癥的這種進化樹,”梅爾·格里夫斯說,“僅僅羅列出發生變異的基因是不夠的,因為它們處于進化樹的不同分支上,彼此隔離。”
能夠證明上述觀點的一個證據就是,研究發現,白血病在被治愈之后有可能復發,從基因遺傳角度來看,復發的白血病與被治愈前的白血病是不同的。格里夫斯和他的同事利用熒光探針分析5位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患者所出現的基因變異,來研究復發的白血病。當他們分析復發白血病病例時發現,最初樣本中的某些腫瘤變異已經被其他變異所替代。蒂莫西·萊伊的研究團隊利用完整基因組測序,對8位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的診斷和復發進行了白血病細胞的DNA對比,發現急性髓系白血病的復發也有上述類似情況出現。
變異基因的這種不穩定性對于白血病的治療意義重大。針對某一組變異基因的藥物可以消除部分白血病細胞,但隨后其他細胞亞群就會擴展并取代被消除的白血病細胞的位置。“我認為,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很多靶向治療最終會失敗。”蒂莫西·萊伊說。
格里夫斯認為,這個過程就好比是在修剪灌木:削去一個大的分支只會刺激其他分支的生長。“我們面臨的挑戰就是要除去全部有害的生長,并使它永遠不再復發,”他說,“所以我們需要從根基上去切除它。”
從臨床角度說,這就意味著,治療需要針對的并不是診斷時發現的大量繁殖的腫瘤細胞,而是要針對最初發生基因變異的細胞,因為那些變異將會出現在整個腫瘤中。而科學家們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確定這些最初的基因變異。
遺傳基因變異性也是基于這樣一個事實——就像任何一種癌癥一樣,白血病也包括兩個基因組:一個是宿主基因組,代表遺傳的基因組;另一個是腫瘤基因組,包含癌變過程中所出現的變異基因。而大多數關于白血病的基因研究,都是主要關注腫瘤基因組。
小兒白血病中的腫瘤基因組很早就已發生變異,甚至可能在出生之前。胎兒發育期間,淋巴細胞前體在肝臟內迅速擴張,其中之一可能會產生易位或是發生變異,使其開始變成惡性腫瘤。例如,與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相關的ETV6和RUNX1的易位,被發現存在于新生兒的血液中。
出生之后,血液干細胞的分裂速度要慢很多,平均大約一個月一次,因此一個細胞大概需要數十年的時間才能獲得必要的變異組合使其轉化為惡性。這就能夠解釋,為什么其他類型的白血病,例如急性髓系白血病,主要患病群體為老年人。“這種病確實有隨機性,且主要針對老年群體。”蒂莫西·萊伊說。
遺傳性風險
盡管基因變異對于引發白血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些研究人員還是比較傾向于關注遺傳性風險。“我們花費了大量時間研究腫瘤基因組中的變異,但對于宿主基因組我們還沒有足夠的關注。”美國田納西州孟菲斯市,圣裘德兒童研究醫院的一位藥劑學家楊軍說。
楊軍正在嘗試著恢復一種平衡。據發布于2013年3月的報道,楊軍的研究團隊進行了一項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關于遺傳性風險基因的研究,他們對2 450名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患兒童進行了基因組掃描,同時進行10 977項對照實驗。
他們所識別確定的4個風險基因中的3個——IKZF1、CEBPE和CDKN2A/2B,其對白血病和血細胞發育的影響是已知的。而他們確定的第4個基因ARID5B,在白血病腫瘤基因組研究中從未被識別確定,有初步證據顯示該基因可能牽涉到淋巴細胞的分化。
研究中所確定的,與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相關的基因變異是普遍存在的:20%以上的人是上述某些變異基因的攜帶者,其中大多數人并沒有患上白血病。然而,如果存在哪怕僅僅一個高風險的變異體,那么染上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風險就會增加一倍;如果攜帶6個或以上的變異體,就會使患病風險增加9倍。
還有另一種方法來研究宿主基因組的影響作用,即研究那些幾個家族成員患上同一類型白血病的情況。這種家族是比較罕見的:例如,家族性急性髓系白血病僅占該類白血病全部病例的1%。然而,美國西雅圖市華盛頓大學的遺傳學家馬歇爾·霍維茨(Marshall Horwitz)認為,若能解決家族性白血病的遺傳基因問題,就可以有力地證明一個既定基因在癌癥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霍維茨和同事曾研究過名為GATA2的基因變異與家族性急性髓系白血病之間的關系。另有其他研究人員已經確定家族性急性髓系白血病與RUNX1和CEBPA基因變異的關系。
GATA2、RUNX1和CEBPA這三種基因,總共占據了家族性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一半。其他類型家族性白血病的基因秘密也開始逐步被揭開:霍維茨透露自己與合作者現有尚未公開發布的數據,可以確定首個牽涉到家族性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基因。
多種變異
然而要想了解白血病的遺傳基因,單單確定可能發生哪些個體變異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了解,多種變異是如何共同作用而引發癌癥的。這一過程可以在小鼠實驗中得到一步步的探究。
英國辛克斯頓,維康信托基金會桑格研究所血液學和癌癥遺傳學家喬治·瓦西里歐(George Vassiliou)和同事們通過實驗使小鼠的NPM1基因產生缺陷,該基因在35%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中均發生了變異。上述NPM1基因產生缺陷的實驗小鼠有1/3后來都患上了急性髓系白血病。但當瓦西里歐的研究團隊使小鼠的血細胞前體誘發了額外的基因變異時,“你會發現這大大加快了小鼠患上白血病的進程。”瓦西里歐透露說。
如果使變異小鼠與攜帶FLT3基因復制的小鼠進行雜交繁殖,也會出現同樣的情況。這兩種基因的改變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例中是最為常見的。“兩種孤立存在的基因變異能產生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不會引起突然的大變化,”瓦西里歐說,“但如果你設法將這兩者放在一起,作用就截然不同了,小鼠會很快就患上白血病。”
研究人員觀察到,人類白血病例中有著同時存在的基因變異的模式。例如,基因ETV6與RUNX1的易位,基因PAX5的缺失,兩者一般同時存在于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例的B細胞中。由于這些模式會影響到患者的預后和對特殊治療的響應,研究人員開始以基因檔案,而不僅僅是細胞外觀為基礎對白血病進行分類。“10年前,我們只是將兒童白血病分為5或6種亞型,而10年后,現今已經有了11或12種亞型,其中每一種都有一組不同的基因變化。”美國田納西州孟菲斯市圣裘德兒童研究醫院,研究兒童白血病基因組的查爾斯·馬利根 (Charles Mullighan)說。
相比之下,其他變異似乎是相互排斥的。例如,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RUNX1基因通常會發生變異;但是如果急性髓系白血病例中出現了一種名為16倒位的易位,那么RUNX1基因就絕對不會發生變異了。這是因為,16倒位會導致出現一種名為CBFB-MYH1的融合基因,該基因迫使RUNX1在細胞轉化為惡性方面發揮作用,美國馬里蘭州貝塞斯達國家人類基因研究所分子生物學家劉浦波(于1993年首次對該融合基因進行了描述)如是說。劉浦波正在嘗試利用該項研究發現,針對這種急性髓系白血病亞型,研發一種新療法。他已經發現了一種化合物,將其作用在實驗小鼠身上,可以擾亂融合蛋白和RUNX1基因之間的交互作用,從而延緩白血病的引發。他希望能夠很快開始進行該藥物的人體試驗。
羅爾思·萊文(Ross Levine)的實驗室正在調查研究與不良預后相關的基因變異群,他也認為,弄清白血病變異基因的結合方式是很有發展前景的。“希望我們不是在研究一種基因,而是在研究一種基因型,”他說,“這可以使我們更好的了解白血病的模式,也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引發白血病的整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