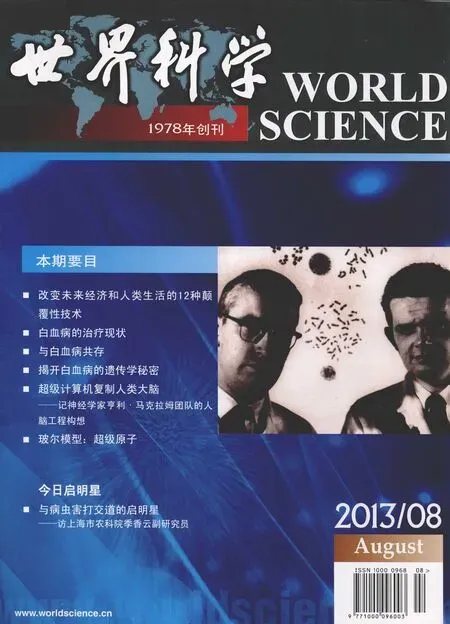藥物安全:雙重危險
蔡立英/編譯

喬倫娜·漢森(右)在童年時期接受了各種各樣的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治療
●小兒白血病可醫治程度很高,但是許多幸存者遭受了嚴重的、甚至有生命威脅的長期的藥物副作用。科學家正在尋找一種更安全的治療途徑。
喬倫娜·漢森(Jolene Hanson)的最早記憶之一,是在明尼蘇達大學醫學中心,坐在輪椅上吃生日蛋糕,那是在1976年3月13日,她4歲生日那天。僅僅16天后,她被診斷患上了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ALL)。那個年代,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奪走了2/3患病兒童的生命。
關于白血病治療,漢森記憶甚少,除了記得她媽媽碾碎了一顆藥丸放到冰淇淋里給她吃。但是她的醫療記錄顯示,她服用了長春新堿、氨甲喋呤、阿霉素、門冬酰胺酶、潑尼松、環磷酰胺和阿糖胞苷等藥物,并且她尚在發育的大腦接受了12輪的放射治療。
這樣高強度的治療治愈了她的白血病,但是隨之而來的是一個詛咒:長期的副作用糾纏了她37年之久。她只有4英尺8英寸高——放射治療導致了她生長激素缺乏并且永遠禿頭。她的醫學日記記錄了長達9頁的劫難:1987年10月15日,“英格沃德斯塔特醫生(Dr Ingvaldstat)排干了我的右側卵巢囊腫,有橘子那么大”;1999年7月20日,“我有一個基底細胞癌從第3、第4腰椎區當場切除了”;2004年8月,“幾個月服用導致不孕不育的藥物、看高風險的醫生之后,診斷結果是我不能懷孕了。”
“我還能怎么樣?”這個問題也是那些尋找能治好白血病而不給患者留下持續幾十年的心臟損傷、認知缺陷、繼發性癌癥和中風等后遺癥的治療方法的醫生們面臨的一個迫切問題。
長期危害
如今,許多白血病的病例都是可治愈的:超過85%的小兒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ALL)患者都幸存下來了,ALL是最常見的小兒白血病。但是超過1/4的小兒癌癥幸存者在接受治療之后的起初25年里,報告了至少是嚴重的、威脅到生命的或是致殘的健康狀況。
研究者面臨的挑戰是尋找到在不降低治療的有效性的同時,能降低這些治療帶來的副作用風險的療法。為了讓副作用風險最小化,他們介紹了能保護患者免受一些危害的藥物,替換有害的療法,并尋找能指示出哪些病人最脆弱的生物標記物。
“過去的哲學是你能活下來就已經是謝天謝地了,治療帶來的問題你就全盤接受吧,”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的弗雷德哈欽森癌癥研究中心的兒科腫瘤醫生 K.斯科特·貝克(K.Scott Baker)說,“但是過去患者的那種心態現在已經改變了。”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那些對小兒白血病進行大腦放射治療的醫生們對復發可能性的關心更甚于對繼發效應的關心。許多化療藥物使大腦容易受到白血病細胞的入侵,因為這些藥物一般不穿越血腦屏障。
“那時候的醫生們沒有真的思考過他們的病人20或30年后會發生什么事情,因為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治愈病人,”在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的達納法勃癌癥研究所領導一個幸存者研究項目的兒科腫瘤醫生麗莎·迪勒(Lisa Diller)說。只有當兒童幸存者達到一定數量時,放射治療對發育中的大腦的風險才變得清晰:它造成了腦腫瘤、生長激素缺乏癥、甲狀腺功能減退癥及學習和記憶障礙問題。
降低風險
現在,很多醫院只有當大腦有很高的舊病復發風險時——例如,白血病細胞已經擴散到腦部,或者該疾病通常是一種影響T淋巴細胞的來勢兇猛的類型,才對兒童實施放射治療。
再次,在e航海項目的建設過程中,航海保障部門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具有e航海示范工程建設維護的實力和技術以及將e航海服務協調整合的能力。同時還為自身儲備了足夠的人才、技術、數據、基礎設施等資源。
如今,醫院也通過管制減少了放射治療——放射量鮮有超過1 200厘戈瑞的,是漢森所接受的累積劑量的一半。大多數兒童不接受放射治療:醫生們寧愿選擇在兒童患者的脊髓液中注射甲氨喋呤和阿糖胞苷之類的藥物,來保護他們的年輕病人的大腦免受白血病細胞的入侵。
但是這些藥物可能導致長期認知缺陷,并有它們自己的其他后期副作用。例如,甲氨喋呤可能損害平衡和正常行走的能力。美國田納西州孟菲斯的圣猶大兒童研究醫院的流行病學家和癌癥研究員萊斯·羅比森(Les Robison)說,甲氨喋呤這種藥物與如此多的問題有關,也許有一天,我們也會像現在看待大腦放射治療一樣看待它,把它視為一種有如此多長期副作用的療法,所以只要有可能我們就應該避免使用。
另一類藥物——包括廣泛使用的阿霉素在內的蒽環類抗生素,則與另一種威脅到生命的后期副作用有關。幾十年前,醫生們就已經知道阿霉素和另一個類似藥物——柔紅霉素,會使左心室壁薄弱,從而導致一些患者充血性心臟衰竭。
醫生們只需減少用藥劑量,就能避免一些這樣的后期副作用。例如,大劑量的阿霉素會使30%的成年人罹患充血性心臟衰竭,但是劑量減半,就會使致病比例大幅縮減。但是,兒童就沒有如此幸運了,因為即使是低劑量的用藥也會增加心臟病的風險,而減少劑量又可能降低藥物的有效性。

“如果你去掉一些治療,以避免毒性,與此同時,你也在冒降低療效的風險,”達納法勃癌癥研究所的兒科腫瘤醫生斯蒂芬·薩蘭 (Stephen Sallan)說。更好的策略也許是增加一種能克制阿霉素傷害、保護健康細胞的藥物。但是過去三年的研究漸漸表明,這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沒有人知道為什么阿霉素對心肌有害,一個可能性是因為阿霉素抑制了拓撲異構酶II,這是一種有助于放松DNA螺旋的酶。研究發現,心臟細胞中缺少這種酶的老鼠在接受阿霉素治療后不會有心肌損傷。但是許多研究者,包括薩蘭,都說阿霉素的毒性可能來自它產生的自由基——如果是這種情況,那么給患者施加抗氧化劑就會有幫助。
一種具有抗氧化劑特性的藥物——血管緊張素轉化酶(ACE)抑制劑——在老鼠實驗上已經取得了誘人的結果,包括發現兩個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可能“幾乎完全阻止”幾種類型的心肌損傷。在成年患者的臨床試驗中,也有一些有希望的結果,但是這些藥物貌似對兒童就沒有這么有效了。薩蘭和他的同事們發現,在接受蒽環類藥物治療之后,服用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的兒童,一開始能看到他們的左心室壁有所加強,但是療效不能持久。
薩蘭更喜歡使用另一種不同的保護心臟的藥物——右丙亞胺,這是一種用于正在接受乳腺癌治療的婦女的自由基清除劑。這種藥物好像有幫助,但是對其使用卻有爭議。歐洲藥品管理局在臨床試驗表明一些兒童相繼產生急性髓細胞性白血病和影響骨髓干細胞的障礙之后,于2011年禁止醫生給兒童開此藥處方。
薩蘭駁斥歐洲藥品管理局的決定是扯淡,指出那些孩子同樣也服用了另一種與這種并發癥有關的藥物。但是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卻對歐洲藥品管理局的決定足夠認真對待以致向醫生建議,還加一句說禁止將右丙亞胺用于兒童。
限制阿霉素的傷害的另一個策略是,只對具有正確基因、能安全地控制此藥的患者使用。對于具有一個特定的調節阿霉素代謝的CBR3基因變量的兒童來說,阿霉素治療可能比白血病本身更可怕。對于這些兒童,“似乎根本不存在阿霉素的安全劑量。”研究者說。
后來的生活
躲過放射治療和化療的后期副作用的患者未必就脫離了生命危險。如果他們的治療包括骨髓移植,他們仍然可能面臨其他風險。“有一整套很獨特的問題,其中有一些還相當長期。”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療中心的血液學家和腫瘤醫生大衛·艾維岡(David Avigan)說。
就像所有的移植一樣,骨髓移植的風險是供體組織的免疫細胞會把接受骨髓移植者識別成是 “外來的”,從而攻擊人體,出現免疫排斥反應。這會導致嚴重的后果,包括對肝臟、肺、皮膚和消化道的長期損害。一個更驚人的后期副作用是接受骨髓移植的白血病幸存者,其瘦肌肉質量會被脂肪代替。這個過程本來是自然衰老的一部分,但是在骨髓移植之后,這個過程似乎被加速了,貝克說。他的研究團隊表明,進行骨髓移植的患者還產生了胰島素抗性,這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其他屬于 “代謝綜合癥”的廣泛類別里的疾病有關,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幸存者罹患這些疾病的風險本來就已經增加了。
盡管后期副作用如此廣泛,但是令人吃驚的是這個問題卻很少被研究,尤其是對除了小兒白血病之外的白血病幸存者的研究。羅比森領導的小兒癌癥幸存者研究項目,跟蹤研究了兩萬多名兒童患者,提供了豐富的數據。但是這樣的研究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金錢,而對小兒急性髓細胞白血病的幸存者的首個長期研究直到2008年才發表。
同樣地,對成年白血病幸存者的后期副作用的研究數據也很少。“兒科醫生們已經領先于我們了,”達納法勃癌癥研究所的研究成年幸存者的腫瘤內科醫生安·帕特里奇(Ann Partridge)說,“顯而易見,既然我們有成年的幸存者,我們就應該為成年幸存者做得更好。”
那些受到歷史上最惡劣治療的喬倫娜·漢森那一代的患者,如今已經40或50歲了,可能產生了一撥如同過早衰老的后期副作用。例如,迪勒提醒說,小兒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幸存者的骨頭密度損失,會導致他們在中年時骨折的風險增加。
美國密蘇里州的圣路易斯兒童醫院的兒科血液病學家和腫瘤醫生羅伯特·林(Robert Hayashi)擔心,高強度的類固醇化療(例如漢森受到的潑尼松化療),會使兒童過早得關節炎。羅比斯發現一群三四十歲的幸存者,有與其年齡不相稱的驚人的肺部高血壓,導致了呼吸困難。
薩蘭說,一些心臟受到蒽環類藥物損傷的兒童,也許最初幾十年可能避免充血性心臟衰竭,只不過是晚些年再發病。“有后期副作用,”他說,“有很晚才出現的后期副作用。”
漢森的病例,當然是如此。幾年前,她說,她的身體還算健康,但在2012年年底,她的右眼后面出現了一個腦瘤,需要動手術。她可能寧愿用放射治療切除腫瘤,但是放射首先就可能致癌,她已經接受過太多的放射治療了。漢森說,她已經準備好了新一輪的后期副作用,“但是,我真的希望我的身體能讓我清凈一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