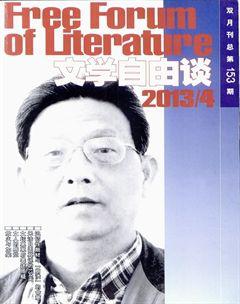文字里的玄機
張傳倫
文字的玄機無時無處不在,孩子在娘肚子里,甚至還沒孕育,名字就早早起好了,大號小名,都要細斟細酌,一點不能含糊,起了什么幾乎應驗什么,關系一生之命勢。以前我不全信,近些年才漸漸開竅兒,《康熙字典》收四萬七千多字,何以你就選定了這四萬分之一二為名為號呢?
以前只知有詩讖,詩讖小者隱昭個人之星途命勢;大者預示國家之興盛衰亡。章淵《槁簡贅筆》載唐代名妓薛濤事極靈驗:“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庭中,指井梧而示之曰:‘庭除一古桐,聳干入云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嗟嘆不已。及長,薛濤果入青樓迎來送往……”
清代袁枚《隨園詩話》載宋徽宗趙佶詠金靈芝句:“早知金帝來為主;不待春天便發生。”金國的鐵騎果真在這一年蕭殺的晚冬之際攻陷北宋首都東京汴梁。運耶?命耶?究是事物發展之必然規律?還是偶然不幸而言中?抑或是冥冥之中自有主宰?
我有一友,性耽木藝雕刻,聊補家用,嘗請人書齋名“苦藝軒”,而后勞艱厄困,每每怵于棘上竟巧,不復樂焉。
世人居家度日,無不期盼戶牖領靜、闔府昌安。就怕有什么三長兩短之事。說來真真難以置信,偏偏有一詩書印大佳之通家作手,親篆堂額冠之以“三長兩短齋”,殊不知吉兇禍福于消長兩端,早有爻象顯焉。
1970年代,吳玉如先生觀弟子山水畫家張鴻千經年運勢蹇促,鴻千適逢六次赴日機會,最后關頭悉被他人頂替,難免意下不快,吳先生開導說:“給你改個名吧,今后遇事當少有人從中作梗,鴻字,易為洪水的洪,鴻翮羽毛縱然萬千,吹一氣繽紛四散,更與你的張姓大不相合,張字偏旁從弓,張弓射鴻,豈有好運,凡張姓起名對活物,多有兇隙隱伏。洪字不同,洪水來了,誰能擋得住?!”洪千即允師命,吳先生一高興,賞其行草唐人詩一幀“直掛云帆濟滄海”,洪千從此一路順風,擘山渲水,喜作瀑布水口,腕下波瀾飚起,一派大水,砰崖囀石,其勢果不可擋。洪千七十從心所欲,常憩鄉間別業,增葺園囿,種樹百行,蒔蔬兩畦,頤養天和,世慮盡釋,畫亦不多作,間一點染,滿紙煙云蒼秀,骎骎入古。
書畫家的名字一旦升為社會認知的符號,若乖若和,易見靈驗,和則祥乖則戾,北方某書家取奉謙虛而實應名讖,書作名款“半知”,壯歲之年身罹半癱。
袁二公子克文,屬“寒云”款字幅,我從來不忍心收藏,望之悵然。1927年,袁克文登報鬻字,廣告聲明:“不佞此后將廢去‘寒云名號。因被這‘寒云叫得一寒寒了十余年,此次署名用‘克文,在丁卯九月以后,無論何種書件均不再用‘寒云二字矣。”然未幾年,復用‘寒云,只是易為草體之‘寒云,云字故意寫成云朵狀,形似‘四十二,這下更要命,不單是寒意陣陣逼人了,陽壽終于四十二歲。
再記一則古代名讖,更可為當今濫名者戒。李靜訓,字小孩,貴為大隋公主,文帝之外孫女,“訓承長樂,獨見慈撫之恩,教習深宮,彌遵柔順之德”。然其壽數實應小孩之名讖,“繁霜晝下,英苕春落,未登弄玉之臺,便悲澤蘭之天”。小孩李靜訓不幸萌年九歲病逝皇宮。一千多年后這個美麗而短命女孩的皇家級別的大墓于1957年被挖掘,出土大量金玉寶器,有關部門頗為得意,競相夸耀:隋代考古,以小孩墓出土文物最為豐富。
當今書家欲為公私堂主題詞作書,炫才還須慎用古典。某書法大師特為香港鳳凰電視臺書“鳳凰臺上鳳凰游”,作草作狂,馳神縱意,足資鳳舞,“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其所取意,尚稱吉順,然此一句七言詩,惟獨不可興題鳳凰臺,電視臺不明究里,偏偏編作片頭廣為播放,忘了太白詩的下一句是“鳳去臺空江自流”。細味此語簡直沒有比這更糟糕的題詞,幸以無甚大礙,而禳解之法亦頗容易。
我有個書法家朋友黃國慶,其于書法一藝的恩師是天津書協主席唐云來,唐先生三年前頃見國慶小楷,取法乎上,鐘繇筆意朗朗可尋,欣然納入門下,不及年余,吸收其為書協會員,如此一來,黃國慶是乃福建、天津之雙編會員,融匯南北書道精粹,潛心修煉,假以時日或當更上層樓。然查以“國慶”為名,全國戶籍可達數百萬。黃姓人家起名只可對植物不可對事物。最是卑姓人家倘欲芳名其女,會意指事,察其締構,名喚“雪蓮”,才使不卑不誣,妙在可與阿爾卑斯山產生聯想。王姓勉強可叫“王國慶”,但萬萬不可叫“王國君”,君不管是哪個君,都要命,這姓名在古代沒有比這更犯忌的了,金榜不會題名,名擺著是在咒皇上呢!古人絕少起這個名字,閭巷苫闔之家不懂文字的玄機,不知不怪,孩童開蒙時,塾師也定會幫助改過來。這番算不得道理的道理總算黃國慶還能聽進一二。他是賣字的寫家,靠此討生活委實不易,起個講究好聽順當的名字大利于生意,不妨落款“大慶”,也好轉轉運,跟他挺般配,大慶是福建人,長得身高馬大一米八五,南人北相有福,鄉梓地望“福安”,福享安康,大吉!他人犟嘴硬,有時嘮叨“國慶”這名也不錯,“國乃五千年古國,焉能不慶”,矯情的太過空泛而且無聊,“大慶”的名款他果然用了沒幾天又換回了他的“國慶”,因為忌憚有人“會一下子想到大慶油田”。尼瑪廢話!油水大發了有什么不好?
國慶寫字有卅載功夫墊底,一筆小楷終歸上得了臺面。一向睿賞小楷的董橋看了喜歡,發一短信要我轉發黃國慶嘉勉一番。給董先生寫字,國慶懂分寸,以小工楷恭錄“乾隆揚州一日膳食譜”,落“八閩秋水軒主”堂號款,未敢亂署“國慶”。先生短信上說:“小工楷寫成這樣真漂亮,不容易,請問他的尊姓大名,八閩秋水軒主出于何典?請代我向他致謝致敬!”
八閩是福建的古稱。“秋水軒”的齋號也還不錯,興許能留住些財運。可我總覺得此一“秋水軒”與他掛筆單的字畫店堂號“慶云堂”一樣清虛一樣飄渺,不如起一個如“慶吉堂”、“吉慶堂”一類趨吉不避俗的堂號倒著些邊際。一心外面混的書畫家福緣湊泊起上一個響當當亮堂堂的堂號同樣重要,寧可大俗不可大雅不可矜貴不可奧古。
我的老朋友當代著名花鳥畫家霍春陽先生的大名他老爸給他起得妙,妙在與“霍”姓乃絕配,春陽春陽,哪個艷麗得過春天的太陽,一切都“霍然開朗”起來,這個“霍”,依常規必用“豁”字,此處易之為“霍”,無病。“霍”字的第一要義是:“鳥疾飛的聲音,引申為迅速貌。”這兩年霍春陽反倒踏實地躲在書齋畫室,悶頭讀書畫畫,讀書有何心得我不知道,畫是越賣越貴,畫價喊出了天價,那些不大不小的資本家都被這“霍霍”磨刀聲嚇得不輕。
我兄何家英先生大名倘以常理度之,或不如世英國英偉英什么英的來得氣派非凡。其實不然,何家英三字深藏玄機。兄已大貴不忌道破。十多年前,一夕興忽來,我寫成一篇文言文的家英畫評《一任清風送白云》,洋洋數千字,得家英睿賞者,不過開篇數語:“何為家英?家法卓英也,家法者,開自家法成天下宗者也。家英之諱名或有數存乎其間矣,世人仰觀家英之畫,當知名實相符。”此文我曾請范曾先生裁鑒,大師以為借何姓創意,妙在只可一敘獨贊何家英,范公早歲曾將“大家風范”,拆鐫為兩方圖章,陰文為“大家風”,陽文為先生尊姓“范”,可謂文思諧妙,與“何為家英”?雅具異曲同工之趣。
古今中外文學大師都精于煉字,狠摳字眼,追求文字美的同時,避一切忌諱,既是照顧自己也是祝福他人。“我們的社會需要更多的專業人士用簡潔的文筆和生活的角度寫本行的知識。學建筑的陳從周用隨筆的文體寫園林,學物理的楊振寧用干凈的英文寫治學的趣事,愛因斯坦一生致力從簡單、普通、統一的原則去描述人類世界的自然規律。”董橋先生舉此三人的例子之前,先從《明報》“成長路”上看到一篇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學系系主任黃重光教授寫的“媽媽,你摘天上的星星給我,好嗎……?”說起這位黃先生“用溫馨的筆調寫孩子的心愿,寫父母的分寸,值得一讀”,可惜黃先生不小心又寫了后面的兩句,“星星當然摘不下來,但父母真摯的愛和無限祝福卻可以把孩子送到天上”,這句話用意正確,比喻不當,送到天上,有歸天之虞。
若論當今散文高手文字之高雅,考究不過董橋,甚至有幾個常用字如“便”,董先生輕易不肯碰,以為“便”字有一句不錯:“小處不可隨便”。壬辰歲尾,我在《天津日報》,“滿庭芳”發表文章“讀書要出聲”,文友羅文華先生好心囑我用毛筆寫這五字做刊頭。好幾個朋友起哄說好,紛紛索書,即興書草,著實令我過了一把癮。黃國慶看著難免技癢,寫了四言橫幅:“讀書便佳。”頗具引申發展了林語堂式“生活的藝術”之功能,林先生說過:“在我看來,快樂問題大半是消化問題。我很想直說快樂問題大抵即是大便問題。”此亦符合美國人尊崇之基督精神,據說一位美國大學校長對每年的新生演講總要說:“我要你們記住兩件事:讀圣經和使大便通暢。”一個人大便通暢,就覺快樂。
“讀書便佳”這件字幅,怎么掛?掛在書齋還是廁所?我是不會懸之于素壁的,我怕讀書就要上廁所上了還要讀書,而讀書的好處不止是排便通暢。黃國慶不妨直截了當書三字“讀書好”或“讀好書”!倘若掉掉書袋,揮毫寫下清乾嘉時期席姓詩人的一句詩,“多讀詩書命亦佳”,豈不更佳!選詩甚苛的袁枚因此句曾引得龍睛賞睞,乾隆說好,故謂“深得朕心”,得載《隨園詩話》。有清一代詩人無不以詩作輯入《隨園詩話》為榮。“多讀詩書命亦佳”,的確是比“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兩句不知害死多少代讀書人的混賬話好得太多太多!多讀書求命好,好在其所求者沒有那么多的功利目的才算真好。
“讀書便佳”,倘若非要擰巴著勁寫此四字不可,也不必較真不必一分高低雅俗,說歸結還是莊子無鞍乘野馬的鬯道之言周詳得很:道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
“便”字,古賢業曾有妙用之辭,唐杜工部七言詩句:“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宋范文正八字家訓:“不為圣賢,便為禽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