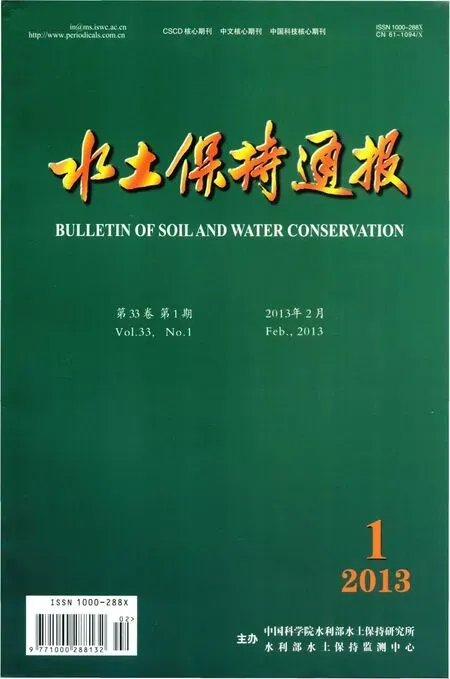陜北黃土區山杏林下草本層植物群落特征研究
王露露,朱清科,趙彥敏,鄭學良,李 萍
(北京林業大學 水土保持與荒漠化防治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北京100083)
山杏(Armeniaca sibiriea)喜光,耐干旱、耐寒、耐瘠薄。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半干旱黃土區山杏人工造林面積不斷擴大,一是促進生態恢復,二是生產甜杏仁;且大部分無或者有較小人為干擾,群落自然演替。自90年代尤其是退耕還林政策實施以來,山杏研究逐步受到重視,但是大多集中在山杏的豐產技術、栽培技術、抗旱生理特征方面[1-2],而對不同立地類型下山杏人工林的生態系統健康狀況和生態恢復效果等未有專題報道。陜北黃土區在植被區劃上屬森林草原交錯帶,植被屬性復雜,由于原生植被基本被破壞殆盡,在該地區的生態修復工作中主要以人工喬(灌)林和自然恢復草地的生態系統健康狀況和生態恢復效果為參考來確定植被恢復的目標和方法[3]。因此,對這一地區分布廣泛、種植面積大的山杏人工林的群落結構、生態系統功能、演替過程等方面進行研究,評價其生態恢復效果,對該區的植被恢復和重建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森林生態系統中林下草本層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人工林中,由于建群種種類單一,群落垂直結構簡單,群落的物種多樣性主要體現在林下草本層,另外林下植被在促進系統養分循環、減少水土流失和維護林地土壤質量中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4];林下草本層與生態系統各組分關系密切,其物種種類和生態型組成、多樣性、生物量等群落特征隨上層林木發育過程不斷發生改變,也會隨著生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5],因此人工林下草本層植物群落特征和演替方向是評價生態系統健康及生態恢復效果的重要依據。
以往對該區人工林的研究多集中在林分的徑級和高度分布、生產力[6],林內土壤水分、養分狀況上[7],對林下植物群落的研究則不多,主要為同齡不同密度條件下或同齡不同樹種林下物種組成、多樣性的差異[8-10],對不同立地類型人工林林下植物演替進程和群落特征鮮有研究。本文以位于半干旱黃土區的陜西省延安市吳起縣為研究區,吳起縣的造林歷史可以追溯到新中國成立之初,但是到1997年之前林木保存率很低,1998年吳起縣先于全國開始了大規模“退耕還林(草)”,是退耕還林(草)工程建設試驗示范縣之一,截至2005年年底,累計退耕還林1 132.47km2。本文選擇該縣不同立地類型保存下來的70—80年代營造的山杏人工純林和山杏沙棘混交林的老齡林為研究對象,通過對林下草本層物種組成、多樣性、水分生態型、蓋度和生物量分布等群落特征動態的研究,揭示陜北半干旱黃土區各立地類型下山杏人工林的林下草本層植物演替過程和方向及不同植被配置模式對林下草本層發育的長期影響,從而從一個新的視角探討各立地類型下營造喬木林的合理性,為該地區生態恢復中植被配置模式的選擇提供依據。
1 研究區概況
吳起縣地處107°38′57″—108°32′49″E,36°33′33″—37°24′27″N,海拔1 233~1 809m,面積3 791.5km2,屬黃土丘陵溝壑區。多年平均降水量478.3mm,年際變化大、季節分配不均,50%~80%降雨量集中在7—9月,年平均氣溫7~8℃,極端最高氣溫37.1℃,極端最低氣溫-25.1℃,無霜期96~146d,為暖溫帶大陸性干旱季風氣候。多年平均陸地蒸發量400~450mm,屬干旱、半干旱地區。土壤類型為黃綿土,質地為輕壤。
該縣植物組成以華北區系植物占主導地位,植被為森林草原向草原過渡類型。由于長期的人類經濟活動,原有植被已不復存在,在現狀植被中以次生植被為主,落葉闊葉林及灌木草叢占主導地位。主要樹種有山杏、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小葉楊(Populus simonii)、油松(Pinus tabulaeformis)、側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山桃(Amygdalus daridiana)等,灌木主要是檸條(Caragana korshinskii)、沙棘(Hippophae rhamnoides)。
2 研究方法
2.1 樣地選擇與群落調查
對吳起縣城周邊的楊青川流域、金佛坪流域、袁溝流域、柴溝流域進行全面踏查,了解山杏老齡林的樹種組成、齡級、立地類型等。立地類型的劃分主要根據地形因子中的坡度和坡向,不考慮海拔、土壤等因素的影響,因此所選樣地土壤類型相同,均為黃綿土,樣地間高差在100m以內。在黃土丘陵溝壑區,以10°~35°的坡面分布面積最大[11],這類坡面也是營造人工林的重點,因此本研究選擇在這一坡度區間內劃分立地類型,10°~25°劃為緩坡,25°~35°劃為陡坡;坡向劃分為陽坡和陰坡。在此基礎上采用空間代替時間的方法,在以上4個小流域選擇不同立地類型的25齡、40齡山杏人工純林和40齡山杏沙棘人工混交林典型樣地。共有樣地類型11種(陽向陡坡立地下沒有山杏—沙棘混交林),每種類型取3個樣地,共有樣地數33個。各樣地概況如表1所示。

表1 山杏人工林樣地基本情況
每個樣地面積10m×10m,記錄樣地的位置、海拔、坡度、坡向,對樣地內山杏打生長錐測定林分年齡。在每個樣地的四角及中央布設1m×1m的草本層調查樣方,記錄草本樣方中植物種類及每個種的個體數、高度和蓋度,對樣方內植物地上部分全部收獲稱量鮮重,并在每個山杏沙棘混交林樣地的四角及中央布設2m×2m的灌木樣方調查沙棘密度。
2.2 物種多樣性測度
采用重要值測度群落種群組成,選取豐富度指數(S),Shannon—Wiener指數(ISW)衡量植物群落物種多樣性特征,Pielou均勻度指數(J)衡量植物群落物種的分布均勻程度[12]:
豐富度指數S:
S=群落中出現的物種數目
Shannon—Wiener指數ISW:
ISW=-∑(Pi×lnPi);
Pielou均勻度指數J:

式中:S——物種種數;Pi=Ni/N,i=1,2…S;Ni——樣地中第i種物種的重要值,并且N=∑Ni。
重要值的計算公式:

2.3 植物水分生態型
依照植物與水分的關系,可以將植物分為旱生植物、中生植物和水生植物等水分生態類型。黃土高原干旱缺水,其顯域生境中生活著從旱生到中生各種水分生態類型的植物。本文將山杏林下植物分為4種水分生態型:旱生型,如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星毛委陵菜(Potentilla acaulis)、長芒草(Stipa bungeana)、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糙隱子草(Cleistogenes squarrosa)、硬質早熟禾(Poa sphondylodes)、火絨草(Leontopodium leontopodioides)、二裂 委 陵 菜 (Potentilla bifurca)、冷 蒿 (Artemisia frigida)、糙葉黃耆(Astragalus scaberrimus)等;旱中生(中旱生)型,如鐵桿蒿(Artemisia sacrorum)、茭蒿(Artemisia giraldii)、達烏里胡枝子(Lespedeza davurica)、大披針苔草(Carex lanceolata)、阿爾泰狗娃花(Heteropappus altaicus)、中華隱子草(Cleistogenes chinensis)、白羊草(Bothriochloa ischaemum)、菊葉委陵菜(Potentilla tanacetifolia)、茵陳蒿(Artemisia capillaris)、野菊花(Dendranthema lavandulifolium)、狹葉柴胡(Bupleurum scorzonerifolium)、披針葉黃華(Thermopsis lanceolala);中生型,如龍須菜(Asparagus schoberioides)、風毛菊(Saussurea japonica)、蓬子菜(Galium verum)、茜草(Rubia cordifolia);濕生型,如蘆葦(Phragmites australis)[13-14]。
3 結果與分析
3.1 林下草本層物種組成
山杏林下草本層共有維管束植物58種,分屬19科,41屬。其中含有5個種以上的科有菊科(Compostae,14種),其次是禾本科(Gramineae,11種)和豆科(Leguminosae,8種),占總科數的15.8%,這3科包含的種數有33個,占總種數的56.9%。其余的16科中有9科為單屬單種占總科數的47.4%。含有1個種以上的屬11個占總屬數的26.8%,11屬共包含28種占總種數的48.3%,其中包含種數較多的有菊科蒿屬(Artemisia,4種),豆科黃耆屬(Astragalus,3種),菊科菊屬(Chrysanthemum,3種),薔薇科陵菜屬(Potentilla,3種),禾本科隱子草屬(Cleistogenes,3種)。其余30個屬均為單種屬,占總屬數的73.2%。物種組成分析結果表明,菊科、禾本科、豆科3科在半干旱黃土區人工山杏林林下草本層中占有重要地位,物種區系構成表現為多數種屬于少數科,少數種屬于多數科,且很多物種為單屬種,符合西北干旱區的植物區系特征[15]。
表2表明,陰向緩坡、陰向陡坡、陽向緩坡25齡山杏純林林下均為旱中生小半灌木鐵桿蒿、達烏里胡枝子組成的共優群落。主要伴生種一般有阿爾泰狗娃花、大披針苔草、中華隱子草、火絨草、長芒草等,僅在不同立地類型下重要值大小不同。隨著自然演替的進行,林下草本層中大披針苔草的優勢度不斷增加,在40齡的山杏純林下成為優勢種,同時鐵桿蒿仍在群落中占有重要地位。
以上3種立地類型下的40齡山杏沙棘混交林林下草本層群落類型均與同齡山杏純林相似,為鐵桿蒿與大披針苔草的共優群落。該地區自然恢復草地在陰坡和陽坡建群種一般不同,陽坡物種更趨向于旱生[16];但各齡級山杏林下草本層優勢種卻基本相同,可能由于山杏林的生長一定程度上減小了生境間尤其是不同坡向立地間的差異。

表2 不同立地類型不同植被配置模式山杏林林下草本層物種組成
陽坡陡坡的25齡及40齡山杏純林林下則分別為星毛委陵菜+鐵桿蒿群落和甘草+大披針苔草群落。星毛委陵菜、甘草在半干旱黃土區多出現在山地草原或森林草原干旱生境中,均為典型旱生植被[14]。因此,陽坡陡坡山杏純林下出現這類次生植被,可能是由于生境逐漸在旱化。
3.2 林下草本層物種多樣性與生物量
由表3可見,相同立地類型下40齡山杏純林林下草本層的香農指數、豐富度指數和均勻度指數均低于25齡山杏純林。林木進入成熟期以后,林下環境因子趨于穩定,因此優勢種的優勢度持續增加,導致多樣性降低。另外,多樣性各指數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除陽坡陡坡立地40齡山杏純林林下物種多樣性顯著低于25齡林(p<0.01),其他立地類型下這2個齡級山杏林林下物種多樣性水平的差異并不顯著,說明在這一階段林下物種多樣性變化緩慢。40齡山杏沙棘混交林林下物種多樣性高于同齡山杏純林,但不顯著。

表3 不同立地類型不同植被配置模式山杏林林下草本層物種多樣性、蓋度和生物量
山杏純林林下草本層蓋度與生物量的變化規律基本一致,在陰坡緩坡、陰坡陡坡、陽坡緩坡3種立地類型下均為40齡山杏純林高于25齡山杏純林,但不顯著;而在陽坡陡坡40齡山杏純林則顯著低于25齡山杏純林(p<0.01)。40齡山杏沙棘混交林林下草本層蓋度與生物量均高于同齡山杏純林,且生物量的差異極顯著(p<0.01),蓋度的差異也達到了顯著水平(p<0.05)。
同林型山杏林在不同立地類型下林下物種多樣性高低排序為陰向緩坡>陰向陡坡>陽向緩坡>陽向陡坡,其中陰向緩坡林下物種多樣性與其他3種立地的差異顯著(p<0.05)。40齡山杏純林及混交林在各立地類型下林下草本層生物量大小順序為陽向緩坡>陰向緩坡>陰向陡坡>陽向陡坡,25齡山杏純林則是在陽向陡坡立地下生物量最大。林下草本層蓋度大小順序與生物量基本一致,也為緩坡大于陡坡。林下草本層蓋度及生物量的變化與喬木層郁閉度有密切的關系[17],郁閉度較高的林分其林下光照條件較差,并且種內種間競爭較大,不利于林下植被的生長發育。在緩坡條件下陰坡林分的郁閉度相對于同齡陽坡林分要大,因此林下植被生物量相對減小一些;陡坡不利于植物種子的定居,水、養分條件相對緩坡也較差,因此蓋度和生物量也相對較小。陽坡陡坡的山杏純林林下草本層生物量25齡時在4種立地類型中最大而40齡時最小,可能的原因是在該立地下山杏林喬木層生長差,郁閉度低,在25齡林林下發育了大量的旱生、喜陽植物,但喬木的生長對地力的消耗超出了其承載能力,使生境無法得到改善甚至惡化,表現在林下植被發育上為隨著林齡進一步增大,植被蓋度、生物量、多樣性均急劇下降。
3.3 林下草本層植物水分生態型
植物由于外界生態因素的影響,逐漸演化出各種各樣的形態和結構以適應生長的環境,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植物生長環境中水分的供應狀況。黃土高原干旱缺水,其顯域生境中生活著從旱生到中生各種水分生態類型的植物。
圖1表明,所有4種立地類型下的山杏25齡、40齡人工純林及混交林林下草本層均為以鐵桿蒿、大披針苔草、達烏里胡枝子、茭蒿、阿爾泰狗娃花等為代表的旱中生(中旱生)植物重要值所占比例最大,取值均在53%~61%,其次是旱生植物,如冰草、長芒草、糙隱子草等,重要值百分比為19%~34%,中生和濕生植物比例最低,分別為5%~20%和0%~5%。分別對比相同立地類型下25齡與40齡山杏純林林下草本層植物水分生態型分布比例可以看出,在陰向緩坡、陰向陡坡、陽向緩坡均為隨著林齡的增加旱生植物比例減小、旱中生和中生植物比例增加,說明林下草本層逐漸由旱生向中生轉變;在陽向陡坡則是隨著林齡增加旱生植物如甘草、星毛委陵菜的重要值百分比增加,而中生植物優勢度減小,林下草本層逐漸趨向于旱生。另外,40齡山杏沙棘混交林林下旱生植物所占比例均小于同齡山杏純林,中生加濕生植物比例也均高于山杏純林。山杏純林林下草本層植物各種水分生態型在不同立地類型下重要值所占比例按大小排序為:旱生植物為陰向緩坡<陰向陡坡<陽向緩坡<陽向陡坡,中生加濕生植物則為陰向緩坡>陰向陡坡>陽向緩坡>陽向陡坡。

圖1 不同立地類型與不同植被配置模式山杏林林下草本層植物水分生態型
4 結論與討論
陜北黃土區山杏林下草本層共出現維管束植物19科41屬58種,以菊科、豆科、禾本科為主,有典型西北干旱區的植物區系特征。山杏純林進入成熟期后,草本層演替趨勢在陰向緩坡、陰向陡坡、陽向緩坡3種立地類型下基本相同,而在陽向陡坡則相反。陰向緩坡、陰向陡坡、陽向緩坡草本層由鐵桿蒿、達烏里胡枝子組成的多年生蒿類群落演替到大披針苔草或鐵桿蒿與大披針苔草組成的森林苔草群落。對比該地區撂荒地(退耕地)由以鐵桿蒿、茭蒿等為優勢種的多年生蒿類群落到較穩定的地帶性白羊草草原群落[18]的自然演替過程,說明營造山杏喬木林后產生了林下小環境,草本層沒有向地帶性的草原植被群落發展而是具有更明顯的森林群落特征。并且在造林25~30齡后,隨著林齡的增加,草本層群落整體水分生態型由旱生型向中生型轉變、蓋度和生物量小幅升高、多樣性略有降低也均符合群落正向演替并趨于穩定的一般規律,說明在以上幾種立地類型下,山杏人工林發揮了森林生態系統的功能,對生態環境的改善有促進作用。而在陽坡陡坡,山杏純林林下草本層物種組成由星毛委陵菜—鐵桿蒿群落演替到甘草—大披針苔草群落,典型旱生物種始終占據優勢,而且多樣性、蓋度、生物量均隨林齡增加顯著降低等現象均說明群落正在逆行演替,生境不斷惡化。
另外,在陰向緩坡、陰向陡坡及陽向緩坡,與純林相比山杏沙棘混交林下草本層優勢種雖然相同,但物種多樣性、植被蓋度和生物量均增加,其中蓋度和生物量顯著增大,并且旱生物種優勢度減少,中生成分增加。在半干旱的黃土區,能夠維持較高生態系統穩定性的能力和良好的水土保持功能是選擇人工林植被配置模式的重要依據。穩定性與物種多樣性關系密切,雖然多年來對于有關“多樣性與穩定性”的生態學基本問題爭論不斷,但大多數試驗研究結論和多種假說認為多樣性導致群落和生態系統水平上的穩定性[19];高的物種多樣性可能意味著更多種功能群或者冗余作用的存在,能夠對于干擾作用下生態系統功能的發揮起到補償作用,從而提高群落和生態系統的穩定性[20]。人工林物種多樣性主要體現在林下植被層,因此增加林下植被層物種多樣性對提高生態系統穩定性有著一定的意義。另外,人工林群落中地被植物層的物種多樣性、蓋度、生物量等的提高,能夠直接減弱降雨動能,同時通過改善表層土壤結構,增加入滲和土壤抗蝕性,從而減少地表徑流和土壤侵蝕量[21],具有更好的水土保持效果。因此從林下植被發育情況的角度來看,山杏沙棘混交林比山杏純林具有更高的穩定性和水土保持功能。
近年來,半干旱黃土高原森林草原區人工林下普遍出現不同程度的土壤干層,林木出現生長發育不良現象,部分形成“小老樹”,甚至成片死亡,引發了對在這一地區配置喬木林的質疑[22]。然而研究表明,這一地區能夠自然更新的天然針葉疏林同樣生長緩慢并且林下存在土壤干層的發育[23]。說明森林在半干旱地區生長緩慢和產生一定程度的土壤干化也是自然現象[24],抗旱性強的樹種在受到干旱脅迫后會通過減慢生長速度來減少蒸騰耗水同時提高水分利用效率,從而保持與環境供水能力的平衡狀態,維持群落穩定性;只有當樹種選擇失當、密度過大、群落生產力過高導致林下土壤處于持續而嚴重的“赤字”狀態,才會使植物生長衰退,群落發生逆向演替。因此本研究認為在半干旱陜北黃土區恢復植被應根據立地條件選擇樹種和控制密度。在陰向緩坡、陰向陡坡、陽向緩坡立地應配置山杏這類低耗水、生長慢喬木樹種,采用與沙棘等鄉土灌木樹種混交的模式更有利于提高群落穩定性和加快生態恢復的進程,但應嚴格控制密度,山杏林林分穩定密度約為400~800株/hm2,且山杏沙棘混交林密度比純林更小。不同立地類型下準確的林分合理初植密度和穩定密度還需要更進一步研究確定。在陽向陡坡立地應以營造生長速度適中的灌木林或自然恢復草地植被群落為宜。
[1]劉明國,王威,賀江,等.山杏混交林花果期小氣候特點及其對坐果率的影響[J].東北林業大學學報,2010,38(6):28-30.
[2]黃世臣,李熙英.水分脅迫條件下接種菌根菌對山杏實生苗抗旱性的影響[J].東北林業大學學報,2007,35(1):31-32.
[3]劉中奇,朱清科,秦偉,等.半干旱黃土區自然恢復與人工造林恢復植被群落對比研究[J].生態環境學報,2010,19(4):857-863.
[4]褚建民,盧琦,崔向慧,等.人工林林下植被多樣性研究進展[J].世界林業研究,2007,20(3):9-13.
[5]Kume A,Satomura T,Tsubei N,et al.Effects of understory vegetation on the eco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n overstory pine,Pinus densiflora [J].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2003,176:195-203.
[6]張光燦,劉霞,周澤福,等.黃土丘陵區油松水土保持林生長過程與直徑結構[J].應用生態學報,2007,18(4):728-734.
[7]張建軍,李慧敏,徐佳佳.黃土高原水土保持林對土壤水分的影響[J].生態學報,2011,31(23):7056-7066.
[8]趙娜,查同剛,周志勇.晉西黃土區不同樹種配置對林下植被物種多樣性的影響[J].東北林業大學學報,2011,39(3):44-45.
[9]楊曉毅,李凱榮,李苗,等.陜西省淳化縣人工刺槐林林分結構及林下植物多樣性研究[J].水土保持通報,2011,31(3):194-201.
[10]高艷鵬,趙廷寧,駱漢.晉西黃土丘陵溝壑區人工林下草本植物生物多樣性研究[J].水土保持通報,2011,31(1):103-108.
[11]趙薈,朱清科,秦偉,等.黃土高原溝壑區干旱陽坡的地域分異特征[J].地理科學進展,2010,29(3):327-334.
[12]馬克平,黃建輝,于順利,等.北京東靈山地區植物群落多樣性的研究:Ⅱ.豐富度、均勻度和物種多樣性指數[J].生態學報,1995,15(3):268-277.
[13]朱志誠,黃可.陜北黃土高原森林草原地帶植被恢復演替初步研究[J].山西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3,16(1):94-100.
[14]雷明德.陜西植被[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233-282.
[15]黨榮理,潘曉玲.西北干旱荒漠區種子植物科的區系分析[J].西北植物學報,2002,22(1):24-32.
[16]秦偉,朱清科,張宇清,等.陜北黃土區生態修復過程中植物群落物種多樣性變化[J].應用生態學報,2009,20(2):403-409.
[17]Rankin W J,Tramer E J.Understory succession and the gap regeneration cycle in a Tsuga canadensis forest[J].Canadian Journal of Forest Research,2002,32(1):16-23.
[18]秦偉,朱清科,劉中奇,等.黃土丘陵溝壑區退耕地植被自然演替系列及其植物物種多樣性特征[J].干旱區研究,2008,25(4):507-512.
[19]Tilman D,Wedin D,Knops J.Productiv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fluenced by biodiversity in grassland ecosystems[J].Nature,1996,379:718-720.
[20]黨承林.植物群落的冗余結構:對生態系統穩定性的一種解釋[J].生態學報,1998,18(6):665-672.
[21]王震洪,段昌群,侯永平,等.植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土壤保持功能關系及其生態學意義[J].植物生態學報,2006,30(3):392-403.
[22]李軍,陳兵,李小芳,等.黃土高原不同植被類型區人工林地深層土壤干燥化效應[J].生態學報,2008,28(4):1429-1445.
[23]朱志誠.陜北黃土高原杜松疏林草原初步研究[J].林業科學,1991,27(4):447-451.
[24]趙景波,周旗,侯甬堅.黃土高原土壤干層對生態環境建設的影響[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3,31(4):9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