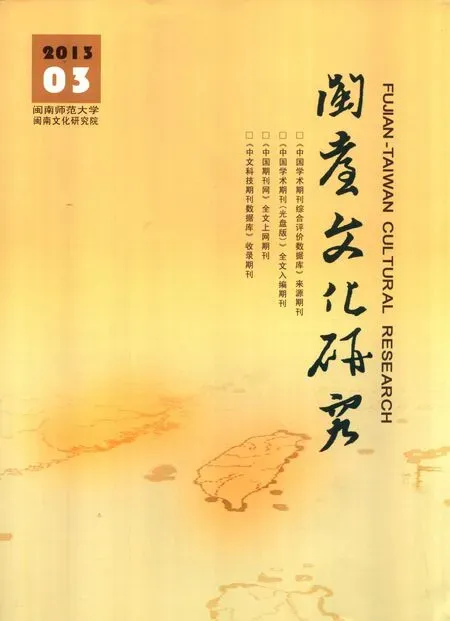朱熹知漳與漳州理學之進路
鄭晨寅
(閩南師范大學 閩南文化研究院,福建 漳州363000)
閩人楊時、游酢從學于二程,遂有“道南”一脈;洛學南傳,朱熹接緒之,又直接催生了閩學;朱子知漳雖僅一載,其于閩南理學,可謂遺澤深遠。漳州自唐初設郡以來,文教漸興,開漳將軍陳元光子陳珦首創書院于松州,推行教化,元和有龍溪周匡物始及第;宋時又為朱子過化之邦;明時清漳大儒輩出,而王守仁亦曾勘亂此地,析置平和縣,漳州的歷史文化積淀頗為深厚。本文以朱子知漳為發端,梳理漳州理學大致脈絡,探討宋明理學(主要是朱子學)在漳州的源流與發展。
一、朱熹之前的漳州儒學與朱熹知漳的歷史意義
閩中儒學開先于唐歐陽詹。在朱子學(又稱閩學,或稱考亭學派)產生之前,閩地先有北宋“海濱四先生”倡導理學,后又有楊時、游酢之南傳洛學(即“道南學派”)。漳州建州始于唐垂拱二年(686),自宋以來文化重心南移,漳州文化事業亦逐步發展,朱子(1130~1200)之前的漳州理學家主要有漳浦蔡元鼎、龍溪顏慥、高登等人。蔡元鼎當五季喪亂,隱居不仕,以文章自娛,宋初屢征不就,講學大帽山,生徒至者千人。朱子稱道之曰:“元鼎獨潛心六經,著《大學中庸解》、《語孟講義》,何其擇術之正與! ”顏慥(1009~1077)與蔡襄(曾任漳州軍事判官)為金石交,“時海濱文教未興,慥倡明道學,教授生徒,人皆化之。”高登(1104~1159)字彥先,號東溪,宣和七年(1125)金兵犯京師,他與太學生陳東等聯名上書,請誅蔡京等六賊,名震天下,其學則以慎獨為本,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云:“漳江之學至北溪得紫陽之傳而遞衍繁盛,然在靖康間,時有東溪高先生者,以忠言志節著聲,朱子蒞漳,曾新其祠宇,又為之記,言先生學博行高,志節卓然,有頑廉懦立之操,其有功于世教,豈可與隱忍回護以濟其私而自托于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語哉!按:東溪之學亦一時倡起之師也。”其弟子漳浦陳景肅乃唐開漳將軍陳元光裔孫,師事高登,有學行,紹興二十一年(1151)登進士,因惡秦檜而乞歸,與門人楊士訓(后亦為朱子門人)、吳大成等講學漸山。高登另一弟子漳浦林宗臣則引導陳淳入朱子門下。于此可見,朱熹與高登乃為志同道合者,高東溪學派與朱子學派在思想上、人員上又有著緊密的聯系。除上述幾人外,另有黃碩、楊汝南等皆以名儒直節見稱,此不詳述。由上可知,漳州理學有著較為深厚的文化底蘊
漳州自古以農業為本,又負山濱海,“近山之民藉種植……濱海者以漁為生”,故萬歷癸酉《漳州府志》云:“其民務本,不事末作,質樸謹畏,俗尚淫祀,互作淫戲,樂善遠罪。”朱子守漳一年,政績顯著,他輕徭薄役、移風易俗,行經界、興文教、定禮儀,而民安習其化,故《漳州府志》言朱子,“至任,以節民力、易風俗為首務……民被其惠,至今思之。”對漳州的影響極為深遠,史志如《宋史》、《漳州府志》,時賢論著如張立文《朱熹評傳》、束景南《朱子大傳》等,于朱子知漳事跡皆有述論。林宗臣有詩稱道:“笑憑詩句說丹霞,城郭人民千萬家。禮接紫陽風俗厚,學傳鄒魯道源賒。”漳州遂有“海濱鄒魯”之稱,后人于此亦多所追憶,如明羅青霄萬歷癸酉《漳州府志》序云:“大儒朱文公來守其郡,勉齋、北溪二公實羽翼之,講明理學而教化丕振。及至我國朝,名宦鄉賢彬彬輩出,文獻足征,稱為海濱鄒魯,信不誣矣。”清覺羅滿保康熙《漳州府志》序云:“當宋紹熙間,風氣猶薄陋,洎紫陽朱子領郡,定法制,興教化,而風俗稍變。”車鼎晉則序云:“漳郡為朱子舊治之邦,自南宋至今五百余年,禮教猶新,名賢輩出,舊稱海濱鄒魯。”在這些敘述中,“朱子—漳州—海濱鄒魯”三者密不可分。朱子知漳已成為漳州一種獨特的歷史記憶。
二、朱熹漳州門人述略
朱熹在漳州大力推行教化,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加強學校教育,他“每旬之二日必領官屬下州學,視諸生,講小學,為正其義;六日下縣學,亦如之。”同時,加強講官的擇用,“擇士有行義、知廉恥者,列學職,為諸生倡”,延請郡士黃樵仲、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陳淳、楊士訓及永嘉徐寓八人為學官,入學表率諸生,對漳州教育事業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劉樹勛《閩學源流》所附“朱熹門人錄·漳州朱熹門人”列有九人,其中包括上述八位學官中的七人永嘉人徐寓除外,另二人為王遇、朱飛卿。朱飛卿亦受業于朱子,“自言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灑落處,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傾向于淡泊礪志一路。龍溪王遇(1142~1211),字子合,號東湖,從游于晦庵(朱熹)、南軒(張栻)、東萊(呂祖謙)三先生之門,其學務求精思力行,“朱子稱其純篤”,楊士訓即為其女婿。《漳州府志》又云:“漳自朱子守郡,講明禮樂,以正人心,自是海濱家弦戶誦,有能心朱子之心者,且一變而進于道,北溪、東湖其人也。”對王東湖給予了高度評價,可見王遇在當時漳州學界的地位北溪詳下。除此九人外,還有龍溪陳思謙,學問該博,朱子喜之,語其門人李唐咨以女妻之;黃學皋及宋聞禮于朱子守漳時“以稚年輪講”(黃學皋后更入郡齋校勘《朱文公續語錄》),似亦可列入朱子門人。除漳州士人外,黃榦等朱門弟子及外地求學者亦先后踵至,這也促進了當時漳州理學的繁榮。蔣垣《八閩理學源流》云:“清漳文物,自朱晦翁守郡,延黃道夫(即黃樵仲)于學以勵勸生徒,從者風云動蒸,一趨于正,而儒道大興。”朱子于紹熙元年(1190)知漳,約一年后去漳,離任時,其政治主張雖不能盡行,但漳州已蒙大儒周年之澤,無論是制度層面,還是風俗人心,都已打上了朱氏烙印,程朱理學從此根深蒂固,故明代中葉以后心學盛行,漳州學界卻仍是朱子學占據主要地位;而朱子學的格物窮理、求實力行的品格及追求至德之境的主體精神,也深深地影響了后世漳州士人。
此處有必要對朱門高弟—陳淳略述一二。陳淳(1159~1223)不僅是朱子的弟子,還是朱子學的發揚光大者,在理學的“道統”中有著特殊地位,故《漳州府志》稱之為“朱門高弟”。陳淳生于漳州北溪之濱,天資高穎,初習舉業,后因林宗臣授以朱子所編《近思錄》,遂盡棄其舊學而服膺朱學,朱子守漳,陳淳往見,二人相見恨晚,朱子授之以“根源”二字,對陳淳深究義理有重大影響。朱子離漳后,陳淳又多次書札往還問學,及至朱子去世前三月,陳淳復見,朱熹又語之以“下學”功夫。朱子逝后,陳淳“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最終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陳淳有《北溪大全集》等著作多種,其中《北溪字義》最能體現其思辨精神,它對性、命、道、理等理學重要范疇進行分類疏釋,折衷師說,多有精意,《四庫》館臣稱其“每拈一字,詳論原委,旁引曲證,以暢其論”,是解讀理學、尤其是朱子學的重要文本。從陳淳問學于朱子的學術歷程來看,陳淳傾心于朱子,于程朱理學精思竭慮,每有所得,皆為自身體貼而出,故其于朱子學知之深切,因此對于維護師門道統的純粹性也是不遺余力,《宋元學案·北溪學案》稱其“衛師門甚力,多所發明”。作為朱子知漳時的最重要門人,陳淳不負師望,闡明義理、講學嚴陵、授業漳南、衛道師門,成為朱子學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漳州理學史上標志性的人物。《漳州府志》稱其“使清漳之流接源于濂洛洙泗”,信不為過。《閩中理學淵源考》之“陳淳學派”列有陳淳弟子友人10人,多莆田、泉州人士,其中漳籍人士中有弟子蔡逢甲(字國賢)、友人潘武(字叔允)。
三、朱熹對漳州理學進路之影響
(一)元代漳州理學概觀
蒙古族入主中原,在殘酷的民族壓迫的同時,漢化也在不斷地進行。除了對孔子的尊崇(武宗至大元年詔尊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外,以程朱理學為科舉考試(仁宗皇慶二年實行)的判斷準則,也是漢化的重要內容。故宋元間學派繁多,但朱學仍遞傳不失,而漳州一地,據李清馥言,“元代明卿諸賢一時斌斌儒林之選,其隱身巖穴或以薦舉而膺師儒之任者,比比矣。”“清漳諸先生學派”中列有林廣發(字明卿)、王吉才(號益齋)、黃元淵(字君翊)、周祐(字于一)、楊稷(字宗璉)五人,皆好古篤學,其中林廣發向慕宋儒高登(號東溪)、陳淳(號北溪)、蔡汝作(號南溪)三人,故其著作名曰《三溪集》;黃元淵私淑朱子,重修龍江書院于漳,建祠堂祀朱子,并以黃榦、陳淳二人配祀。故《漳州府志》論曰:“元去宋未遠,鄉先生遺烈猶有存焉者。淵源所漸,學有家法,以是嘆考亭之教思無窮矣。”這使得漳州朱子學在元代仍得以延續與發展。
(二)明代漳州理學概述
明初,朝廷以程朱理學為統治思想,永樂十三年(1415)三部《大全》(《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的纂定標志著朱學統治地位的確立。明中葉,隨著封建統治危機的加深,心學崛起。朱學仍處于官方哲學的地位,又面臨心學的沖擊,呈現衰落景象,《明史·儒林傳》云:“嘉、隆而后,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但在漳州則仍是朱學為主的格局,其中自有朱子知漳之緣由,而師友相傳之“家法”、大儒迭興之勝況,使明代漳州理學呈現特有的發展脈絡。
《閩中理學淵源考》以學派來標明師友淵源,“諸賢有傳習源流者,皆錄于學派”,對梳理有明一代之漳州理學頗具參考價值。“清漳明初諸先生學派”列有劉宗道(名駟)、李貞(永樂時曾參與編輯《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林皥、胡宜衡(名楀)、柳文通、吳汝華(名霞)等六人,皆習程朱之學,如劉宗道曾從學于三山趙彥進,“彥進修程朱之學,議論極為醇正”,對他影響很大;宗道又好修《家禮》,鄉人稱為“愛禮先生”,有《愛禮集》十卷,陳真晟讀之,“稱其繼北溪而起大有功于名教”。又如胡宜衡為龍溪胡宗華之次子,胡宗華號草澗居士,潛心理學,《漳州府志》給予高度評價:“朱子之學,由元入明,盛于浙東何、王、金、許四先生(即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觀草澗胡氏之規言矩行,以律身稽古正學以迪士,何其與四先生之心相契也……當洪武立國之初,為閩學開先,此其人矣!”胡宜衡家學淵源,自是朱學一脈。
明初還有“唐泰學派”。唐泰(1393~1455)字師廓,長泰人,通曉五經,尤邃于《易》,筑草舍百余間以教四方之士,隨才誘誨,皆有成就,學者稱東里先生。唐泰弟子陳真晟(見下文)、謝璉(字重器)、林震(字敦聲)、陳亹(字尚勉),無論文章、政事,皆名重一時,故李清馥稱:“唐公在明代國初沈潛經訓,諸名徳多出其門,實倡起之師也。”
其中陳真晟又自為一學派。陳真晟(1411~1473)字剩夫,漳浦人,從學于唐泰,參加省試時,聽說有司防察士子過嚴,無待士之禮,故歸而不試,自號漳南布衣。陳真晟雖身為布衣而關心國事,曾于天順三年,效仿程頤故事,詣闕上書,進《程朱正學纂要》,揭揚程朱心法。其理學主張為“主一”之說,曾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明末大儒劉宗周評曰:“‘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即慎獨之說,誠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識慎獨義,故以‘主一’二字代之。此老學有本領,故立言諦當如此。”陳真晟曾聽說臨川吳與弼(1391~1469,號康齋,著名理學家)之名,欲往質之,行至南昌,張元禎叩其所學,大加稱許,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如康齋(即吳與弼)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陳真晟強調儒家之“圣學心要”,認為:“拳拳以主敬、窮理、修己為首例,以口耳浮靡為痛革,正與程氏心教之法相表里。”他倡主一誠敬,弘揚正學,心系教育,身為布衣而心懷天下,可謂直接程朱道脈,故張元禎言“得其真”并非虛譽。其弟子丁世平送其詣闕上書詩云:“心借程朱五百載,道憂孔孟三千年。”也是就其于道脈之接續而言。布衣學派中有龍溪林雍(字萬容),學者稱蒙庵先生,憲宗時曾上疏請進周敦頤、程灝、程頤、朱熹于顏曾思孟之后,列為八配;又請祀陳淳于兩廡,皆不報。后歸,與陳真晟相師友,陳真晟稱其學“始終本末,有序有要”。“漳人謂北溪之后得正學之傳者,真晟與雍二人而已。”布衣弟子還有龍溪魏富(字仲禮)、丁世平(字迂峰)。
稍后有周瑛。周瑛(1431~1519)字梁石,學者稱翠渠先生,祖籍莆田,其父于洪武間自莆田調戍于漳浦之鎮海衛,周瑛生于此;致仕歸莆后,漳州知府陳洪謨聘他主修府志,他慨然受聘,其正德《〈漳郡志〉序》稱:“漳亦鄉郡也。”周瑛早年為陳真晟學生,學問力主居敬窮理、一歸本原,他認為:“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為先務。收放心,居敬是已。蓋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由此日生,然后可以窮理。窮理者,非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周瑛弟子中漳州人有龍溪鄭衷(字世和)、施仁(字近甫)。
龍溪蔡烈曾受知府陳洪謨之命,詣莆請周瑛修漳志。蔡烈(1479~1558)字文繼,長年隱居鶴鳴山白云洞,學者稱鶴峰先生,曾從學于晉江蔡清、莆田陳茂烈。蔡清為著名朱子學者;而陳茂烈則為心學先驅陳獻章(1428~1500,廣東新會人,學者稱白沙先生)高足,“獻章語以主靜之學”。蔡烈于學問之道反復求索,嘗游武夷山,居考亭精舍數日而歸,曰:“腳跟自此定矣。”可見其對朱學的潛心探究與衷心信服,故《漳州府志》稱“其學一宗程朱,以窮理力行、為實主敬為要”。
這一階段是漳州理學的繁榮期,《漳州府志》將唐泰、陳真晟、林雍、周瑛、蔡烈五人合傳,并分別指出其學術特色:“布衣以主一為要……東里思誠,翠渠檢心,蔡氏文繼不言而躬行,蒙庵……始終本末,有序有要。”因而稱道曰:“自安卿師紫陽,倡道海濱,至明而大儒繼起,或淵源相接,或羽翼互持,清漳之學于斯為盛矣。”其中陳真晟、周瑛、蔡烈入《明史·儒林傳》唐泰、林雍亦見載于《閩中理學淵源考》、《八閩理學源流》等著述,與朱熹、陳淳入《宋史·道學傳》先后輝映,延續了漳州理學的發展命脈。
明末,漳郡有漳浦黃道周出。黃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又字幼平、螭若等),人稱石齋先生,其學問博大精深,學主程朱,又積極回應當時心學思潮,是明代漳州理學的一個總結性人物。
據莊起儔《漳浦黃先生年譜》載,黃道周七歲即由其父授朱子之《通鑒綱目》,“先生昕夕研閱,便知忠良邪正之辨、人治王道之大。”(參見《明漳浦黃忠端公全集》卷首)黃道周身處明末,其時國勢日危,建州女真虎視眈眈,與朱子所處南宋面臨異族入侵的情境相當,朱子主張“華夷之辨高于君臣之分”,并于上孝宗《封事》中旗幟鮮明地反和主戰:“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不可和也,明矣。”而黃道周也極力反對與建州議和,《漳浦黃先生年譜》先生五十四歲時有載:“其《論遼撫臣議款疏》謂:‘臣接得遼撫臣方一藻揭帖,援俺答故事議款,臣不覺為之頓足,投牒于地……惟陛下慨然發樞邊諸疏,眾正其論,毋使事成禍積,異日不可復悔。’”后來黃道周于南明隆武朝時,以一介書生率師抗清,兵敗被俘,以身殉國,其民族大義凜然,良有得于朱學之熏陶。作為漳州人,黃道周每“念是桑梓為紫陽過化之邦”,在講學時,時時不忘標榜朱學。崇禎五年(1632),黃道周因直言進諫被削籍還鄉,途經浙江余杭大滌山,門人為之創大滌書院,后來黃道周多次講學于此。大滌山洞霄宮有李綱、朱熹二賢祠,黃道周有詩文多篇,極力稱道二賢之忠君愛國,并揭揚朱子之學。崇禎七年(1634),黃道周講學于漳州榕壇,榕壇在郡城芝山,上有紫陽祠。黃道周榕壇首講便以“格物致知”發端,當看到諸生課義“半依朱義,無為陸氏之說者”,為弟子能遵循朱子學說而感到欣慰:“私喜晦翁實詣之效一遂至此”。《榕壇問業》共十八講,“大旨以致知明善為宗,大約宗法考亭而益加駿厲”。崇禎十七年(1644),黃道周講學于漳州鄴山書院,書院建有三近、樂性、與善三堂,其中與善堂為先圣先賢之神堂,前楹祀朱子、陳淳、黃榦、王遇、高登、陳真晟、周瑛、林魁、蔡烈,稱“九先生”,除林魁外前文皆有論及;而從這些先賢身上,正見出漳州理學的發展脈絡。
明末,作為理學的補偏救弊的王學也開始走向沒落,學術思潮面臨著新的整合,黃道周在堅守朱學的同時,也注意自身思想的調整,融通朱陸,以應對當時的社會現實。他在《朱陸刊疑》中說:“晦翁之格致,子靜之良知,皆有瑕亹,亦皆不遠于圣門之學。化子靜以救晦翁,用晦翁以濟子靜,使子靜不失于高明,晦翁不滯于沈潛,雖思、孟復生,何間之有?”他在《大滌書院三記》中,結合自身學問之道對朱陸之學作了總結:“由子靜之言,簡確直捷,可以省諸探索之苦,然而弊也易。由仆之言,靜觀微悟可以開物成務,然而弊也支。由元晦之言,拾級循墻,可至堂室,高者不造頂無歸,深者不眩崖驚墜。由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晦。”前人亦已注意到黃道周與朱子的一脈相承,故多有將二人并提之論。黃道周門人洪思《收文序》云:“其于理也,為程氏,為考亭,至于今日乃兼之。”指出黃道周對程朱理學的繼承。陳壽祺《重編黃漳浦遺集序》則提及黃道周“德性似朱紫陽”。沈定均《增刊〈漳州府志〉序》云:“自宋朱子為之官師,洎明石齋黃氏以理學忠孝倡導后進,士民益敦志行。”著重指出二人之于漳郡教化的重要性正相類似。
《閩中理學源流考》有“黃道周學派”,包括張若化(字雨玉)、張若仲(字聲玉)、張士楷(字端卿)、蔡春溶(字時培)、賴繼瑾(字敬儒)、林邁佳(字子篤)、洪思(字阿士)、陳天定(字祝皇)、涂仲吉(字德公)、紀許國(字石青)、王仍輅(字載卿)、張燮(字紹和)、范方(字介卿)十三人。而海澄周起元(1571~1626,字仲先)、鎮海何楷(1594~1645,字玄子,號黃如)為黃道周同道,其道德文章為時人所敬仰,故與黃道周一起成為晚明漳州士人之典范。傅小凡、卓克華《閩南理學的源流與發展》一書中所論及漳州理學家有宋陳淳,明陳真晟、周瑛,清藍鼎元、蔡世遠,而不及于黃道周。陳來在《黃道周的生平與思想》一文中則將黃道周歸為“比較傾向于朱子學格物論的獨立思想家”。黃道周的理學思想仍有待深入研究。
易代之際,往往也是人才凋零之時。隨著明朝的終結、乃至南明的覆滅,漳州理學也告一段落。雖然清代理學仍有發展、延續,漳州一地也出現了如藍鼎元、蔡世遠等朱子學者,但總體缺乏新的內涵,且清代的學術主流為考據之學,故不在本文論述范圍。
四、漳州理學之特點
以上所論漳州理學之源流,僅就其大略而言,諸多理學先賢不能一一論及,然漳州理學的一般特點卻可試歸納如下:
(一)重道統,守宗傳,恪守朱子學脈
朱子學自身的理論優勢、朱子知漳的歷史遇合、宋明時期朱學官方地位的確立等都對漳州士人對朱學的選擇與接受產生重要影響。由上述可知,從“朱門高弟”陳淳的衛道師門,一直到明末“學無師承”的黃道周之學宗考亭,朱子學在漳州一地始終得以傳承與發揚,漳浦林一陽(字復夫)所謂“道至程朱,有何不盡,何須別立教門”很能代表漳州士人的看法。故魏荔彤稱漳郡“鮑謝庾徐,風雅固多哲匠;關閩濂洛,宗源更有醇儒。”雖然閩地學術本有“篤師承、謹訓詁,終身不敢背其師說”的傳統,但李清馥仍對漳郡學脈之綿延感慨系之:“大賢之澤,百世其昌,雖蒞政僅及一期,而遺風余榘于今猶未艾也,尋學脈者能無慨系于茲邦!”漳州理學家本身即很重視道統,陳淳的《師友淵源》、林祺的《考亭源流錄》及續朱子《伊洛淵源錄》之《考亭麗澤錄》、蔡烈的《道南錄》及《諸儒正論》、黃道周的《儒脈》等都是對儒家道統的尋根溯源。
(二)重讀書,于浩瀚文獻中探究學理
朱子本就極重視讀書窮理,所謂“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漳州的理學家繼承了這一點,前文已言及陳淳“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友潘武亦“于書無所不讀”,周瑛“早歲博覽郡籍,鉤深探賾”,林祺“祁寒暑雨,手不釋卷”,周瑛稱之為“正學之徒”,蔡烈人稱“力行好學,老而不倦”,何楷則“博綜群書,寒暑勿輟”,黃道周未中進士時曾閉門讀書數年,所居處旁開一門如狗竇,只許問學者進出;他說:“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四庫》館臣稱其《榕壇問業》:“書內所論凡天文、地志、經史、百家之說,無不隨問闡發,不盡作性命空談,蓋由其博洽精研,靡所不究,故能有叩必竭,響應不窮。”不博覽群書則無由至此。應該說,這種通過讀書積累以致知的治學路數,與心學的側重內省、不假外求是截然不同的。
(三)重踐履,積極入世,心憂天下
讀書窮理要與躬親實踐、身體力行相結合,方為真道學。漳州理學家大多能學以致用,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如前述陳真晟以布衣詣闕上書即為明證;而其主張每不為當道所用,據林雍所作《行實》,陳真晟“既無所遇,每四顧徬徨,不能自釋”,可見其所憂。謝璉為翰林時亦敢于直諫,《閩中理學淵源考》稱“故事,翰林居養優之地,以筆翰相高,慷慨論朝政自璉始”。實啟翰林論政之風。蔡烈雖為隱士,但并不空談心性,“主簿詹道嘗請論心,烈曰:‘宜論事。孔門求仁,未嘗出事外也。’”故學士豐熙稱其“不言躬行”。黃道周友人張燮屢征不起,人稱“征君”,然論周起元之死曰:“吾漳二百年來金紫相望,獨以身殉國者寥寥,今乃得仲先忠臣孝子,天地正氣,此是鐘靈之最者。”對周起元為國而死之于漳郡的意義作了深刻的解讀。黃道周于崇禎朝時以一介文臣,屢次請纓出關;隆武朝時奮然率師北伐;南京就義前絕筆“蹈仁不死,履險如夷;有隕自天,舍命不渝”,皆可見其渴望治平天下、舍身取義之儒者胸懷。
(四)重交流,在學術切磋中完善自我
朱子早年亦曾泛濫辭章、出入佛老、轉益多師,并在與陸氏兄弟等持不同見解的學者相互問難中汲取他人所長,最終形成自身學術體系。漳州雖僻處閩南一隅,但漳州理學家亦有較開放的學術心態,在以朱學為主的同時,并不閉門自是、固步自封,而積極加強與外界聯系,在向他人的學習、交流中完善自身的學術品格,而這一點特別體現在漳州學者與心學學者的交流上。前文已言及楊士訓本從學于陳景肅,后又入朱子門下;王遇從游于朱熹、張栻、呂祖謙三先生。至明時,陳真晟“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聞吳與弼之名,欲就問之,臨行對其侄云:“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布衣陳某墓’足矣。”為問學而一輕生死。陳真晟與吳與弼弟子陳獻章則為神交之友,《漳州府志》載有陳獻章《與布衣先生詩》,中有“多謝泉南翁,神交愿傾倒,聊將一瓣香,寄向君懷抱”之語;布衣逝后,陳獻章又作挽詩以悼之。周瑛未第時受學于陳真晟,舉進士后與陳獻章“上下議論,然瑛以居敬窮理為鵠,白沙之學有所不契。”《明史》亦載:“獻章之學主于靜,瑛不然之,謂學當以居敬為主,敬則心存,然后可以窮理。”
《明史》稱:“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余裔……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嘉、隆而后,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學術風氣變遷在漳州也得到體現。白沙弟子湛若水(1466~1560,號甘泉,廣東增城人,與王陽明共同推進了當時的心學思潮)與漳州士人關系亦極密切,詔安陳鳴球(字舜夫)“嘗與湛甘泉論體認工夫,謂工夫無處不貫,然下手處不可不知。甘泉大嘆服之。”漳平曾汝檀受學于湛若水,知撫州時首建陸象山(九淵)、吳草廬(澄)、吳康齋(與弼)三賢祠。李世浩(字碩達)早年從學于蔡清,后司教南海,“講論王陽明、湛甘泉合一之學”。龍溪施仁則“講明正學,以姚江致良知之說為宗”。上述漳州學者在理學與心學間的抉擇,正是嘉、隆以后心學流行的反映,《漳州府志》為此聲明:“有志斯道者,知稟北溪之為是,則知從姚江之為非。”而前文亦已言及黃道周對朱陸異同的一些評價;出于朱子學的立場,黃道周本來對王守仁(1472~1529)心學持有異議,但對王守仁困守龍場、最終悟道的過程亦有獨特理解。
可見,在心學盛行的明代中后期,漳州理學或多或少也受其影響,并適時地作出調整。觀《閩中理學淵源考·嘉隆以后諸先生學派》,主理學者與主心學者各有其人。程朱與陸王二者其實只是儒學的“內部矛盾”,如馮友蘭先生所說:“戰國時有孟荀二派之爭,亦猶宋明時代新儒家中有程朱、陸王二學派之爭也。”如何融通二者,漳州學者作出了有意義的嘗試。
蔡世遠康熙《漳州府志》“序”云:“維漳建郡,始于唐初,僻陋涉海,然山水峭冽,郁積雄奇。有宋朱文公蒞郡以后,陳北溪、王東湖兩先生親承其統緒,道術既一,禮法大明;勝朝陳剩夫、蔡鶴峰等又起而庚續之;沿及明季,周忠愍、黃石齋、何黃如諸公,氣節文章尤巋然為天下望,流風余韻,至今猶存。”概括了朱熹知漳后漳州理學的大致發展脈絡。總之,作為理學集大成者、朱子學開創者,朱熹對漳州理學的影響至為深遠。朱熹知漳與漳州理學及閩南理學之發展淵源,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
注釋:
[1](清)沈定均修:《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蔡元鼎》本傳“論”引,光緒三年芝山書院刻本,下文凡未另加注明的《漳州府志》皆指此版本。
[2]《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顏慥》。
[3](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十四《承務郎高東溪先生登學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高登》亦云:“朱子守漳,為作祠堂記,復奏乞褒實祿。”
[4]參見《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十二《清漳陳氏家世學派·廉獻陳和仲先生景肅》。
[5]參見《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十四《承務郎高東溪先生登學派·主簿林實夫先生宗臣》。
[6]《漳州府志》卷四十八《紀遺上·民風》。
[7](明)彭澤修:《漳州府志》卷一《風俗》,萬歷元年刊刻,《明代方志選》(三),臺灣學生書局,1965 年,第 24 頁。
[8]《漳州府志》卷二十四《宦績一·朱熹》。
[9]可參見《宋史·道學三·朱熹》(脫脫等撰:《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第 1448頁,版本下同)、《漳州府志·宦績一·朱熹》、張立文《朱熹評傳》(長春出版社,2008年,第16~17頁)、束景南《朱子大傳》(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91~824頁)等著述所載。
[10]“鄒魯”本孔孟故里,“海濱鄒魯”為海濱文教興盛之地美稱,宋真宗時有陳堯佐《送王生及第歸潮陽》詩云:“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鄉。從此方輿載人物,海濱鄒魯是潮陽。”《八閩理學源流·福州府》亦載:“朱子當時見諸儒輩出,大書‘海濱鄒魯’四大字匾于西關譙樓。”見(清)蔣垣《八閩理學源流》,舊排印本,第23頁。
[11][41][94]皆見《漳州府志》卷首《舊序》。
[12]參見《漳州府志》卷二十四《宦績一·朱熹》;《漳州府志》卷四十八《紀遺上·學校》有朱熹《延郡士入學牒》,對八人學行評價甚高,可參見。
[13]劉樹勛主編:《閩學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65頁。該《朱熹門人錄》據言參考陳榮捷《朱子門人》加以考訂、增補。
[14]清吳宜燮修:《龍溪縣志》卷十五《儒林傳·朱飛卿》,光緒五年補刊本,《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99頁,版本下同。
[15]《龍溪縣志》卷十五《理學傳·王遇》,第 199 頁。
[16]《漳州府志》卷七《學校》。
[17]《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十一《朱子漳州門人并交友》列有10人,為李唐咨、石洪慶、施允壽、林易簡、王遇、黃學皋、宋聞禮、朱飛卿、陳思謙、楊士訓。
[18]《八閩理學源流》,第 53 頁。
[19][23]參見《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陳淳》。
[20]參見《宋史》卷四百三十《道學四·陳淳》(第 1450 頁)、《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陳淳》。
[21]《四庫全書》子部一·儒家類《北溪字義》提要。
[22](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第三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2219頁。
[24]參見《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十八《主簿陳北溪先生淳學派》。
[25]見《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十六《清漳諸先生學派》按語。
[26]《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五先生合傳“論曰”。
[27][85](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傳》前言,中華書局,1974 年,第 7222 頁。
[28]《閩中理學淵源考》“凡例”。
[29]嘉靖《龍溪縣志》卷八《道學傳·劉駟》,天一閣藏本,《明代方志選刊》,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5年。
[30]《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七十九《清漳明初諸先生學派·總憲劉愛禮先生宗道》。
[31]《漳州府志》卷二十九《人物二·胡宗華》“論曰”。
[32]《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八十《州守唐東里先生泰學派》按語。
[33]《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學一·程頤傳》:“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第1442頁。
[34][35](清)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卷四十六《諸儒學案上四·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中華書局2008年,第1086頁,1087頁。
[36]《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一·陳真晟》,第7242頁。張元禎此說固然是對陳真晟的高度評價,但亦應與其對吳與弼的誤解有關。吳與弼以名高見嫉,人多有流言中之,“編修張元楨不知其始末,遺書誚讓,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語”(見《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一·吳與弼》,第7241頁),故“不可見,亦不必見”之語其來有自。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可參見《明史》卷一百八十四《列傳第七十二·張元禎》,第4879頁。
[37](明)陳真晟:《陳剩夫集》,商務印書館,1935 年,第 23 頁。
[38]《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八十一《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學派·丁迂峰先生世平》。
[39]《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八十一《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學派·郎中林蒙庵先生雍》。
[40]故《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五十三《布政周翠渠先生瑛學派》稱之為“莆中先正”;《八閩理學源流》則將其歸于“興化府”(第 68 頁)。
[42]《四庫全書》集部六·別集類五《翠渠摘稿》卷四《題嘉魚李氏義學》。
[43]參見《漳州府志》卷首《舊序》之陳洪謨(正德)《〈漳郡志〉序》所述。
[44]《明史》卷二百八十三《儒林二·陳茂烈》,第 7265 頁。
[45][70]《漳州府志》卷三十《人物三·蔡烈》。
[46]《漳州府志》卷三十《人物三》五人合傳“論曰”。
[47][79](明)黃道周著,(清)陳壽祺編:《明漳浦黃忠端公全集》卷首《漳浦黃先生年譜》,道光十年刊本,以下簡稱《黃漳浦集》。
[48](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卷十一《壬午應詔封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42頁。
[49]《黃漳浦集》卷二十八《鄴山祀諸賢文》。
[50]可參見《黃漳浦集》卷二十八《大滌書院告李忠定公、朱文公文》、卷二十四《大滌書院記》、《大滌書院后記》、《大滌書院三記》、卷四十九《大滌空山初宿李忠定公朱文公祠四章》等。
[51](明)黃道周:《榕壇問業》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
[52][74]《榕壇問業》“提要”。
[53]參見《黃漳浦集》卷二十四《與善堂記》。
[54]林魁字廷元,龍溪人,弘治壬戌進士,自幼博聞強記,肆力《墳》《典》;為官有善政;乞休歸,為德于鄉。詳見《漳州府志》卷三十《人物三·林魁》。
[55]《黃漳浦集》卷三十《朱陸刊疑》。
[56]《黃漳浦集》卷二十四《大滌書院三記》。
[57][58]《黃漳浦集》卷首。
[59]《漳州府志·序》。
[60]《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八十三《黃石齋先生道周學派》。
[61]傅小凡、卓克華:《閩南理學的源流與發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
[62]陳來:《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544頁。
[63]《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八十一《嘉隆以后諸先生學派·縣令林復夫先生一陽》。
[64]《漳州府志》卷首《康熙志征啟》。
[65]《閩中理學淵源考》原序。
[66]《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十一《朱子漳州門人并交友》按語。
[67]《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十八《主簿陳北溪先生淳學派·特奏潘叔允先生武》。
[68]《漳州府志》卷三十《人物三·周瑛》。
[69]《漳州府志》卷三十《人物三·林祺》。
[71]《明史》卷二百七十六《列傳第一百六十四·何楷》,第7077頁。
[72]《黃漳浦集》卷首《漳浦黃先生年譜·三十三歲》。
[73]《榕壇問業》卷八。
[75](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五·集部二十八·別集存目二《陳剩夫集》,中華書局,第2401頁。
[76]《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八十《州守唐東里先生泰學派·侍郎謝重器先生璉》。[77]《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一·蔡烈》,第 7236 頁。
[78]《漳州府志》卷四十九《紀遺中·周起元》。
[80]《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一·陳真晟》,第 7242 頁。
[81]《漳州府志》卷三十《人物三·陳真晟》。
[82]《漳州府志》卷四十八《紀遺上·藝文》。
[83]《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五十三《布政周翠渠先生瑛學派》。
[84]《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一·周瑛》,第 7253 頁。
[86]《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八十一《嘉隆以后諸先生學派·陳欽齋先生鳴球》。
[87](清)蔡世紱修:《漳平縣志》卷八《人物·理學·曾汝檀》,民國廿四年重印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261頁。《漳州府志》卷一《建置》載:“大歷十二年割汀之龍巖縣來屬”;“成化三年析龍巖地置漳平縣”。而就漳州理學的歷史敘述而言,龍巖、漳平二地亦應論及。龍巖明代有黃芹(字伯馨)、邱嶸(字天立),漳平則有宋劉棠、明曾汝檀等理學家。《漳州府志》卷三十《人物三·陳真晟》云:“真晟生于鎮海,遷于龍巖,晚定居漳之玉洲。”《龍巖州志》載,“會漳平新設縣,教席缺,當道以禮聘署教事,即以程朱學為教,士化之。”(卷十二《人物志上·理學列傳》,光緒十六年重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故陳真晟對漳平一地之文教影響頗大。
[88]《漳州府志》卷二十九《人物二·李世浩》。
[89]《漳州府志》卷三十《人物三·施仁》。
[90]《漳州府志》卷三十《人物三》陳鳴球等傳后“論曰”。
[91]據洪思說:“黃子學善朱子,素不喜文成良知之說者。一日在榕壇作《平和文成碑》,謂文成‘獨于文字散落之余,豁然神悟,今其學被于天下,高者嗣于鵝湖,卑者溷于鹿苑。天下爭辯又四五十年矣,然于文成所以得此,未之或知也’。門人因問:‘文成良知之說著于海內,今謂其“所以得此未之或知者”,何也?’黃子曰:‘文成自說從踐履來,世儒皆說從妙悟來,所以差耳。’”(《黃漳浦集》卷二十一《王文成公集序》洪思按語。)
[92]《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八十一《嘉隆以后諸先生學派》所列五人中,林一陽、陳鳴球學術傾向已如前述,紀孚兆“以程朱為的”,高則賢長于程氏《易傳》,潘鳴時則問學于陽明弟子王畿、錢德洪,“歸來,自以為有得”。
[9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中華書局,1984 年,第 35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