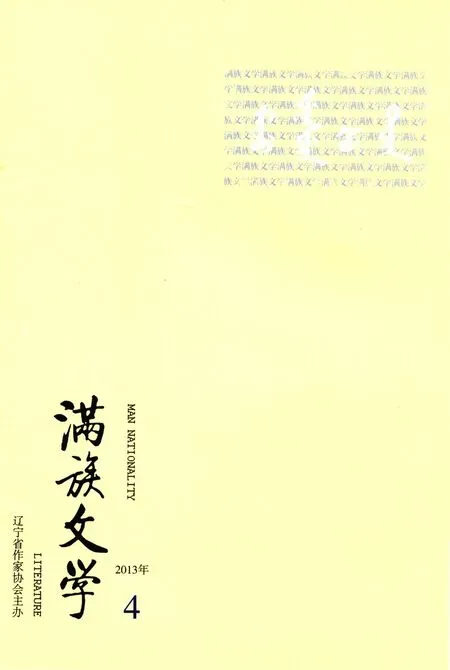廣州滿族墳場嘆情說事
〔滿族〕沈延林
癸巳年清明期間,作為廣州滿族歷史文化研究會新當選的副會長,我首次到麓湖邊的廣州滿族墳場值班。那幾天,廣州下起了大雨。然而雨再大,也擋不住滿族掃墓的隊伍來到墳場。
廣州美術學院著名滿族畫家關悅老先生來了,廣州滿族美女形象代言人茹櫻來祭祀她的巴雅喇故老了,李躍副會長來看他的祖先了,文靜副會長也來看她的列祖列宗了,嘉祥副會長告訴我,他姥姥弟弟的墳塋已經供上了祭品……更多不知道姓名的滿族同胞走進來了,來看望沉睡這里幾百年的祖先,那些埋在這片土地下的曾經活生生的滿洲八旗子弟兵……
二百五十八年前的南粵來了滿洲八旗兵,《駐粵八旗志》記載:乾隆“二十一年,第一起滿兵到廣,二十三年,二十四年,第二起,第三起滿兵到廣,前后共到五百名,不敷操防,三十年第四起另戶滿兵二百五十名到廣,三十一年第五起另戶滿兵二百五十名到廣。京旗再難調,三十二年乃調天津滿兵五百名,陸續到廣,以足一千五百名定額”。他們的后裔于德民(裕糊魯氏)先生告訴我:他考證自己的祖先是乘船走江河來的,從大運河到長江,再入洞庭湖或鄱陽湖轉到其他河流,再到北江或西江到珠江,當然也有可能走運河至長江至海,再進入江河,最后在天字碼頭附近登岸。我認為,既然是分六批次來,也許出發地或京旗或通州或天津衛各不同,走的路線也會不同。但都是從嚴寒的北國來到炎熱嶺南,帶著家眷和工匠。廣州滿洲瓜爾佳氏與全國滿族姓氏一樣都是第一姓氏,在這支南下隊伍里也是大家族,有瓜爾佳·佟梓、有瓜爾佳·京文、有瓜爾佳·賞那哈、也有瓜爾佳·那木金布等等,八旗都有瓜爾佳。隊伍里還有小伙子舒穆祿·穆升額、有快樂的薩克達·遮克敦、有幽默的完顏·全德、有老成的富查·朱爾杭阿、有謹慎的鈕咕嚕·善德,還有尼瑪察姓氏的一等藤甲兵珠成額……他們是最早落戶廣東的滿洲族祖先——他們都叫“落廣祖”,還因為漢語“下”的粵方言讀音即“落”。
無論怎樣的南下路線圖,他們都是艱難地應對季節突變,從白雪皚皚的雪原來到這個冬季都盛開鮮花的亞熱帶地方,那是怎樣的一個轉換,我實在不知道他們的雙足、他們的兀喇子鞋履會怎樣的不適應。于是想到上個世紀我的參加四野軍團43軍128師383團的父親,來自安東省安東縣小甸子紅旗溝三道林子的八旗后裔,背著斗笠扛著機關槍,戴著棉帽穿著棉衣踩著防寒老棉鞋從東北打進暑天廣州、打到盛夏的雷州半島和廣西十萬大山追逐土匪時,甚至解放熱帶海南島時,是不是也是這樣狀況。
那些滿洲落廣祖們來到的新地方是南海縣和番禺縣之間的地域,那地域叫廣東省城,或者叫廣州府的治所。那時城外越秀山叫觀音山,那時的麓湖公園就是荒野山麓野湖。那時還沒有廣州大都市,清代省城最高的地方就是觀音山,除城內文武官員的府邸,山下建筑如今日廣州的工棚區。
那些滿洲落廣祖們于是開始守衛著大清朝陸地疆域的最南部、守衛著南海邊的商業水道、守衛著“湖廣熟天下足”的大清國糧倉、守衛著遠離“京師”容易為“賊人所乘”的南粵。
年復一年,落廣祖們完全沒有做好久居異鄉的心理準備,他們想家,想念家鄉“臘七臘八,凍掉下巴”的冬季的刺激寒風,想念家鄉那踩著就會嘎巴響的厚冰雪和年三十晚上杠香的秋子梨、酸湯子和血腸,想念家鄉“七九河開、八九雁來、九九耕牛遍地走”的場景,想念家鄉的野蒜、刺嫩芽和飛龍,也想念家鄉桀驁的海東青和薩滿跳神的舞姿,更想念家鄉的黑土地。朝廷說:國家統一和社會安定后就會安排你們輪崗的,新一批滿洲八旗子弟一定會前來替換你們的,你們就會回到關外,回到家鄉。但是,朝廷食言了。因為,無兵可以替換啊!國家那么多的邊防和海防、那么多的重要部門,滿洲軍隊如何能抽出多余的替換呢?落廣祖們等不到那天了,他們紛紛走進了衰老和死亡。他們一批批地倒下,合上雙眼、停止喘息,沒有家鄉的玉米小米查子、也沒有粘豆包,臨終只有餃子就南方涼茶送行。鑲紅旗的舒穆祿家族的穆升額倒下了、正黃旗的佟佳哈喇的五達色倒下了、鑲藍旗瓜爾佳的伊凌額也倒下了。正紅旗瓜爾佳的那木金布也倒下了。石刻的墓碑證明:埋葬瓜爾佳·賞那哈的是他兒子發洪阿,埋葬發洪阿的是他兒子花里雅孫(滿語的意思為“和諧”)。尼瑪察家族埋葬珠成額的是他的兒子二等藤甲兵依隆阿,埋葬依隆阿的是他的兒子三等藤甲兵巴彥布,薩克達姓氏埋葬敦氣的是他兒子八十一、埋葬八十一的是他兒子魁安。前廣州滿族聯誼會副會長佟順先生祖先五達色被他的兒子莫克登布埋葬了,埋葬遮克敦的就是他的兒子八旗戰士倭什科,而倭什科也永遠地躺在了南方四季花兒不敗的丘陵上,山野還彌漫著熱帶腐殖質的異香。
于是朝廷又改口說,你們生不在家園、死必歸鄉土。我朝保證你們身后的骨殖一定會送回家鄉安葬,駐粵八旗志里就說“康熙二十三年舊例,凡駐防各省官兵本身物故之后,家口俱令來京,……病故官兵之妻子若撤回京師,贍養無資,然仍不許在彼處安葬。”最初確實有一些骨殖送到京師安葬,也沒有送家鄉。但后來朝廷再食言,駐粵八旗志記載著大清國“中央文件”精神:“先是,廣州八旗官兵歿后,五載一次運柩回京安葬。及至滿、漢合駐,因運柩維艱,奉旨著在駐防官地安葬,以便祭掃。二十一年九月,暑將軍李侍堯特委吉隆阿偕漢軍協領舒九思擇地為旗塋,后于大東門外勘得蟠松嶺、駟馬崗、官路、東碑亭、西碑亭等處無稅官地,約八十九畝零,堪做旗塋,請移知督撫立案,俾免爭訟。滿漢八旗。沐生順死安之惠矣”。停止回送亡故的八旗子弟們的骨殖,就地安葬的原因是滿漢八旗合駐廣州后,需要運送棺材不方便。康熙二十一年來到這里的遼東漢軍八旗可以歸葬北京,滿洲八旗到達后逐漸不允許。于是駐粵滿洲八旗男丁們一代代地出生在廣東省城,一代代的承繼父業當兵吃糧,一代代地最終埋葬廣州府城的郊外地方。
廣州滿族的傳統墳地其實還有多處地方,關景鴻家譜告訴我們,他的歷代八旗祖先埋葬地點不同,如高祖阿勒京阿葬于“小北寶鴨池”,二高祖阿布湯阿葬于“小北橫窿”,三祖恒康與妻子倉氏同葬“飛鵝嶺”,“三叔音德賀”與“四叔格得賀”同葬“金臺嶺”,其落廣祖的墓碑在大北門外的“磨盤崗”。從舒氏族譜發現,他的家族落廣祖穆升額葬于廣州大北門外小鹿鳴崗、他的落廣祖妻子關氏于乾隆二十七年葬于北京平則門外二里溝,說明關氏是在穆升額北京駐防期間去世的,也說明穆升額不是乾隆二十四年的第三批之前離開北京的,而是乾隆三十年或三十一年的第四批或第五批離京,也不是三十二年從天津出發,因為在平則門外二里溝安葬妻子才從北京出發。當穆升額等滿洲八旗到達廣州才知道,漢軍正開始建滿漢旗塋,滿洲八旗將無法再歸葬京師,所以穆升額只能夫妻兩地分葬。于是其二世祖七十八也葬于廣州大北門外小鹿鳴崗,妻子吳扎拉氏葬于大北門外銀魚崗,三世龍祥葬于小北大西竹,三世叔祖特克慎布葬于小北雙塔,四世噶爾薩葬于小北獅球,五世錫蘭葬于小北小鳳三臺嶺,六世裕厚葬于小北獅球。盡管都埋在小北,地點也不同。何況大北、大東門?
辛亥事變那年的革命黨在武昌推翻了當地的清軍政機關統治,廣州滿漢八旗料定無法與其PK掰腕子,乃與革命黨談判,滿洲派出舒穆祿·穆升額的后代舒穆祿·裕厚先生等人洽談,要求不戰不辱、保護滿洲利益,當然要求包括滿洲先人墓地,于是“和平易幟”承認共和。然而在此前,革命黨史堅如用二百磅炸藥暗殺兩廣總督、滿洲人德壽未遂。除了孚琦和鳳山等幾個將軍被革命黨暗殺,以及化州等外地旗人官員全家被殺外,廣東省城的滿洲八旗幾乎沒人在辛亥事變中死亡,盡管如此,必須要提到使孚琦致死的溫生才臨終說的“吾決心先殺滿官、再殺滿族”的話,言之在耳啊,廣州滿洲們能不擔心革命黨想殺自己的想法嗎,但畢竟沒再死人,值得慶賀。裕厚先生的后代肇蘇先生跟我談過他的爺爺當時選擇“談判”的做法及一些滿洲族后人對為“投降”做法不理解的議論,我表示,裕厚先生的功勞絕不可以否定,那是必須的抉擇。但滿洲八旗駐軍還是被戲弄了:先被改編粵城軍,再被集中繳械,接著再遣散,活著的絕大多數滿洲八旗子弟們失去了作為“鐵桿莊稼”職業的固定收入,被社會歧視,承認自己是滿洲者就無法擁有體面又養家的工作,同時八旗駐軍的旗產被視為公產,必須贖買才可以繼續居住。當兵的廣州滿洲們哪有自己的儲蓄,于是被“革命政府”和“革命黨”掃地出自己居住幾百年的家門流落街頭,于是病死餓死和凍死的消息出現在驕傲的八旗子弟后續新聞聯播里。從此廣州“滿洲們”低下自己的頭顱,夾著尾巴做人,從事最底層最卑微的工作,茍且偷生,溶化在廣州土著番禺南海人蕓蕓眾生中間。必須說明,廣州駐防八旗兵與全國所有滿洲八旗兵在辛亥事變之后的政治生態環境和經濟生態環境都一樣,與裕厚先生當年的談判無關。
活著的廣州滿洲八旗們幾乎都被社會拋棄,死去的先人墳頭豈能再有風光的祭祀儀式,據說辛亥后滿洲墓地確實“骨骸遍地”!
在如今廣州滿洲墓地,我發現埋葬于1911-----1921十年內的墓碑幾乎沒有,即使有也是簡單名字,而沒有光耀的“鑲黃旗滿洲”、“正白旗滿洲”和“鑲藍旗滿洲”文字了。因為那個時候的“滿洲們”被逐放被唾棄,“八旗”無法保護自己,還帶來厄運。死就死了,草席一裹隨處埋葬,哪里是沒有主的土地,那里就可以掘坑,墓碑估計也沒有。漢軍八旗本來屬于滿洲共同體成員,當年漢軍李侍堯將軍為滿漢勘定的八旗墳塋,應是八旗的“旗塋”,而不分滿漢軍各自的“旗塋”。但在辛亥大事變后,廣州漢軍幾乎無歷史記載有人承認自己的“滿洲”身份,幾乎對滿洲八旗的稱呼也是“你們滿洲人”。于是,以后的廣州漢軍后裔復身“漢人”中,盡管我認識部分的廣州漢八旗子弟如今埋怨滿八旗后人不認同他們,但是自己的祖先在“患難時刻”為什么不做身份上勇敢的擔當呢。所以,廣州漢八旗早就跳出“滿洲共同體”之外,換取“新生”,喪葬也不與滿洲八旗為伍,白云山上還可以找到這些旗人孤獨的墳塋,包括當時漢軍八旗協領的“劉紹基將軍”墳。
民國至解放初,廣州城郊區滿洲八旗墳塋高高的荒草啊,淹沒了墓碑。墳場里的《廣州滿族墳場建立過程》里記錄著:“辛亥革命后,滿族受著壓迫和歧視,該墳地(指的是大東門蟠松嶺和駟馬崗和北郊的滿族先人墳場)更無人使用,以至不復存在”。廣州滿洲八旗們繳械后,因為孫文革命的發展而恐慌而大逃亡,尼瑪察·珠成額“落廣”時居住在光塔街的同德新街八旗鑲紅旗兵營的今滿族小學,其后代因為家庭房子被革命政府充公,全家逃往韶關,直到日本入侵后才再從韶關回到廣州。世居廣州的許許多多滿洲男人無法回到幾千上萬里的山海關外的滿洲故地,他們根本不熟悉幾百年沒有接觸的家鄉,能去哪里?有點辦法的選擇到香港,大多數窮困潦倒者選擇在廣州賣菜、補鞋等最簡單的工作,或選擇到廣州城附近農村謀生。他們改姓易族,從此成為漢人的一員。省城許許多多滿洲姑娘遠嫁順德、中山和南海番禺鄉下,成為漢人農民家庭的媳婦,因為她們不愿紛擾的民族之爭,只要安居安全和安定。一時,廣州滿洲八旗軍民后裔人口頓減。因為廣州滿族都會說一口流利的廣府話,唱一段標準粵腔,于是廣州滿族成為地道的廣州人的語言“祖宗”,說起來,粵劇名伶郎筠玉稱雌嶺南,誰人知道她的落廣祖就是說著“米尼格布 伯 善德 散木比”(我的名字叫善德)滿洲語的鈕轱轆善德!
再后來,那是五十年代,汪宗猷老會長乘抗美援朝勝利的呼聲,乘著各族人民一致團結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呼聲,以中國人民和平委員會廣州滿族支會負責人的名義,要求重新劃土地給廣州滿族以安葬滿洲八旗祖宗的墓地,得到政府批準。墳場內,由汪宗猷撰稿、潘阜民書寫的《石刻碑記》記載當時批準的墳場:“方向坐西南向東北,面積二千四百平方公尺,以作安葬先人骨骸之所。”
麓湖杉窿山地新墓地明確后,廣州殘留的滿洲人把大東門蟠松嶺和泗馬崗和北郊的滿族先人骨殖遷到麓湖新墳場,這就是現在的廣州滿族墳場。
如今的滿族墓地集中著廣州滿洲八旗的歷代先人,如果考據墓碑,可以寫出一段段歷史篇章。這里安葬的最大的官位頭銜的墓碑記錄是富察氏家族的二品級別的關姓夫人,當然她先生就是二品官員“武功將軍”富察哈喇松福。松福是富察家族的七世,該家族還未南下廣州時,始祖額楚和第二代額蒙額、第三代瑪穆善都是一品官封職,他家第四代的薩穆哈還擔任清朝的禮部尚書,按照清朝文官級別,尚書是“從一品”官。廣州滿族富察氏的這支人的祖先從一至四代均為一品高官,按照今日我國行政待遇,富(傅)察氏家族四代都有“黨中央國務院”級別的,但這些高官的墓碑都不在廣州滿族墳場,因為該家族第七代的松福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到達廣州,最后一批滿洲八旗駐防軍,他是隨同兩個哥哥松祿和松齡來戍守廣州,他們三弟兄才是該家族的落廣祖。按照清朝職官待遇,武將的駐防副都統為“正二品”、駐防協領為“從三品”。松祿和松齡均為三品軍官、而最小的松福為滿洲協領和“祀名”副都統,本人記得《駐粵八旗志》記載的鑲白旗的松福在乾隆年間一直都擔任協領,死后給予“祀名”副都統也就有了“二品”將軍級別待遇,所以該家族后代傅剛先生,是正兒八經的廣州滿州八旗的“高干子弟”。沙氏家族的亨如的墓碑也寫著“武功將軍”,埋葬時間是光緒二十二年,埋葬者是他的兒子吉勒他渾。但沒有注明“武功將軍”級別待遇,“武功將軍”應該是死后的封號。最早記錄的墓碑是乾隆三十年仲冬吉日被安葬的鑲藍旗敦氣,該家族在乾隆、嘉慶、道光等朝都有先人的墓碑,是最齊全的歷代墓碑。
從墓碑記錄來看,出現頻率較多的廣州滿族的姓氏有:瓜爾佳(關)、佟佳(佟)、完顏(汪、王)、舒穆祿(舒、蘇)、巴雅喇(白)、他塔喇(唐)、那喇氏(那)、伊爾根覺羅(趙)、薩克達(倉)、鈕咕嚕(郎)、裕糊魯(余)、尼瑪哈(于)、洪額奇(洪)、伊克德哩(伊)、希塔喇(希)、扎庫塔(張)、馬佳(馬)、鄂吉氏(鄂)、赫舍哩(何)、庫雅拉(胡)、吳扎拉(吳)、朱舍哩(朱)、那木都魯(南)、董鄂(董)、西林覺羅(黃)、鄂佳(陳)、寧古塔(劉)、伊拉哩(李)、尼瑪察(楊)、郭洛羅(郭)、烏蘇里(武)、顧佳(顧)、溫察氏(文)、哈思呼哩(韓)、果洛羅(高)、周佳(周)、扎思呼哩(賈)、索吉(索)、沙拉(沙)等。雖然有滿族老姓,但光緒年間墓碑多數直接寫漢姓加滿名,如張氏巴依江阿、李氏多隆武,余公伊薩布、郎公扎克丹、關公伊凌圖、鑲藍旗張公和色布、余公扎蘭布、富公達興阿、倉公八十一等等。有的不寫姓,體現滿族稱名不舉姓的特點,如二世祖扎坤奇。還有的墓碑寫“清都倫阿舒君“說明姓舒穆祿,名字叫都倫阿。不少墓碑寫上了自己是屬于哪個旗的,如“滿洲鑲黃旗倭什渾”。姓文的老姓不是文佳氏,而是溫察氏,滿研會辦公室的文淑娥就是溫察氏的家族成員。還有一個墓碑姓氏在《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上也沒有,如佟伊哈喇的,名字叫巴哈布,再注明為佟氏。有的姓氏見于家譜,但不見墓碑,如落廣祖京文的滿洲妻子蔡氏、額圖渾的滿洲妻子珠氏和哈奇先的滿洲妻子沈佳氏都未見有墓碑。有些墓碑為后補的,如乾隆年間的落廣祖瓜爾佳京文的墓碑據說“失竊”,當然在墳場沒有墓碑,民國時期再立碑與其他地方。
從墳場來看,廣州滿族一些喪葬習俗已經漢化,廣州滿族墳場的墓碑多數上面有紅色的圓形,據說是學當地漢人的標志。
廣州前民委主任關培的祖先也安葬這里,他家有清武舉人的石碑,滿八旗與漢八旗在進士狀元的考試中,最有區別的就是滿洲的武舉人勝過文舉人。我還記得松福將軍的孫子舒泰也是武舉人,但也沒看到墓碑,還有廣州市郵政局的楊世民先生和他侄女楊偉萍小姐的祖先富琳是御點第七名武舉,他的兒子德壽是光緒元年乙亥恩科的武舉第十名,《駐粵八旗志》里都明確記載,不知道這個武舉人德壽與辛亥年間那個德壽將軍是否同一人。墳場沒有看到德壽的墓碑,很遺憾。
廣州滿族墳場埋葬的主要是滿族人,也有少量漢族,當然是早期先埋葬在那里的漢族。廣州與北方不同,廣州滿八旗后裔與廣州漢八旗后裔在“滿族”概念上劃分得很仔細,廣州漢八旗不算滿族,最多就“旗下人”,這是廣州漢八旗自己在歷史關鍵時候的選擇。而爺爺或奶奶是滿八旗的,后裔是滿族。姥姥或姥爺是滿族的,后裔也是滿族。當然爸爸是滿族兒女是滿族,媽媽是滿族的后代也是滿族。無論男女雙方誰是滿族,后代就是滿族,這很正常,父母雙方的骨血都構成后代骨血。廣州滿族在這里不糊涂,滿族男女的后代都是我族成員。
姚大姐退休多年也是熱情人,今年也在墳場值班志愿人員,同時祭祀自己的滿族先人墓。她告訴我,姚章甫生前掌管孫文革命黨推翻清政府的金庫。革命黨人姚章甫先生一生致力于“革”清朝政權的“命”,他的兒子娶了廣州滿洲姑娘,應該是“革”滿洲“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他兒子事實上就成了滿洲女婿,生下姚章甫先生的孫子或孫女,問題就出來了,這個生命是造出來了還是革掉了呢?始料不及啊,其孫子輩們選擇族份為滿族。按照滿族墓場有關規定,滿洲媳婦和女婿可以同葬在滿族墳地。姚先生也隨同兒子及滿族兒媳被孫子們葬在廣州滿族墳場,真是“無言的結局”。“姚總管”為孫先生民族革命提供“財政營養”的一生,不僅“革命”事業未競,最終為廣州滿族延續了民族的部分生命,而自己也被埋在滿族人的墳場。那滿族姑娘就是姚大姐的母親,孫文革命黨著名追隨者是姚大姐的親爺爺,滿族孫女說的這個故事,孫文先生當然也不知道,我為姚大姐謳歌,其實該表揚她的革命黨爺爺。
走進愛新覺羅(金)·寶森題寫的滿文牌坊門,進入墳場,滿洲先人的墳頭一座座地列在廣州城麓湖一偶,左邊密密的寫著“左01、左02……”層疊上去直達山頂,右邊也寫著“右01、右02……”密密的疊上山去,汪老會長用滿文標志的許多小石碑圈定了墳場的四周范圍,據說可以再用幾十年、放置幾百座墳塋,但由于白云山管理局反對廣州滿族在墳場內繼續設新墳,廣州滿族歷史文化研究會只好采取“掛榜”形式安葬后入土之人,也就是說新去之人只能在墳場有故人位置,才可以“掛”進去。
兩年沒有來墳場了,因為重新修葺了墓道和紀念碑座,墳場漂亮了,在那座紀念碑前,有兩座花籃,分別是廣州滿族歷史文化研究會的和香港滿族族胞敬獻的,兩條鮮紅的鍛帶十分醒目。穿行在大雨后的墓與墓之間的過道,見到了許多廣州滿族名人碑:汪老前會長家族墓地、前滿族小學校長郎秀萍伉儷的墓、前廣州滿族聯誼會副會長關國華的墓。汪老就是廣州滿族小學、廣州滿族聯誼會的創始人汪宗猷老先生。1919年汪宗猷出生在廣州滿族鑲紅旗完顏氏八旗兵家庭,辛亥事變后,八旗兵家庭生活艱辛,汪老童年跟隨父親賣魚、賣雞蛋。無論家境如何清貧,少年的他都堅持在惠福西路的一個只有十名學子的“卜卜齋”上學,抗日戰爭勝利后,汪老和其他滿族鑲紅旗知識分子,目睹廣州滿族失學兒童占學齡兒童49.56%,非常痛心,大家決定征得該旗代表和管祠人汪玉泉同意,將位于光塔路89號的鑲紅旗“宗祠”作為校舍。1946年6月向廣州市教育局申請開辦,校名定為“廣州市私立國光小學”,汪任校長。1950年7月12日,廣州市人民政府教育局批示:準予廣州市私立國光小學重新備案,批準汪宗猷繼任校長,1954年11月,經過商議,作為學校領導人的汪主動將滿族國光小學全部財產獻給政府。自此,學校由廣州市教育局接辦,并將校名改為“廣州國光小學”。1956年8月,廣州市教育局接受學校及滿族人民的意見,將廣州國光小學命名為“廣州市滿族小學”,據說是全國第一家滿族小學,校長仍是汪老。盡管后來的滿族小學校長更換多人,但開山者汪老。1984年9月汪老創辦了全國第一個滿族聯誼會并擔任會長,后改廣州滿族歷史文化研究會,為廣州滿族人民服務到90多歲才從會長位置上退休。汪老被稱為廣州滿族歷史的活字典,出版過《廣東滿族志》、《廣州滿族史》和《駐粵八旗》等多部廣州八旗駐防歷史的書籍,還編寫《滿族通訊》雜志及組織廣州滿族老人佟直臣、舒仲璣、關興、關漢宗、李國、趙全俊、武耀材、郎珍、余秀貞、關美、傳紉芳、關鳳臣等編撰《廣州滿族文史資料》多集,這些老人如今多數都埋在這個墳場里,但留下珍貴的史料彌為珍貴,汪老被中央民族大學聘請為客座教授。廣州滿族墳場的建設與汪老一生努力分不開。看著汪老的家族墓地,我似乎見到那個跋山涉水來廣州駐防的汪氏落廣祖完顏全德先生,想到汪老為民族工作終身不輟、勤勤懇懇的摸樣。關前副會長生前是個低調的削瘦的小老頭,曾經是廣州業余大學副教授,跟隨在汪老身邊隨時做談話的補充。滿研會的老前輩為廣州滿族的管理、聯誼和研究活動提供了很好的平臺。
墳場很擁擠但不亂,在墳場的左邊,還新設了“無主”滿洲墳和集體墳,盡管“無主”但墳是有主的,如“無主”祭祀的墓碑名字寫著“滿洲鑲黃旗倭什渾”、“清都倫阿舒”等等,他們整齊的排列,有幾十座墓,在挺整潔的花草間和寧靜的松林下,那氣氛令人肅然、肅穆、肅靜。
從廣州滿族墳場的治理和滿族民眾掃墓的盛況,感受廣州滿族歷史文化研究會的工作果實。廣州滿族歷史文化研究會工作主要兩大項:一是戶籍滿族的管理和聯誼活動,二是廣州滿族的研究活動。民族聯誼包括:滿族中小學生的獎勵,凡是三好學生的廣州滿族中小學生都可以到研究會領取獎金。每年對貧病的廣州滿族老人慰問、面向滿族青年和婦女的聯誼活動,如民族體育和文藝活動。開展面向滿族青年的滿語學習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動。滿族研究主要內容是落廣祖文化研究、廣州八旗駐防史研究、廣州滿族人物研究等等。研究的載體是《廣州滿族》雜志。還承擔部分管理工作。市民族宗教局部分業務下放后,協助該局進行民族社團和戶籍民族管理,包括民族團結教育、和諧文化教育等等。墳場管理是最需要重視的活動,管理和修繕都是研究會組織進行的,墳場地處白云山保護區內,與白云山管理局打交道是研究會經常的業務之一,墳場如今的管理得到滿族同胞們嘉許。現任會長為遼寧省岫巖出生成長的金玉階先生,鰲拜后人,大學畢業分配到廣州市工作,在大學校長位置上退休后被選舉接汪老的班。廣州滿族歷史文化研究會的格言:做廣州滿族的娘家和精神家園。
幾年來,在廣州滿族歷史文化研究會的治理下,墳場淹沒腳脖子的雜草被鏟除了,為來掃墓的滿族人民消除了蛇蟲叮咬的可能。在墳場的長尖石碑前,是仰慕前人的石筑方型基座。當年到達廣州的滿洲八旗官兵1500人,加上家屬應該超過6000人,墳場的墳塋原來只有1911穴,據說再次搜尋挖掘,目前超過2000座墳,所以還有許多的滿洲八旗的墳早已不知道去向。然而,廣州滿族墳場在全國集中安葬的滿族八旗子弟墓地中都是僅有的。
思著想著,來掃墓的滿洲人越來越多,據說頭天就超過一千七百人,廣州市滿族歷史文化研究會開任何會議和舉辦任何慶祝活動都沒有掃墓的人多,這不需要通知,這沒有福利刺激,因為大家都要看望自己的八旗祖宗安眠的地方,獻花圈添土拔草、獻供品叩首祭酒,說說心里的祝愿和保佑的話,滯留一會、思念一會、流連一會、感受一會、認同一會。
看著他人拉家帶口的祭掃活動,我為他們而心動、情動而感動至激動。廣州滿族以“愛拼才會贏”的人生態度去搏,為自己的八旗祖先爭取榮光。乾隆年間到達廣州的正黃旗的瓜爾佳·佟梓的廣州第二代叫朱達里、三世叫靠山保、四世叫得爾禎柯、五世名字納親布,六世開始姓關。正黃旗的祖先沒有想到第八世出了著名粵劇名伶關楚梅,成為廣東地方劇的翹楚;正黃旗的祖先沒有想到第九世的關尚賢回到家鄉滿洲,擔任東北大學著名教授;正黃旗的祖先沒有想到他們的子嗣關尚慶先生如今在美國休斯敦經商,幾百年前八旗子弟四海為家,現在還是四海為家。正黃旗的祖先更沒有想到他們的子嗣關尚遲是廣州著名的特色小提琴制作大師并成為優秀的企業家,還被選舉為廣州市政協委員和授予全國輕工行業的勞動模范。當然該家族最多的還是默默無聞地為國家做最基礎的事,如廣州滿族歷史文化研究會的關兆福退休前擔任基礎教育教學和管理工作,如今為滿研會文體活動繼續奉獻,我為他的祖先激動和自豪。百年后,這些駐防八旗的后代不忘先人,來祭祀的有大中小學生、有國家各行公務事業的領導、有科學家和實業家、有人民教師、有律師和醫生、有街道大媽、也有……總之來自各自崗位,他們都是廣州滿洲八旗駐防軍的后代。二百多年前,八旗駐防軍身在國家各邊防、江防和海防駐地,而心系萬里白山黑水。他們牽掛滿洲,他們當然也擔心身后,他們無論如何都想不到今日曾孫、重孫和玄孫們的成長和對他們的孝敬,雖然身份已改——不是大清國的步馬甲或者養育兵,但他們都是當今棟梁。
我的祖先沒有在這埋葬,因為我祖先不是廣州滿洲八旗駐防兵,是北京駐防兵和遼東駐防兵。在康熙26年由“京旗”回撥奉天岫巖城三道林子駐防屯墾,1949年劃到安東縣(今東港市),家鄉的祖墳至今還有祖先如“伯成額”們的墓碑。中華56個民族各有各的祖先,我難以于清明日回遼東祭掃我的八旗先人們,然今日于此在廣州滿族墳場值班,我心情同樣和祭祀自己的祖先的廣州滿族八旗后裔一樣。他們都是來自白山黑水,都是一樣在1644年隨同攝政王多爾袞入關的八旗滿洲先驅們。
雨后空氣特別的新鮮,臉上和手臂沾上墳場邊的濕漉漉草葉和竹葉上冰涼的水滴,心情尤其濕漉漉的舒爽,是眼淚是心淚。看著絡繹不絕的掃墓男女,感覺到滿族人氣的旺盛,來的有滿洲兒孫,也有滿洲媳婦和女婿,感覺滿族人不會絕,感覺滿族的血脈會繼續延續下去,盡管這些廣州的滿族都使用粵語交流,但是我相信他們的骨子里、血管里都有民族親情。
想到這里,又一潑大暴雨傾瀉下來了,廣州滿洲八旗百年的熱淚于斯的狂瀉,我能徹底理解,于是寫下這些暢想、懷想和感想文字及標點符號以記之。
歇息吧,廣州滿族的落廣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