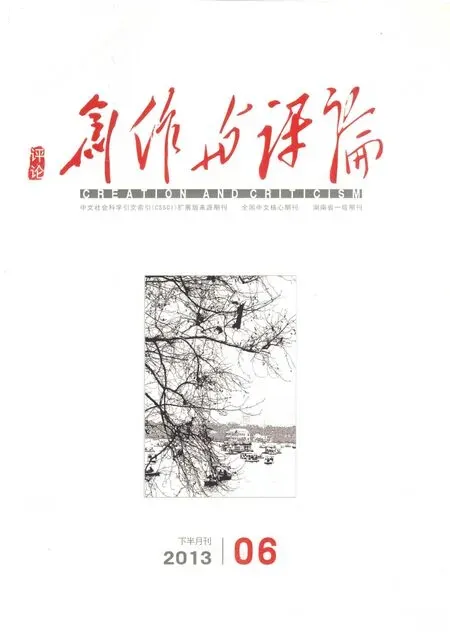尋找有情懷的好故事——電影《一九四二》的審美價值辨析
○ 周思明
一個成熟的藝術家總是不斷變化自己的創作范式,以追求審美藝術上的獨創與新穎。馮小剛近年在電影創作上的“轉型”便是如此。一向以賀歲喜劇示人的他,近年來一口氣拍了好幾部悲劇,繼《唐山大地震》和《集結號》之后,現在我們又看到了《一九四二》。由劉震云編劇、馮小剛導演的《一九四二》,反映的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場災難,中國抗日戰爭處于戰略相持階段,此時河南大旱,千百萬民眾離鄉背井外出逃荒。影片以兩條線索展開,一條是逃荒路上的民眾,主要以老東家和佃戶兩個家庭為核心,展現他們的掙扎和痛苦、希冀和憤怒;另一條則是國民黨政府的當權者,他們對人民的蔑視加深了這場災難,并最終導致自己失敗的命運。
一、好故事與情懷立場
電影《一九四二》呈現了馮小剛一以貫之的民本主義思想與大眾人文情懷。劉震云曾對馮小剛說,好劇本的創作方法不外乎兩種,一是靠一群聰明人坐在賓館里搞“頭腦風暴”;另一種是笨人笨辦法,就是靠兩條腿走出來的,沒有故事,就要到現實中去找故事。于是,為尋找《一九四二》的故事,馮小剛和劉震云帶著一隊人馬,開始了他們的艱苦創作之路。“河南、山西、陜西、重慶……路上這個故事在不斷生長。”對此,馮小剛頗有心得:“走了以后才知道,‘喝口涼水都不餓’這句災民的原話,不是我們在賓館里就可以想象的。我們住當時蔣介石的別墅,也沒想到會是那么簡陋的。《一九四二》怎么變成電影就是要在1942這個年份里尋找。”正因為有了這次的實地考察,才讓劇本成型并愈加豐滿,電影不能讓這300萬人復活,但也許能讓他們的死變得有價值。
劉震云說的這種笨辦法可能耗時很長,但只有這樣,人物和故事才能真正存留下來,電影人物也才能在創作過程中“慢慢生長起來、成熟起來”,這對創作者來說自然很有成就感。在當今互聯網時代,信息已過剩,傳說滿天飛,要編故事很現成,頭腦風暴乃是一種路徑。但是,無論是寫作還是拍電影,尋找真正吸引人感動人的好故事,已成為中國創作群體中一種普遍的焦慮。但除此之外,還有比尋找“中國好故事”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人的情懷與民本立場。一個創作者能否講述一個“中國好故事”,不僅是講故事本身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他的情懷與立場。情懷和立場有了,好故事就有了方向和溫度。
從影視美學角度說,一個電影故事的飽滿程度內涵的寬度和深度,都與創作者的情懷與立場有關小說和電影中的見識,實際來自于創作者在生活中的見識。對生活中每個細節的態度,反映了他的胸懷和見識。中國電影需要逐步培養富有遠見卓識的創作者。應該說,馮小剛在小人物、民間人物的刻畫上有獨到的功力,且駕馭手段也隨著他對這種題材經驗的積累而變的愈加如火純青。
馮小剛是個很有民本情懷的電影人,綜觀他所創作的一系列影片,喜劇也好,悲劇也罷,往往給人以人性的關懷與人生的啟迪。《一九四二》亦莫能外。馮小剛在談及《一九四二》時說:“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災難深重的民族,是災民后代。我們對自己認識不夠,也不愿意認識。這個電影是逼著大家來認識。它在撕開歷史給大家看的時候,依然可以看到掉進深淵里的人的人性溫暖。”長達5個多月的拍攝,對馮小剛來說是禍也是福,“每天那么多群眾演員,100多部車子,在山西的荒山野嶺拉練式的拍攝真的非常疲勞,但是當初真的沒想到這部小說能搬上銀幕,算了結了一個心愿。”
《一九四二》中,由徐帆、張涵予、張默等4個不同人物群體展現4條不同的故事線索,猶如1942年的4個橫切面,展現出“一段被遺忘的歷史,一個必須面對的真相”。《一九四二》不是一部人們常以歷史題材譽之的“史詩”,實話實說,全片沒有詩意,非常粗糙。所有的災民的感情都很粗糙,不是他們不會抒情,是他們沒有心情抒情。所以,電影沒有煽情,抒情的部分不會讓它存在,因為和災民的處境不適合。
二、再現歷史的真實
歷史題材的電影,當然不是歷史教科書,但也不是脫離史實的創作,而是歷史真實與電影藝術的有機結合,因而它的生命是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對歷史題材影視,歷來評論者的意見不一。但總的說,無外乎兩種,或過于拘泥史實,缺乏藝術創造;或離開史實太遠,違反歷史真實。依據筆者的淺見,《一九四二》在反映歷史和藝術創造方而,盡管存在一些遺憾,但從它的主要內容和總的傾向來看,應該說,它比較完整而深刻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并升華到藝術的真實,因而給觀眾帶來許多新的感受,也讓馮小剛們飽嘗歷史題材電影創作的酸甜苦辣咸,看到電影藝術的價值與意義。
《一九四二》拍得很真實,看似平鋪直敘,沒有什么高潮。煽情指數也不及電影《集結號》和《唐山大地震》,鮮有催人淚下的震撼。夾雜著河南方言說出的馮氏黑色幽默風格的對白,有評論者認為有點不合劇情基調,但悲劇的情節仍讓人潸然淚下。在饑餓和死亡面前,人格尊嚴、宗教信仰和國家情懷也許暫且會被擱置。電影中有個情節:因為旱災和兵禍原先的東家后來的逃荒者老范從河南和鄉親們一起往陜西逃難,一路上饑寒交迫,歷時三月到了潼關,最終結局是馬車沒了、錢財沒了、家里的人死的死賣的賣一個個也沒了。孑然一身的他萬念俱灰,逆著逃荒的人流折返河南老家時,有人問:“大哥,怎么往回走哇?往回走就是個死”,老范木然發出“沒想活著,就想死得離家近些”的可憐兮兮的哀鳴。
老范的命運無疑是《一九四二》中的成千上萬逃荒者的一個縮影。災難面前,人的命“賤”得就像螻蟻,幾百萬人非正常死亡的輿論關注度卻抵不上甘地已經絕食七天。上世紀1939年發生的波及豫皖蘇三省的黃河決堤引發的黃泛區水災,影片中講述的1942年發生的河南特大旱災,因為有些久遠,后人可能已然淡忘;但是1962年前后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引發的波及全國的大饑荒,筆者還是記憶猶新且難以釋懷。其實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此類自然災害和人為災難不勝枚舉。樂觀和健忘的人可能會想,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往事不堪回首。民族或者家庭曾經的創傷愈合了再揭開來,為之心疼是在所難免的,讓人傷心落淚悲痛欲絕又是何苦來哉?其實,這是一種糊涂。
吃飽穿暖、安居樂業、沒有戰亂、避免內訌、乃是中國人的夢想,也是人們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和生存權利。但不論是盛世明君還是亂世梟雄,均難能真正實現這個不算奢侈的夢想。饑餓和災荒還有戰亂,幾乎貫穿整個中華民族歷史,在朝代更迭的劇烈動蕩時期更其如此,特別是對于處于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就此意義上,《一九四二》如同余華的小說《活著》,它告訴我們一個樸實的道理:活著,就是幸福。
顯然,《一九四二》是一部“在路上”的電影。主創馮小剛和劉震云采取災民、軍隊、政府、宗教、記者五條線索并行推進。19個主角,50個次要角色,這似乎在戲劇、電影中乃為大忌,而雜多人物之間互不交叉,這對影片的戲劇性美學構建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戰,風險性極高。事實也確如此,多線敘事多少分散了角色的情感力量,讓習慣于追隨幾個人物命運為之喜怒哀樂的觀眾無所皈依。
如果說《唐山大地震》人們看到的是天災,那么《一九四二》便是人禍,古語告訴我們不必“杞人憂天”,但藝術家“杞人憂天”卻是情有可原甚至很有必要。不唯如此,藝術家更應有先知先覺的本領。一個有責任心有擔當的藝術家,其更重要的使命是提醒和昭示人們反思與警醒,體悟佛所說的“無常”。“無常”之前需珍惜,“無常”之后要平靜,用內心平靜的力量,去對待人生中的驚喜或者驚恐。
世界上災難片很多,不同民族對災難片的態度也不一樣。我們這個民族的態度,雖然不必西方那般富于幽默,但也不是完全不懂幽默,不會幽默。一個民族,如果用幽默的態度去對待災難,災難就會像一塊冰,掉進大海融化。馮小剛嘗試用幽默來化解,這與他一以貫之的幽默訴求吻合。他就是這么個人,難怪能和王朔、葛優交成鐵哥們。后者也常常以民間小人物作為自己的表現對象,從不拉大旗作虎皮,虛張聲勢自我膨脹。葛優很少演皇帝,曾經拒絕過此類在別人看來乃千載難逢的“轉型”機會,這與他們的為人個性、美學訴求相匹配。
《一九四二》有故事、有人物、有思考、有審視和批判、有懺悔和救贖,且這一切都用極其平靜、收斂和克制的情緒、手法在呈現,不急不躁娓娓道來,在馮小剛眼中,災難猶如庖丁刀尖帶血的鮮肉,可以輕而易舉的烹飪出鮮美的宴席。災難越大,材料越足,美廚的鍋勺施展的空間也就越大。哭訴、控訴,還是陳述、自省,這是平庸導演與優秀導演之間的不同。馮小剛顯然屬于后者。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信息潮涌,各種各樣多元化創作方法的涌現,現實主義直面歷史與社會的選擇,無疑值得欣賞,這也是人們喜歡馮小剛電影的理由。包括《一九四二》在內的馮氏電影系列,無疑為我們開辟了一片廣闊的影視藝術空間。《一九四二》直面歷史真實,為揭示民族生存的真實境遇而創作,為探討并反省民性與自然、歷史、社會之間復雜關系而創作,為理解民性與人性內在的豐富和繁雜而創作,這是現實主義影視藝術的本質追求,也是馮小剛電影的輝煌所在。
三、尋求最佳演繹效果
拍攝《一九四二》,馮小剛做了新的嘗試:電影粗剪完成后,從大街上找觀眾,每次60個,一共四批,讓觀眾打分,跟觀眾座談,將一直持續到最后的定剪。此外,為了讓《一九四二》獲致最佳最真效果,有鑒于當今影視人物在體形、穿著等外在元素的隨意與虛假(比如舊社會的窮人仍然體態豐滿、穿著光鮮,沒有絲毫“饑寒交迫”的痕跡)馮小剛要求大多數演員都要忍饑挨餓,一方面是從形象上更接近災民,一方面也是為了帶著饑餓造成的眩暈感迅速入戲。劇組拍戲時,演員們普遍都在餓著自己,喝水度日,甚至吃瀉藥減重,不敢去食堂,不敢聞菜香,但凡多吃了一口食物都會感覺到巨大的精神壓力,仿佛離自己扮演的饑民角色遠了一步。最有成效的是張國立,他為這部電影最終減了24斤,像真災民一樣挨凍忍餓,那種感覺真是絕望,但這也是體驗角色的一個途徑,餓得頭暈眼花的時候,甚至都出現了幻覺走路也是哆哆嗦嗦的,但是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地感受到,“人的尊嚴真的是從肚皮開始的。”
影片的成功上映首先得益于小說原著。綜觀中外電影發展史,文學從來就是電影的沃土,成功的電影往往都是“作家電影”或經典名著改變的電影。正如主演張國立所說,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是近些年來他所閱讀的現代作家的作品中,讓他感觸特別深刻的一部。在這部作品里面所呈現的現象、所闡述的問題以及由這些問題引發的反思,讓他頗有觸動。張國立也一直在思考類似的問題,在苦苦尋找這樣問題的答案,他覺得在這篇小說中他找到了一個可以仰望的知己。
在場的生活體驗和歷史體驗,讓電影有了一定的質感。學習莫言,再講一個故事:主創者們在一個教堂遇到一個老太太,她經歷過那段災荒。她告訴演員們,當時有個親戚還沒餓死,被另外一個災民割了屁股上的肉。親戚說,我還中呢,但那個人說,你不中了,就救救我吧。老太太說,從那之后再沒吃肉,也再沒哭過。到了重慶,看到蔣介石當時住的別墅,出乎編導們的意料——太簡陋了,簡直算不上別墅。再想想當時的延安,都特別簡陋。這些,都不是創作者坐在沙發上能想得出來的。后來,《一九四二》的故事不斷豐滿,每個人物都沿著自己的藝術邏輯軌跡在生長。好的人物,它已經有自己的生長之路,這個劇本里的所有人物就是這樣生長出來的。
電影能成功上映,得力于眾人拾柴。用馮小剛話講,《一九四二》這頂大轎子,是一批實力演員給抬起來的。影片中主要角色19個,紛繁復雜的人物線索涉及1942年中國社會的災民、學生、士兵、商人、官員等各階層,選角的標準是要“有默契,不被電影以外的雜音干擾”;具體到每一個角色的挑選,演員本身的質感恰如其分,同時功底扎實。《一九四二》的支柱演員皆為戲骨,因為沉淀多年,所以在《一九四二》中與角色一旦相遇,就迸發出很大的能量和光彩,張國立、陳道明、李雪健、范偉、馮遠征、徐帆、張涵予、張默、王子文,都是不會造成任何困擾且非常投入的或資深或當紅的影視演員。《一九四二》還請來兩位好萊塢大明星阿德里安·布洛迪和蒂姆·羅賓斯加盟,雖然戲份不多,但友情加盟,其名氣顯然可壯電影聲勢。
四、難以避免的遺憾
電影從來就是遺憾的藝術。馮小剛一貫的幽默風格,在這部影片中成了爭議的話題,可謂是一柄雙刃劍。與其它悲劇書寫者不同的是,《一九四二》在講述逃荒災民的故事時,風格并非一味地沉重,而是有幽默的元素在其中,用幽默態度面對災難,其實也是人類生存的一個特質。雖然是災難片,但里面卻添加了一定的幽默成分。對此,馮小剛的闡釋是,“我沒刻意找幽默感,但這個劇本很多段落充滿了歷史的幽默感。”這種在當哭的時候笑一笑,應該謹言慎行,用得好,可能雪中送炭或錦上添花;用得不好,可能會消解乃至顛覆悲劇的氣氛和努力。從爭議看,馮小剛的幽默也許敷錯了藥也未可知。
《一九四二》給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張國立扮演的東家,而那幾個不與情節主線重合的小人物,卻是全片中最搶戲的角色,尤其是范大廚和張神棍,這二位的每一次短暫出現,都如同一個精致設計的小品段子,發散出來的氣場,會毫不留情地掩蓋住主角的光芒。當觀眾看完全片后,即時出現的悲憫會在年末的冷空氣冰鎮之下迅速退回體內,而只剩下對小品短劇津津樂道的回味——這曾經是馮小剛早年喜劇片里最讓他自得的地方,但現在很可能成為讓人尷尬的解讀。這個評價但愿不是空穴來風,電影中范大廚和張神棍出現的地方,是全片中笑場最集中的地方——喜劇的張力在某些片段壓過全片的悲慘氣氛。據說電影上映僅三天,雷人的彌撒曲便在網間傳唱起來。這一點,也許是馮小剛們始料不及的。
應該說,馮小剛是一個有追求的電影藝術家,但他尚不具備思想家的資質,這就決定了其作品《一九四二》的視野所能達到的層次僅是“再現”而非“表現”。作為一個平民導演,他和普通人一樣具有同情弱者、悲憫蒼生的普世情懷,也知曉凡人都善忘,有必要在太平盛世時給予芨芨草民以居安思危的長鳴警鐘,但也僅此而已。接下來該做什么,他就茫然不知所措了。
恕我直言,電影《一九四二》有能力“溫故一九四二”,卻沒能力瞻望2042(未來的泛稱);有勇氣為公眾吶喊“勿忘歷史悲劇”,但沒能力為民眾尋找到一條通往未來的道路——電影的主角踏上的只是一條逃生之路,而不是一條希望之路、光明之路。
應該指出的是,電影《一九四二》寫出了歷史的真實,但在揭示其中更為深刻的來龍去脈、思想內涵和行走方向上,顯得用力不夠,對于我們民族一直以來的超越世俗的夢想,也許創作者有意愿但沒能更生動地描繪出來,沒有在作品中刻畫出偉岸的人格和博大的胸懷,也沒有追問人類靈魂的高貴和浪漫。取而代之的,是對人性和民性的生存層面本能的呈現,對世俗欲望的狂歡性書寫(如面對饑荒人們的自私、偏狹、傾軋、剝奪等等),對歷史現實的表象化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