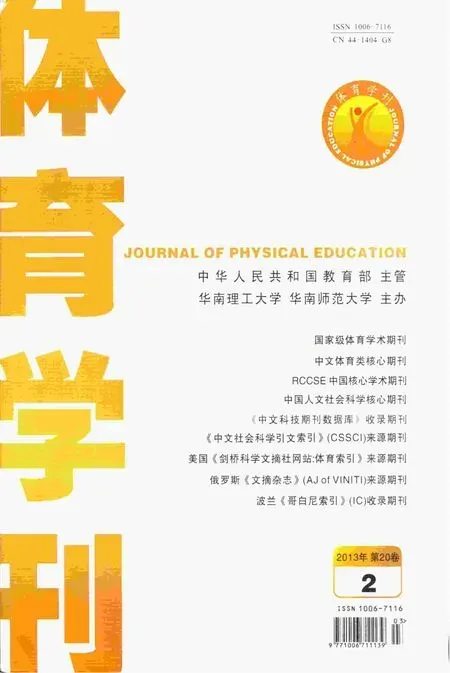武術意境——中國武術藝術理論初探
吳松,王崗,朱益蘭.2
(1.蘇州大學 體育學院,江蘇 蘇州 215021;2.蘇州中學 體育組,江蘇 蘇州 215007)
在我國傳統藝術乃至整個傳統文化中,“意境”這一命題可謂是“說不清、道不明”的深層意蘊,是中華民族在長期藝術實踐中形成的一種審美理想。“意境”之說最早出現在詩歌與散文中,是指作者通過對事物的形象描寫而表現出來的境界和情調,是抒情作品中呈現的情景交融、虛實相生的形象。“唐代王昌齡把詩分為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唐代司空圖提出的‘韻味說’,宋代嚴羽的‘妙悟說’,清代王士禎的‘神韻說’,直到近代王國維的‘境界說’”[1]336等,都是對“意境”的闡述。后來,隨著“意境”說不斷發展,漸漸擴展到其他的領域,如“戲曲、音樂、舞蹈、繪畫、書法、建筑、園林等,均注重創造意境,將意境創造作為藝術追求的極致”[1]340。可以說,作為我國傳統藝術中一種“形而上”的審美形態,任何一門傳統藝術都反映出不盡相同的“意境”內容及特點。武術,作為一項具有鮮明的藝術屬性的傳統文化形態,其“藝術化”的技術形態能夠引發觀賞者產生對武術技擊的聯想或想象,因而也形成了獨特的“武術意境”。在當代武術研究中,盡管也出現了一些關于武術的“意境”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略顯淺顯和空泛,少有人能夠對“武術意境”的概念、構成等內容進行較為細致的解析。因此,本研究借助藝術學的理論,試圖從藝術學的視角對“武術意境”的本質、內涵和特征進行一次探索性的研究。
1 何謂“武術意境”
在藝術學領域中,學者們對“意境”一詞的理解存在不同的表述,例如:蒲震元[2]認為:“意境是特定的藝術形象和它所表現的藝術情趣、藝術氛圍以及它們可能觸發的豐富的藝術聯想與幻想的總和。”成遠鏡[3]則認為“意境是藝術家用心靈構筑的靈性空間,能給人以廣泛聯想與無窮韻味的審美特征,是藝術作品中超越現實時空,富有形而上意味的藝術境界。”而彭吉象[1]335則認為:“意境是藝術中一種情景交融的境界,是藝術中主客觀因素的有機統一。”
從中可以使我們獲得對“意境”本質的把握:首先,“意境”并不是一種客觀事物的存在,而是一種主觀意識的感受。更確切地說,“意境”是在審美活動中由審美主體——觀賞者所產生的一種精神感受。因為“意境產生于藝術審美的過程之中,是審美主體在對審美對象進行觀照時,審美意識高度興奮,完全沉浸在一種精神的享受之中而形成的特殊狀態”[4],所以它是由審美主體依據審美對象在其精神世界產生的一種感受或情感體驗。其次,“意境”是由“意象”引發的一種思維活動的結果。在審美活動中,精神感受或者情感體驗的獲得,無法憑空而來,只有那些“有意味的形式”才能引發審美主體進行的與之相關聯想與想象。而“有意味的形式”在藝術學理論中被稱之為“意象”。因此,“意象”是“意境”生成的基礎。“意象”引發了審美主體在心靈上與情感上的觸動,“意境”才由此應運而生。正如王國維先生所說:“境非獨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的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5]
“武術意境”一詞,是將武術視為一種審美對象,而令審美主體產生審美感受的表述。因為,當武術通過藝術化的形象呈現在觀賞者面前之時,各種形態各異、活靈活現的武術技術動作就“幻化”為一個個美的形象,這些美的形象可以引領觀賞者進入一個充滿無盡想象的藝術空間,通過對各種武術形象的認知和理解獲得關于武術技擊的想象與聯想,這種凌駕于武術形象之上的藝術體驗就是“武術意境”所指向的內容。基于此,我們可以將“武術意境”界定為:通過特定的武術形象而誘發出的一種境界和情調,它是構建在獨特的、藝術化的武術形象之上的藝術體驗,并以一種情感體驗的方式存在于觀賞者的審美世界之中。
2 “武術意境”的構成
“意境是主觀情感與客觀景物相熔鑄的產物,它是情與景、意與境的統一”[1]335。顯然,來自于藝術家主觀層面的“情”和來自客觀現實——物象升華而成的“景”共同構成了“意境”的內容。那么,對于“武術意境”自然也可以從這兩個層面進行解構。
2.1 “武術意境”中的“情”
所謂“情”,可以將其理解為藝術家內心世界的情感。藝術作品之所以具有“抒情”的特征,正是因為寄托了藝術家的思想、情感、情趣等內容。同樣,武術也是如此,武術拳家們獨到見解、深厚思想、特殊情感以及主觀訴求也會被寄托在武術的技術形態之中。于是,“體驗”、“思想”、“情趣”等內容成為“武術意境”中的“情”的內容。
在武術中,我們可以將拳家們對武術技術技法的親身感受看作是體驗,它本身就是建立在個體習武經歷之上的一種主觀層面的情感;思想,可以看作是拳家們對拳理拳法、技理技法等內容形成的理性認識,它是對武術的宏觀性、原則性的認知結果,如太極拳陰陽理論為拳理,八卦掌“以《易經》的不易、變易和簡易之理”[6]為其拳術思想的要義;情趣,是指拳家們對拳術架勢、形態、風格等內容的主觀偏好,它是拳家們的個性化的理解和判斷,其表現為不同拳法在形式和風格上也就具有各自的特點。這些“情”所指向的內容依附在武術的技術形態之中,可以經由演練者出神入化的表演而令觀賞者在審美活動中感知。
2.2 “武術意境”中的“景”
所謂“景”,是指“審美主體在思維上生成的一種對于藝術或藝術作品形象化了的東西”[7]。比如,當人們在欣賞一幅優美的繪畫作品時,紙上的畫作為一種真實的“象”引發了觀賞者審美想象,獲得美的體驗。在這一過程中,觀賞者通過藝術的想象后再次得到的“象”,即是“景”。
同樣,當觀賞者在對武術這一審美客體進行觀照時,其經過各種聯想或想象之后生成的“形象化的東西”,就可以看作是“武術意境”的“景”。武術的“景”是產生于“武術意象”(按照藝術理論中“意象說”,將以現實中的攻防格斗素材,并經過“藝術化”的加工和改造之后的以表現技擊為目的的武術技術技法看作是“武術意象”)之上的“象”,是“對生活形象的變形和改造的結果”[8]——意象的再次成象,即是觀賞者依照演練者創造出的“武術意象”進行各種聯想和想象的結果。因此,“武術意境”中的“景”,是觀賞者通過自我的藝術想象來實現對武術的具象、意象的再次創造,是審美主體主觀認知和抽象思維活動的結果。
2.3 “情”、“景”交融構成武術的藝術整體
王夫之曾說:“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9]可見,“情”是“景中情”,“景”是“情中景”,“情”與“景”的結合與統一,勾勒出藝術的境界,最終形成一個有機的藝術整體。
當武術作為一個審美客體被觀賞時,便同時涵蓋了“情”與“景”的內容,體現著“情”與“景”的交融和映襯。“情”指向的是拳家們的體驗、思想、情感、意趣等內容,表明了武術具有“重抒情”的藝術特征;“景”指向的是觀賞者對武術意象的再次成“象”,表明了武術是通過藝術化的形象引發審美主體進行美的聯想或想象。所以,“情”與“景”的交融,令武術具備了“境生象外”的特征,并因而產生了獨特的藝術境界。
3 “武術意境”的營造
“意境的形成是諸種藝術因素虛實相生的結果。它是特定的藝術形象(實)和它所表現的藝術情趣、藝術氣氛以及可能觸發的豐富的藝術聯想及幻想形象(虛)的總和”[2]22。由此可知,“意境”是“虛”與“實”高度化結合的結果,“虛境”與“實境”共同營造出藝術的“意境”。在武術中,也存在著“實境”和“虛境”的結合。
3.1 “武術意境”中的“實境”
童慶炳[10]指出:“實境是指逼真描寫的景、形、境,又稱‘真境’、‘事境’、‘物境’等。”那么,在武術中,可以將演練者通過肢體的運動所創造出的一個個具體而生動的武術形象看作是一種“實境”,它包括:武術的招式、招法,武術的技術、技法等各種具體的表現形態。
作為“實境”的武術形象,是對現實中的各種攻防技術技法的逼真描繪。然而,“藝術形象的魅力并不在于復制現實,而在于超越現實之后重新獲得意義和真理”[11]。所以,武術形象又絕非是對一般技擊格斗行為的“復制”和“重現”,而是一種經過了提煉、萃取,并被賦予新的形式與內容的技術形態,其表現為“生動鮮明”和“直觀可感”的藝術特征。首先,生動而鮮明的形象能夠使觀賞者在視覺上形成強烈的刺激,進而產生身臨其境的效果;其次,直觀而可感的形象能夠使觀賞者在精神上產生直觀的情感體驗,激發起觀賞者對各種武術情景的想象。例如,“南拳因勁力而稱道,突出的是其陽剛之美、彪悍之感;通臂拳以氣勢奪人,突出的是豪爽的氣勢之美;八卦掌移形轉換貫穿其中,似飛燕鉆云,如云卷煙繞,突出陰柔之美”[12],這些不同類型和風格的拳術,帶給觀賞者的感受和體驗都是不同的。
3.2 “武術意境”中的“虛境”
藝術理論中的“虛境”是“指由實境誘發和開拓的審美想象的空間。它一方面是原有畫面在聯想中的延伸和擴大,另一方面是伴隨著這種具象的聯想而產生的對情、神、意的體味與感悟,即所謂‘不盡之意’,所以又稱‘神境’、‘情境’、‘靈境’等”[10]。由此,可以將武術的“虛境”表述為“審美客體的內在反映,即心靈對審美對象的形象、實景、形體所作的虛景、象征、意蘊的能動的反映”[13],它由觀賞者發起,是對武術的“實境”進行主觀想象的結果。
當“生動鮮明”和“直觀可感”的武術形象激發起觀賞者對武術技術技法的審美想象之時,觀賞者的審美能動性便開始了“個人化”的發揮。此時,呈現在觀賞者面前的武術“實境”使得他們的審美想象空間得以建立,武術“實境”在這一想象空間中便開始了再次“塑形”,從而產生新的景象,得到的便是武術的“虛境”。譬如,武術中的“旋風腳接劈叉”這個技術動作,當演練者騰空跳起后在空中完成里合腿,肢體螺旋上升的“實境”會給人一種猶若龍卷風直沖云霄的想象,緊接著演練者在空中清脆地擊響,然后雙手展開劈叉下落的“實境”會給人一種猶如矯健的雄鷹俯沖地面的想象。其中,“龍卷風直沖云霄”、“矯健的雄鷹俯沖地面”這些感受,就是武術“虛境”的表現。可以說,就在瞬息之間,武術的“虛境”在觀賞者的腦海中萌生并成形。
3.3 “虛”、“實”創構凸顯武術的藝術味道
“武術意境”的化生,來自客觀存在的“實境”和主觀生成的“虛境”兩者的高度化結合。“實境”表現為能夠引發觀賞者進行藝術想象的武術技術技法,它是武術“虛境”產生的基礎,為其提供了進行藝術想象的素材;而“虛境”是觀賞者對武術“實境”進行藝術想象后的結果,存在于觀賞者的主觀意識之中。這兩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體現出“虛實創構”這一藝術特征。
“意境是一種若有若無的朦朧美”[1]337,而“武術意境”所追求的也正是如此。有形的技術技法和無形的技擊景象兩者之間的有機融合,體現了“中國傳統思想中非虛非實、即虛即實的存在”[14],這也是千百年來中國傳統藝術一以貫之的藝術追求。在“實境”與“虛境”相互映照下,武術外具“生動之形”而內含“豐富之意”,在“虛實”之間流露出意蘊深邃的藝術韻味。
“意境”說在我國傳統藝術中的存在,其意義在于凸顯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之間在“情感世界”里的相互融通。也正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對“意境”的追求和向往,才賦予了我國的詩詞歌賦、戲曲書畫等無窮的藝術魅力。盡管,武術并未被界定為傳統藝術的一個門類,但是,我們無法否認:在“情”與“景”交融和“虛”與“實”創構的作用下,武術也具備了獨特的藝術意境。這種意境的存在不僅實現了對武術表現形態的“藝術化”構建,與此同時,藝術化的武術形象也超越了具體化的技術技法、超越了形式化的物象,超越了現實的世界,成為了可以令審美主體在心靈世界里展開藝術想象的基本元素,將審美主體帶入了一個可以進行審美想象的藝術空間。在這個藝術想象的空間里,審美主體可以自由地進行著對武術技術技法的認知,進行著對武術景象的創造,進行著對武術情趣的體味。從藝術學的角度來看,“武術意境”是體現武術藝術價值的高級形態,是武術“藝術性”存在的顯著標識。
[1] 彭吉象. 藝術學概論[M]. 3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 蒲震元. 中國藝術意境論[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3] 成遠鏡. 意境美學[M]. 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135.
[4] 劉鑫. “意境”中的虛實關系淺析[J]. 美與時代(下半月),2010:41-43.
[5] 金銀珍,羅小華. 藝術概論[M]. 武漢:武漢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74.
[6] 劉永椿. 尹式八卦掌釋秘[M]. 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8:1.
[7] 張黔. 藝術原理[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96.
[8] 童慶炳. 文學概論[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61.
[9] 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教研室. 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下冊)[M]. 北京:中華書局,1980:278-279.
[10] 童慶炳. 文學理論[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96.
[11] 朱曉軍. 藝術概論教程[M]. 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46.
[12] 李微. 淺談武術運動中的美學藝術[J]. 吉林體育學院學報,2008,24(1):126-127.
[13] 喬軍豫. 在宗白華的美學中散步——論其“意境說”[J]. 今日南國,2009(11):94.
[14] 彭吉象. 中國藝術學[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