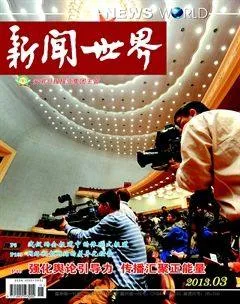我們是否已進入媒體的娛樂化時代?
【摘 要】“病毒式”蔓延的《中國好聲音》,標新立異,打破本土一貫的娛樂手法,大獲成功,這僅僅是一場皆大歡喜的“娛樂”盛宴,亦或是標志著媒體娛樂化時代的到來?本文以此疑問為基礎,在思考媒體的娛樂化對受眾日常社會生活的介入影響之外,更反思整個媒體行業的娛樂化傾向對社會精神指向的侵染。
【關鍵詞】《中國好聲音》 媒體 娛樂化
這是一份精彩、有力、難以辯駁且非常重要的預言:公共話語只能訴諸于娛樂的方式出現,娛樂的內容取而代之的成為文化精神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我們毫無怨言,無聲無息,樂在其中的成為娛樂的附屬物,便也就預示著合理化娛樂時代的正式到來。《中國好聲音》的成功,制造了一幅皆大歡喜的生動圖景,供受眾觀賞、回味,而媒體對后好聲音時代的輿論總動員,更是不遺余力,馬不停蹄。此情此景,腦海中就不由得會聯想到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表達的憂慮:人們會漸漸的崇拜那些使其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①。
《中國好聲音》以區別于以往所熟知的音樂選秀形式,火熱了2012年夏季的娛樂舞臺,它的急速躥紅所引發的輿論爭議,讓我們不禁思考:我們是否已經進入了娛樂的時代?
為娛樂買單——我愿意
我們的媒體正在進行著與之前美國同樣的實驗:讓人們投身到電視插頭所帶來的各種娛樂消遣當中去。既然“魔彈理論”的敘述方式已經讓受眾覺得過于赤裸,那我們就借“有限效果理論”的手,讓大眾為媒體投資生產的娛樂內容買單。
《中國好聲音》的節目模式購自全球熱播的另一個娛樂原版《the voice of Holland》,其中,突破傳統選秀節目的最大特色就是他的盲選階段,讓觀眾自認為置身于一個真正以“好聲音”為選擇標準的正義舞臺,并且,節目的整個比賽過程中將其盲選的特色發揮到了極致。加上巨額的資金投入,四位背對參賽者,面對觀眾,來自不同音樂風格和領域的評選導師,高識別度的V型logo,環形的觀眾舞臺,亮麗的燈光,重復播放,充斥網絡媒體頁面中心位置的宣傳畫面……,視覺盛宴的一波未平,聽覺沖擊的一波又起,讓大眾忙著欣賞,忙著感受,忙著歡呼,只覺得內心的各種希望和理想,隨著舞臺上歌手的演唱和評委的配合點評,也開始騷動不安,仿佛自己的理想和夢想也即將實現,成功也就觸手可及。“媒體”成功了,“娛樂”成功了。他們仿佛在高喊著:“你看,他們依舊是我們的‘奴役’”。
媒體為我們創造的娛樂“幻像”,得到了比他們投入的多得多的回報——如果我們被“幻像”滿足,回到現實后的思考能力和思考主動性就可能會日漸消沉,一旦媒體停止制造,我們的迷茫和不安就是毒藥。
馬斯洛需要理論的娛樂化實現
有限效果理論的主要觀點是:大眾傳播不能直接改變受眾對事物的態度,因為有許多因素對受眾做出決定起著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個人的政治、經濟、文化、心理的既有傾向,以及受傳者對信息的需求和選擇性接觸、群體關系和群體規范,大眾傳播過程中的人際影響等等。
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的需求層次可分為:生理需求、情感和歸屬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
再看《中國好聲音》,真的很好的利用了上面的兩種理論。現在的人們需要強調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和自主決定能力,被動的接受者身份,在他們聽來并不順耳,日益競爭激烈的媒體行業與其他行業的共同點在于:盈利和利潤。若明目張膽的以商業模式盈利,定會招致受眾對媒體社會責任的追究,針對媒體的討伐也就開始。然而這個游戲已經進行了許久,媒體通過扮演與受眾同甘共苦的知己角色,利用媒體本身的社會資源,好像在千辛萬苦的滿足大眾的基本需求,聲嘶力竭的聲討現實生活中人們的疾苦,悄悄的積累了越來越多駐足于臺下的圍觀者,他們熱淚盈眶,感激不盡。實際上,臺上的吶喊確實與他們無關,現實中面臨的困惑依舊存在,沒有一直的掌聲,也沒用一直為你亮著的鎂光燈。
《中國好聲音》的盲選特色,確實給予了所有的參賽選手起點的公平,我們予以肯定這一點釋放出來的正面信息,但轉過身來,仍舊是娛樂的時代。背過身,這個舞臺不在乎你是否是音樂專業出身,不在乎你是否高矮胖瘦,正常或殘疾,美麗、俊俏或姿色平庸無奇,它對這個看中表象的社會在乎的一切外在置若枉然,只要你有夢想、理想,喜歡和熱愛歌唱,就可以來參賽,你看,在這里可以得到尊重、認可、自我實現。但轉過身,它卻在乎你的故事夠不夠讓導師落淚?導師的選擇是不是足夠具有爭議?選手這個或那個的去留是不是足夠延續觀眾的激情?這個舞臺只用了一首歌的時間就滿足了我們所有的內心需求,我們卻用了所有剩下的時間回味這種滿足帶來的虛假“愉悅”,那么真實,那么諷刺。
時代不斷變遷,嘗試拔掉電源插頭的努力歸于徒勞,人們一如既往的相信,技術是社會進步的朋友,文化的一部分,總會帶我們進入理想的天堂。那游戲的結果呢?
歡樂的監獄
談論一個眾人關注且皆都認為無害的東西,必須要提高嗓門,聲嚴厲色,才夠引起別人的注意,但這樣一來就很容易被誤解,認為是“悲觀主義者”、“杞人憂天”。對于監獄這類的東西,生活經歷告訴我們:如果置身事外,就必須對里面關上的東西提高警惕,以免被其污染、禍害,如果置身其中,當監獄的大門即將關閉的時候,就要奮起抵抗。要是還有下面的第三種情況:如果監獄里面充滿歡笑,甚至是在監獄以外從未見過的歡樂景象,完全看不到,也聽不到一丁點兒關乎痛苦的痕跡和聲響,那我們還有什么理由拿起武器,自我保護?
《中國好聲音》以病毒式的傳播速度,聲勢浩大的媒體宣傳,獨特的節目形式,居高不下的收視率,引發越來越多的圍觀者,其實聲音本身是捕捉不定的象征性事物,要評定其“好”聲音與否,不是坐在臺下的四位娛樂圈名人能夠一語定奪,全然成了一個老偶像選擇新偶像的測試,區別是,從原來的小教室搬到了大舞臺,從只有評委和選手到后來還有了觀眾,這性質就不同了。即使能夠保證節目的模式具有不可復制性,但實際上,在轉過身來之后,作為能夠影響評委選擇的因素已經被選手復制使用了。這個舞臺也就形同于標題所比喻的“歡樂的監獄”②明明是一場娛樂的盛宴,卻偏偏要標榜勵志和正義;明明是一場偶像制造偶像的情景劇,卻偏偏讓參賽選手和觀看者當成是至關重要的人生轉折點,好在人群之中總還是有那么幾個清醒、理智的,沒有順從的只去享受發現了一個沒有痛苦只有歡笑的“監獄”的驚喜,明白這還是一個監獄,而這幾個僅有的明智之人,卻是想著如何利用這點“聰明”,從制造這“歡樂”的人那里得到些好處,這就是我們自己的不聰明了。
結語
如果《中國好聲音》僅僅是制造了2012年夏季一場娛樂狂歡的煙霧彈,質疑媒體娛樂化時代的到來未免有點大題小做,問題在于它被定義為“強力打造的大型勵志專業音樂評論節目”,這是否就意味著媒體的娛樂包裝并不再局限于包裝娛樂本身,而是開始涉足嚴肅的公共話語領域。對信息的結構和效應沒有深刻意識的普通大眾,因為不能消除對媒介的神秘感,在一定程度上,很容易被媒體娛樂化包裝的信息所左右和控制。媒體的娛樂化不僅要為大眾所警惕,更應該被整個社會及這個社會的媒體所警惕,如若“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那么,一切的公共事務就真的會形同雜耍。□
參考文獻
①[英]阿道司·雷納德·赫胥黎:《美麗新世界》,重慶出版社,2005
②[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作者: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新聞學專業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