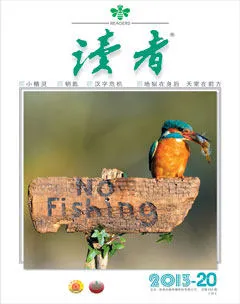去做義工
易萱

到拉美教漢語,到美國學烹飪,在泰國伺候大象,到澳大利亞生態農莊種地,在緬甸修學校,到德國幫助孤獨癥患兒,甚至去塞拉利昂做接生婆……近兩年,越來越多走在潮流前面的青年人發現,原來還有認識世界的“第三條道路”。
無國界醫生
1年前,臺灣男生李一辰還按部就班地做著麻醉師。3年前,北京婦產科醫生安娜還過著往返于家與醫院兩點一線的平凡日子。
帶著內心最后一絲躁動,他們不約而同放棄了原本安穩的生活,去最艱苦的地方行醫,成為“無國界醫生”。
“我就像一只井里的青蛙,抬頭只能望到那一小塊天空。”這是李一辰參加“無國界醫生”前的狀態。5年醫學院本科、2年研究生學習,外加2年畢業實習,李一辰一直按照設定好的軌道奔跑。“我一直生活在臺灣,從未看到外邊的世界。我一面好奇外邊的世界是怎樣的,另一面又擔心自己會不會就在一家醫院這么老去。”
2012年加入無國界醫生組織的李一辰沒想到,自己會被派往敘利亞做戰地醫生。
“我從未看到如此慘烈的狀況。”李一辰說,“在敘利亞,一波襲擊后,醫療點住滿了傷員。有人腸子流出來了,有人頭骨破裂,更多病人因爆炸受傷,面臨截肢……和平地區的醫生很難接觸到如此危重的病情,那場面比電影里呈現的可怕得多。”作為唯一的麻醉師,他簡直忙暈了。
之前,武裝沖突只是電視中一閃而過的30秒新聞,現在這就是他真實而狼狽的工作環境——晴天是敘利亞的“壞天氣”,因為能見度高,空襲總會特別多。戰機呼嘯聲、炮彈爆炸的轟隆聲仿佛是手術室的背景音,忽大忽小,如影隨形。
最艱難的是,戰地醫生需要時刻面對生命流逝。有位老母親曾跪在醫療點一個小時,求醫生挽救她早已死去的兒子。她絕望的神情,李一辰至今記憶猶新。“很多人抱著最后一絲希望將已經死亡的家人送來醫院,有些逝者甚至頭部和身體都分離了。”
敘利亞的項目結束后,李一辰前往土耳其休整。在伊斯坦布爾的酒店里,明亮的房間讓他很不適應。“在敘利亞,晚上大家都生活在黑暗中,以防被轟炸,吃飯、洗澡、走路都在一片漆黑中進行。在土耳其的旅館,我盯著房間里明晃晃的電燈,恍如隔世。”
做國際義工,讓李一辰的生活完全變了。原本他覺得世界大得可怕,但隨著到不同國家做項目,認識不同朋友,他猛然發現世界變小了。原來被套牢在醫院的無力感消失了,眼前的人生一下出現了好幾條通路。
安娜同樣滿懷勇氣出走,她到海外做醫療援助時,孩子還未滿兩歲。從塞拉利昂到巴基斯坦,從索馬里到阿富汗,一晃3年,安娜參與了無國界醫生組織位于亞非4國的5個海外醫療項目。
作為婦產科醫生,安娜的工作地點都是世界母嬰死亡率極高的區域。在衛生和醫療水平極其落后的地區,她時時要面對不同的風俗與矛盾。
塞拉利昂居民大都對醫院心生畏懼,許多孕婦在家難產,最后迫不得已才去醫院急救保命。“你會見到各種在中國從未見過的極端案例。”安娜說,“當地孕婦沒有產檢,很多嚴重疾病和并發癥都在分娩時才顯露出來。病人送到醫院時,情況總是一團糟。”
大量子宮破裂的產婦讓安娜印象深刻,“一般,病人送院后早就休克了,孩子也胎死腹中。很多產婦因為在家耽誤太久導致子宮破裂和嚴重內出血。最初接手這樣的病例,我都情不自禁在心里驚呼:‘哇,太可怕了!”
在巴基斯坦,許多嬰兒營養不良。安娜發現,原來按照當地風俗,很多家庭用一種傳統甜茶代替母乳喂給新生兒,導致孩子長期處于饑餓狀態。在索馬里,許多醫院只是一幢空房子。因為醫療器械和藥品資源極度缺乏,很多時候,面對患者,醫生和護士只能干著急。
做海外志愿醫生,安娜最深的體會就是,同樣是產科,不同地區的病人各具特點。作為醫生,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個產婦,而是不同國家迥異的社會形態、風俗習慣。“美國、日本、加拿大……很多人都去過,但我們服務過的那些非常艱苦的地方,卻是多數人難以抵達、絕少體驗的。”總得有人看到,這世界不容忽視的另一面。
到非洲喂猴子,去泰國養大象
與大多數人花錢出國看動物不同,一些人選擇花錢出國伺候動物。
2013年3月,廣州男孩王博文就參加了納米比亞的30天動物保護項目。
靜靜分享屎殼郎滾糞球的喜悅,或者一整個下午觀察鱷魚捕食。“這可不是紀錄片里的情節,完全親眼所見。”一提到自己的非洲生活,王博文整個人都變得神采奕奕。
與普通游客不同的是,他需要做很多“苦勞力”。比如,學習如何用沙土和石灰制作磚頭、修建營地,又比如,為了能在雨季多為動物們儲存些水,營地還組織志愿者到草原各處挖坑,建人工蓄水池。看似簡單的勞動,在接近赤道的高溫烈日下都極其耗費體能。王博文回憶:“只一會兒工夫,所有人都大汗淋漓。男生們紛紛脫去上衣,過后發現每個人身上都曬出了一件‘背心,特別搞笑。”
“動物園是人造的假象,圍觀動物不代表愛護動物,那完全是人類的娛樂。”王博文說。在非洲,他第一次和動物生活在一起,看鱷魚捕食,研究斑馬交錯站立,圍觀猴子吵嘴。多虧這次義工活動,帶他走進了動物的世界。
在泰國,保護大象的志愿者項目極具吸引力。從一天體驗活動,到持續幾周的志愿勞動,時間安排非常靈活。人們不但能夠近距離觀察大象并了解它的相關知識,更能花幾周時間接受培訓,做大象飼養員。
2012年,Verian參加了清邁和素林兩個大象保護項目。她對大象的感情,到了“愛屋及烏”的程度。在她看來,為大象清理糞便都是浪漫的事,因為那糞便充滿了森林的氣味。
在清邁,Verian常一早跟著養象人下田搬食材,然后在廚房為大象清洗要吃的西瓜、南瓜和甘蔗,一箱箱裝好,11點準時給大象喂食。她很喜歡看大象吃東西——它用鼻子巧妙地將食物卷進口中,一邊咀嚼一邊拍打大耳朵,尾巴左搖右擺,同時提起單腳,像跳舞般向前踢。
在素林,Verian見到大象生存的另一面。她發現很多大象整天持續不斷地搖頭晃腦,踢腿跳舞。直到晚上九十點鐘,周圍完全沒人,一片漆黑的時候,大象還是做著同樣的動作,一刻不停。
泰國的義工項目,讓Verian感觸頗多。回國后,她不遺余力地勸說身邊每個計劃赴泰旅游的人,千萬不要花錢參加“大象娛樂項目”。“在泰國,騎大象的項目總是最受中國人歡迎,但在保護基地,中國人卻寥寥無幾。”她落寞地說,“很多人永遠不了解,他在泰國騎大象最開心的時光,卻是伴隨大象一生的夢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