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手記
凌志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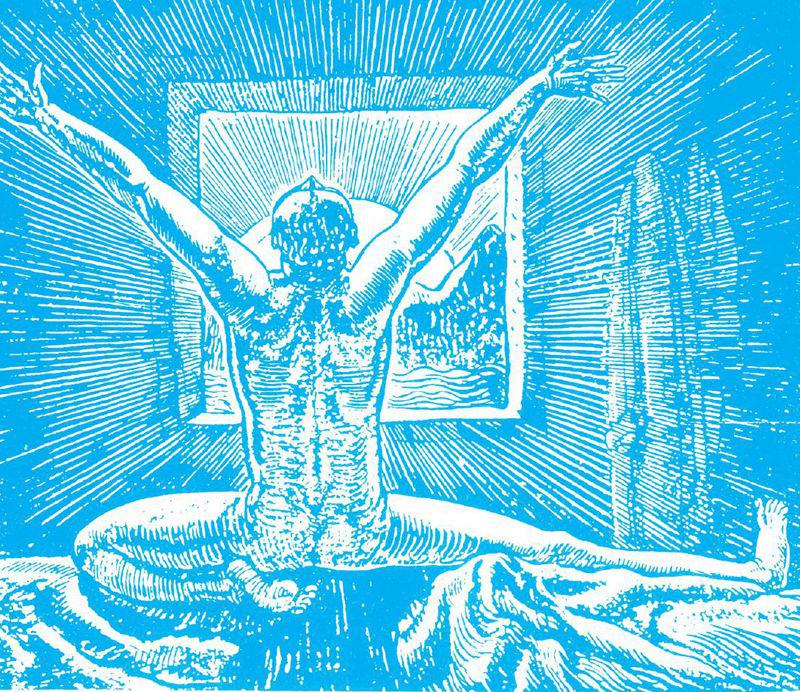
2007年2月,我病倒了。醫(yī)生在我的顱內(nèi)發(fā)現(xiàn)兩處病灶,疑為腦瘤。兩天后又在我的左肺發(fā)現(xiàn)腫瘤,由此診斷“肺癌、腦轉(zhuǎn)移”的概率為98%,也可以說是“肺癌晚期”。醫(yī)生當(dāng)時(shí)認(rèn)為,我活不過3個(gè)月。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我和我的家人都懵了。有生以來第一次與死亡如此接近,真切地感受到一個(gè)癌癥患者的恐懼和絕望。
靠著妻子的攙扶,我搖搖晃晃走出家門,就像所有癌癥患者一樣,開始了慕名投醫(yī)的漫漫路程。
忍耐了兩個(gè)小時(shí)的路上顛簸和頭暈?zāi)垦#只?00元掛上專家號(hào),我們終于獲得機(jī)會(huì)面見這位專家。盡管是個(gè)“特需門診”,卻沒有誰來給我們約定一個(gè)準(zhǔn)確時(shí)間,所以還要經(jīng)過一番漫長(zhǎng)的等待。在昏暗之中耐心等了3個(gè)小時(shí),終于在下班前的最后幾分鐘見到“主任”。
他只看了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核磁共振膠片上。我強(qiáng)打精神,試圖敘述我突然發(fā)作的癥狀,可是很快發(fā)現(xiàn)他對(duì)我的話不感興趣。他的熱情似乎只在向他對(duì)面的年輕醫(yī)生侃侃而談,年輕醫(yī)生則是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這種感覺很快影響了我的心情,讓我疑惑。我能理解由于病人太多,所以醫(yī)生只能讓病人排很長(zhǎng)時(shí)間的隊(duì),看很短時(shí)間的病,但我不能理解他們?cè)趺磿?huì)如此不在乎病人的心理感受;我能理解醫(yī)生因?yàn)橐姸嗖还侄a(chǎn)生的不耐煩和冷漠,但我實(shí)在不能理解,為什么他們只知道那些儀器、膠片和檢查報(bào)告,而完全不顧及病人的身體癥狀;德高望重的醫(yī)生門下理應(yīng)高徒滿座,他們利用臨床病例來教導(dǎo)弟子也是必不可少,可是我很難想象,他們既然已經(jīng)與病人“特約”自己的時(shí)間,并且為此收費(fèi),竟又不肯把時(shí)間專用在病人身上。
告別“主任”時(shí)天已大黑,我們得到的僅僅是一張專家門診掛號(hào)費(fèi)發(fā)票,以及一篇演講、一個(gè)“?”和一個(gè)模棱兩可的“待除外”。我們沮喪地發(fā)現(xiàn)還是在原來的起點(diǎn)上踏步,既不能確定自己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該怎么辦。
我把家里的賬單、存折、信用卡全都找了出來,半睜半閉著眼睛把密碼一一寫在紙上,收拾停當(dāng)。老婆一向不問家里錢財(cái),也不知道我究竟掙了多少錢,又放在什么地方,所以我想,如果我走了,得讓她能夠找到。
做完這些以后心里稍感輕松,感覺自己今生已經(jīng)了無牽掛。如果說還有什么遺憾,那就是在過去的歲月里沒有用更多時(shí)間和他們母子二人待在一起。結(jié)婚25年來,我們一直聚少離多,可我竟從未把這當(dāng)一回事。人總是不在乎自己擁有的東西,要等到失去的時(shí)候才知道珍惜。
上海華山醫(yī)院神經(jīng)外科主任周良輔教授建議我再對(duì)腦部做一次核磁共振掃描,但是必須加上“波譜”。他解釋說,這是國(guó)外的一項(xiàng)新技術(shù),有助于確認(rèn)顱內(nèi)腫物的性質(zhì),甚至還能更準(zhǔn)確判斷它與肺部病灶是否有關(guān)。
波譜掃描的檢查報(bào)告至少還要等上3天,我們意外地收到來自歐洲的消息。當(dāng)大夫的妹妹告訴我,對(duì)于我的病,國(guó)外專家的看法和國(guó)內(nèi)專家并不完全相同,至少?zèng)]有那么悲觀。
國(guó)外的專家認(rèn)為,仍有進(jìn)一步確診的必要。由于沒有見到病人,他們看到的只是我寄去的全部腦部膠片,又認(rèn)真傾聽妹妹轉(zhuǎn)述我的發(fā)病經(jīng)過,對(duì)他們認(rèn)為很重要的細(xì)節(jié)反復(fù)詢問,然后回到那些膠片旁,重新查閱。他們甚至不認(rèn)為這是一個(gè)正式診斷,他們極力建議在中國(guó)重新來一次會(huì)診,要請(qǐng)最好的醫(yī)生。
妹妹當(dāng)即決定從布魯塞爾趕回北京。到北京后,她直接去醫(yī)院,拿到波譜掃描膠片,又到京城最大的書店,買來專門論述波譜掃描技術(shù)的書。一個(gè)上午的求醫(yī)經(jīng)歷讓她失望,現(xiàn)在她決定依靠自己。整個(gè)下午和晚上,她都在閱讀這本書。書比磚頭還厚,很難讀,但她很快弄懂了其中要害。她把我的膠片一一展開,攤在床上,仔細(xì)比照,結(jié)果發(fā)現(xiàn),這項(xiàng)檢查還真的有助于判斷顱內(nèi)病灶的性質(zhì),跟周良輔教授說的一樣。
“所有的征兆都顯示,良性的可能性大。”她在電話里對(duì)我說。
“你相信誰呢?”妻子問我。
“當(dāng)然相信我妹妹。”我回答。
“你不會(huì)是只想聽好話吧?”妻子再問。
“不!”我說。
我接著述說我的理由:我不懂醫(yī),但我了解妹妹。她在腦神經(jīng)醫(yī)學(xué)領(lǐng)域里不是行家,但她是糖尿病方面的專家。最重要的,她是一個(gè)肯接受新事物和善于學(xué)習(xí)的人。過去20多年,她以治學(xué)嚴(yán)謹(jǐn)和對(duì)糖尿病卓有成效的治療獲得了同行尊重。在這件事上她投入的不僅是智慧和專業(yè)學(xué)識(shí),還有感情和責(zé)任心。那些專家只不過投入了他們的時(shí)間——短暫的、以金錢來計(jì)算的時(shí)間,而妹妹投入的是全部心血。她也有可能犯錯(cuò)誤,但她犯錯(cuò)誤的概率一定要比那些專家小。
給自己一個(gè)選擇的機(jī)會(huì)。在接下來的一周里,我忽然意識(shí)到,這一點(diǎn)是我成功獲救最重要的環(huán)節(jié)。
我這樣說有個(gè)原因,大多數(shù)癌癥病人,還有他們的親人們,從一開始就放棄了自己的判斷力和選擇權(quán)。醫(yī)生說什么就信什么,結(jié)果一步步地走向一條錯(cuò)誤道路。
要不要讓醫(yī)生鋸開我的腦袋?這真是迄今為止我生命中最困難的決定。醫(yī)生讓我“不要耽誤最佳的治療時(shí)機(jī)”。所謂“最佳治療時(shí)機(jī)”,就是不能再等那腫瘤滋長(zhǎng)哪怕一分一毫,因?yàn)樗S時(shí)可能壓迫腦干神經(jīng),讓我即刻完蛋。
可是我們?nèi)匀徊荒芡耆嘈裴t(yī)生的預(yù)見。因?yàn)槲覀円馔獾匕l(fā)現(xiàn),腦瘤沒有像醫(yī)生預(yù)言的那樣迅速長(zhǎng)大。
最新的核磁共振檢查報(bào)告上面寫著,我的顱內(nèi)腫物約2.2厘米×1.9厘米,而前一次檢查的結(jié)果是2.5厘米×2.3厘米。
兩次檢查間隔17天,從2.5厘米到2.2厘米,這變化相當(dāng)細(xì)微,我卻近乎偏執(zhí)地相信它意義重大。
“能不能證明它正在縮小?”我指著那一沓膠片小心地問醫(yī)生。
“不能!”醫(yī)生的回答很干脆,看著我的眼神明顯表示這是一個(gè)外行的問題。他們解釋說,核磁共振儀器是依據(jù)斷層掃描的規(guī)則工作,每一斷層間隔為0.5毫米。每一次掃描不可能在絕對(duì)相同的斷層上。由于病灶本身是個(gè)不規(guī)則的球狀體,所以不同的斷面完全可能讓影像直徑出現(xiàn)幾毫米的差別。
醫(yī)生把這種現(xiàn)象解釋為儀器的技術(shù)誤差,從科學(xué)上講無懈可擊,也讓我又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諱疾忌醫(yī)。
就在這左右兩難的糾結(jié)中,我隱約感到其中有些東西被忽視了。
“但是,”我頑固地尋找著問題的焦點(diǎn),“能不能證明它在過去兩周沒有長(zhǎng)大?”
“應(yīng)該是沒有長(zhǎng)大!”醫(yī)生這次回答得也很痛快。
我眩暈的大腦忽然更快地運(yùn)轉(zhuǎn)起來,里面浮現(xiàn)出一個(gè)外行的邏輯:如果醫(yī)生的預(yù)言不差——顱內(nèi)腫瘤屬于惡性并將迅速長(zhǎng)大,不可逆轉(zhuǎn),3個(gè)月內(nèi)威脅腦干神經(jīng),導(dǎo)致死亡,那么,17天之后的這次跟蹤檢查應(yīng)當(dāng)顯示它更大了呀,可現(xiàn)在,它竟“沒有長(zhǎng)大”!
既然它沒有長(zhǎng)大,那么,根據(jù)同樣的邏輯,也就有可能不是惡性腫瘤。
我知道這些不足以推翻醫(yī)生的診斷,但我看到了希望。或者說,它給了我一點(diǎn)幻想,就像漆黑夜空中隱約閃爍的一顆星辰。
我的身體正在發(fā)出微弱卻清晰的信號(hào)。與兩周前相比,目前我的種種不適——頭痛、眩暈、視覺模糊、眼球震顫、重影、畏光、失去平衡等與顱內(nèi)病變相關(guān)的癥狀,并沒有更嚴(yán)重。這與最新一次檢查結(jié)果相吻合。
多日來和醫(yī)生打交道的經(jīng)歷,已經(jīng)讓我產(chǎn)生一種直覺,也可以說是一種信念:我必須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
為了證明這個(gè)想法是出于冷靜和理性,而不是諱疾忌醫(yī),我同意3周后再做一次檢查,以確保對(duì)身體變化的最密切的跟蹤。妻子堅(jiān)決地和我站在一起,“無論你做出什么決定,我都支持你。”
那一天,我和家人共同做出決定:暫時(shí)擱置醫(yī)生的“立即實(shí)施顱內(nèi)腫瘤切除手術(shù)”的建議,繼續(xù)觀察3周,等待下一次核磁共振掃描的結(jié)果,當(dāng)然也包括細(xì)致入微地體會(huì)自己身體的變化。
一天晚上我們得到消息,上海華山醫(yī)院的周良輔大夫來到北京,他知道我已按他的建議完成波譜掃描后,同意為我再做一次會(huì)診。周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認(rèn)為是腦轉(zhuǎn)移瘤的診斷,在仔細(xì)分析了波譜掃描膠片之后,他得出了新結(jié)論:顱內(nèi)病灶不像是腫瘤,有可能是一種罕見的炎癥!
2007年從夏到秋的一段時(shí)間,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我腦瘤的癥狀減輕了。這一段時(shí)間進(jìn)行的復(fù)查表明,顱內(nèi)病灶正在緩慢地縮小。在如同重生般的體驗(yàn)中,我感覺到,癌癥治療體系有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而我們對(duì)癌癥的認(rèn)識(shí)也存在致命的偏差。這兩個(gè)致命加在一起,會(huì)讓生的希望變得渺茫。
一些醫(yī)學(xué)專家指出,“用藥不當(dāng)”大范圍地存在著。其中一位認(rèn)定,“目前癌癥病人符合規(guī)范用藥者僅為20%”。另外一位則指出,“有90%以上的癌癥患者沒有得到良好的治療方案”。
這些數(shù)字令我震驚,癌癥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懼和不正確的治療。
看來,我們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細(xì)胞的侵襲,而在于被中國(guó)式的癌癥觀念包圍著,同時(shí)還接受著中國(guó)式的癌癥治療。這種醫(yī)療環(huán)境正在造就一個(gè)悖論:醫(yī)學(xué)越發(fā)達(dá),越會(huì)剝奪患者的主動(dòng)性和判斷力,越會(huì)造成病人的恐懼和錯(cuò)誤。
2009年春季的一天,我遇到社區(qū)衛(wèi)生站的老護(hù)士長(zhǎng)。說起我的病,她不禁大驚:“你現(xiàn)在還活著,真不容易。別人像你這樣的,早死好幾回了。好好珍惜吧!”
死,是我們的歸宿;生,只不過是我們走向死亡的路途。在經(jīng)歷了與死神的對(duì)話之后,我對(duì)死亡的理解變得達(dá)觀和通透,我的生命也變得更加豐富和從容。
我想這就是所謂“向死而生”吧!
(阿 翔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重生手記》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