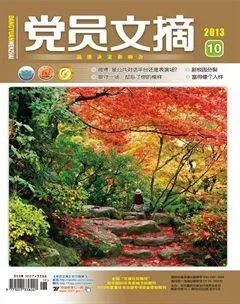“沉睡”背后是“裝睡”
最近,一些“沉睡幾十年,仍管今日事”的規定,引發社會廣泛關注。這些規定,有些如今已淪為聊勝于無的福利,喪失了當初立法的意義,例如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洗理費、每月五元的獨生子女費;有些則造成了新的社會不公,違背了立法的初衷,例如1981年實施的《關于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就將非公有企業職工擋在了“探親假”的門外。
不合理之處如此顯眼,為何這些規定卻能沉睡不醒?
規定的清理與修正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費時又費力。如果既不是政績考核的內容,又沒有問責機制,在尚未產生明顯的消極影響前,有關部門的緊迫性與主動性自然就不強。譬如“獨生子女費”的調整,由誰牽頭做調整、錢從哪兒來、調整多少合適,無不需要大量深入細致的調研和協調。倘若調整幅度讓民眾不滿意,還可能招來一通罵,費力不討好,不如假裝不知道其調整的必要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少數政策規定的廢舊立新往往意味著利益的再分配,這不僅是部門間的權力博弈,更是社會群體間的利益博弈。即便一些部門深諳相關規定亟待修改,卻因為不愿觸動原有的利益格局而選擇性失聰了。于是,“正在研究”成了借口,有些規定一“暫行”就是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在推諉扯皮中陷入了“沉睡”。
作為強制執行的約束性規范,法規需要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修改得太快、太頻繁,就成了朝令夕改,有違法律尊嚴,也有礙政府的權威性。然而,任何法律規定都是有生命周期的。經濟社會發展得越快,那些制定之初發揮巨大作用的規定就可能“衰老”得越快,甚至會“老”到成為經濟社會運行的障礙。從這個角度看,“沉睡的規定”就是變相的行政不作為、懶作為,其背后是少數職能部門在“裝睡”。
清理“沉睡的規定”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僅用一年時間,中央政府就清理了2300多件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地方政府則清理了19萬件地方性規章和政策措施,使我國基本建立了符合WTO原則的國內監管體制。如此龐大而復雜的立法工程僅用一年時間就解決了,可見,規定是否與時俱進,關鍵要看政府相關部門的決心。
是該下決心了。目前,我國各項法律規章的數量已居世界前列,法律未涉及、未覆蓋的領域越來越少,這是一個進步。另一方面,法律規章的公信力也有下降趨勢。此番社會熱議的“沉睡的規定”就是這樣,法律法規成了人們紛紛調侃、取笑的對象。法律的嚴肅性蕩然無存,法律的效力也大打折扣,影響政府取信于民的基礎。
“法與時轉則治,法與時宜則有功。”有關部門應當及時主動回應民意,盡早喚醒那些“沉睡的規定”。
(杜啟榮薦自2013年8月2日《人民日報》 圖:廖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