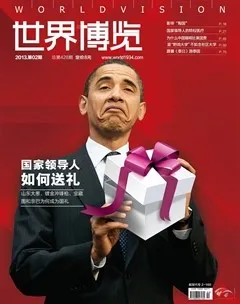俄羅斯孤兒成為報復的犧牲品
濫權腐敗案惹出的亂子卻要由俄羅斯的孤兒們來承擔,這何嘗不是一種荒謬?
去年12月28日,為了反擊美國議會通過的《馬格尼茨基法案》,普京簽署了禁止美國人收養俄羅斯孤兒的《季馬·雅科夫列夫法案》。該法案出臺背景極為復雜,引起俄內外強烈關注。仔細審視整起事件的來龍去脈,可以發現這是一段雜糅了專制獨裁、貪腐濫權、美俄對抗和孤兒悲情的復雜大戲。
其最終的結局是,俄羅斯孤兒們要為俄羅斯當下的體制、難以控制的腐敗和與美國緊張的關系買單,這讓整出大戲顯出一絲悲劇的意味。
俄兒童慘死美國
克里斯蒂婭·弗里蘭在撰寫《世紀大拍賣》一書時,把她在20年前將一名10歲俄羅斯孤兒帶回加拿大收養的事放在最開頭。看過那一段的人相信仍記得兒童們憧憬離開俄羅斯到西方生活的情景。
如今的俄羅斯當然不能與那時同日而語,兒童們至少不必如那時那樣恐懼饑荒。但是,就像俄羅斯人越來越多地享有向國外移民、留學、旅游的自由一樣,孤兒被收養至國外的權利總不該比那個混亂的年代還退化吧?但當普京簽署了這樣一份法案,孤兒們的權利卻實實在在地被限制了。
法案的直接原因是那個命喪于美國的俄羅斯殘疾棄嬰季馬·雅科夫列夫的經歷,法案的名字就由他而來。2006年,出生于俄羅斯普斯科夫州的這位先天殘疾兒童被母親拋棄,母親一紙“同意孩子被領養”的協議將季馬的未來交付于命運之神。2008年,來自美國的哈里森夫婦收養了這個孩子。季馬成了每年大量被外國人領養的俄羅斯兒童之一。但是,幾個月后,季馬喪命于車內的消息震驚俄美兩國。
當時,哈里森將季馬留在車里,自己離開辦事。當天氣溫高達32℃,季馬被關了整整9個小時,就這樣被活活悶死。專家稱,當時車內溫度很可能已經達到了54℃。
俄方自然極為憤怒,媒體對事件進行了連篇累牘的報道。美國人過去虐待從俄羅斯領養的兒童的許多事件都被重新提起。而當哈里森被美國法庭無罪釋放時,俄方朝野更加憤怒。應當說,俄媒報道的美國父母們的種種劣跡確實有根有據,這反映了跨國孤兒領養項目急需改正和糾正的地方。但是否有必要因為個別人的錯誤,讓所有俄羅斯孤兒失去被美國人領養的權利?畢竟虐待俄童的事件仍只是孤例。
此外,俄媒體上許多人也對美國人領養俄羅斯兒童進行了種種過度渲染,比如宣傳相關機構只是為了賺錢。也有人訴諸民族情感,認為這種“出賣”孤兒的事情很可恥,更何況是賣給在俄民眾心中沒少扮演民族情感刺激者角色的美國人。
但是,民意終究改變不了孤兒領養的重大社會意義。對每一個孤兒來說,被人領養就是一次新生的機會。既然外國人有意做出此種善舉,何不成全他們呢,管他是美國人還是法國人、英國人。只不過,對領養父母們的審查需要格外嚴格,其他手續也需慎之又慎。
但最終普京所做的,恰恰是把俄美孤兒領養的通道徹底堵死了。在法庭上,哈里森向俄羅斯人民喊話:“我請求俄羅斯人民的寬恕,在美國有很多想領養兒童并細心照顧他們的父母,而在俄羅斯也有許多急需父母照顧的孤兒。請成全他們,不要因為我的錯誤懲罰他們。”
為報復美國而出臺的法案
其實,如果真的是出于“不能將俄羅斯兒童送給別人照顧”、“美國危險,本著對孩子負責的態度,不能讓他們去美國”的考慮作出這一決策,那么人們難免質疑,其他國家就一定安全嗎?俄羅斯人根據什么來判斷自己的孤兒在哪些國家會受到悉心的照料?
不得不說,普京這次比較“用力”,而且用力的方式有些怪異。
這么說是因為,普京簽署《季馬·雅科夫列夫法案》是直接用來回擊美國國會通過的《馬格尼茨基法案》的。如果了解馬格尼茨基案,大部分人都會感到普京這一回應非常不搭調。
簡單回顧一下馬格尼茨基案。赫密塔吉基金管理公司上世紀90年代在俄羅斯私有化期間憑借出色的判斷賺得盆滿缽滿,該公司老總布勞德的爺爺曾是美國共產黨主席。之后的十幾年里,公司側重于保護俄羅斯大企業中小股東的權益,曾查出部分官僚在“俄氣”等大企業中侵吞國有資產的行為。他們的調查得到過普京的重視,后者因此整肅了大批貪官,挽回了損失。但是,自普京權力體系形成之后,赫密塔吉的調查也開始越來越多地與當局發生沖突,因為普京體系中的官員逐漸成為他們的新調查對象。
最終,布勞德被俄當局禁止入境。因為他調查的一起逃稅丑聞同時任稅務局長、后來成為俄國防部長的謝爾久科夫直接相關。謝爾久科夫本人和他的岳父都是普京體系的重要成員。
布勞德終于明白,他已經惹惱了普京當局。因此,他將公司從莫斯科轉移至倫敦,只留下少部分人繼續進行調查和經營。這其中就包括年輕的俄羅斯律師馬格尼茨基。很多人勸他不要再查下去了,但他不聽,而且繼續調查另兩起直接指向謝爾久科夫的財產被侵吞案件。
沒想到俄當局先出手了。2008年,馬格尼茨基被控逃稅,隨后被關押起來。2009年,他被轉入“水兵寂靜”看守所,隨后,在獄中神秘死亡。
馬格尼茨基的死在世界范圍內引起軒然大波,西方國家指責俄羅斯侵犯人權。但是,俄方拒絕承認,堅持認為馬格尼茨基是病死的。這起案件就這樣成了俄與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沖突熱點。
此時,恰逢美國國會因俄加入WTO而不得不廢除了限制俄對外貿易的《杰克遜-瓦尼克法案》,急需另一個用來牽制俄羅斯的法案。于是,用來制裁涉及馬格尼茨基案官員的《馬格尼茨基法案》應運而生。所有涉案官員被禁止進入美國國境,其在美國的財產都將被凍結。
普京及其權力體系極為震怒,并威脅將回擊這一法案。但誰都沒想到,普京會用一個涉及俄孤兒領養問題的法案來回應。在俄官方手中,美國人虐待俄兒童的事件一直被視為美國人權劣跡的重要材料。人權問題是俄美緊張關系中的一大主題,馬格尼茨基案之后更是如此,克里姆林宮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反擊美國人的有力武器。
普京做此決定后,連俄幾個副總理都表示了異議,議會中的反對聲音更多。社會上的反彈則更加劇烈。
很顯然,兩個被硬湊在一起針鋒相對的法案并不匹配。美國人的法案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對俄內政的干涉,而《季馬·雅科夫列夫法案》卻更多的是對俄羅斯人自身的傷害。而且,前者是正宗的外交內政問題,后者卻壓根不在此列,只是被生生抬高成了政治問題。
馬格尼茨基到底是怎么死的?由于俄政府不做負責任的調查,至今沒有令人信服的結論。但從后來謝爾久科夫去職時外界揭露出來的他及心腹們的種種濫權行為來看,馬格尼茨基的死因很可疑,這里面自然又可能隱含著威權體系濫權腐敗的一面。但這種濫權腐敗惹出的亂子卻要由俄羅斯的孤兒們來承擔,這何嘗不是一種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