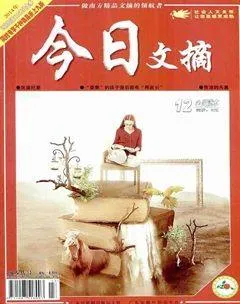“文化名爹”的教子之道
如今,不少二代倚仗父勢(shì),揮霍家業(yè),好逸惡勞,妄自尊大,讓他們的老爹一個(gè)個(gè)長(zhǎng)吁短嘆,頭暈?zāi)X脹。而回顧歷史,遠(yuǎn)的不說(shuō),單是上個(gè)世紀(jì),就有很多“名爹”在教育子女方面為我們作了示范。
新文化革命的闖將魯迅,對(duì)孩子疼愛(ài)不溺愛(ài),為周海嬰日后成材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在談到“怎樣做父親”時(shí),他曾明確表示:“自己背著因襲的重?fù)?dān),肩住了黑暗的閘門(mén),放他們到亮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為了讓孩子將來(lái)“幸福”、“合理”,他的家教既不粗壓暴制,也不嬌生慣養(yǎng),而是教孩子實(shí)實(shí)在在做人。他的“遺囑”也是有力證明:“孩子長(zhǎng)大,倘無(wú)才能,可尋點(diǎn)小事情過(guò)活,萬(wàn)不可去做空頭文學(xué)家或美術(shù)家。”1952年,周海嬰考取北京大學(xué)物理系,研究的是無(wú)線電。走上社會(huì)后,他靠自己謀生存,求發(fā)展,從不向外人炫耀自己的身份,終沒(méi)有辜負(fù)魯迅的期望。
近代出版界巨擘張?jiān)獫?jì)要求孩子自食其力,不要做那種徒有虛名、華而不實(shí)之徒。當(dāng)年,他唯一的兒子張樹(shù)年從美國(guó)留學(xué)回來(lái),想進(jìn)商務(wù)印書(shū)館。對(duì)此,張?jiān)獫?jì)堅(jiān)決反對(duì):“你不能進(jìn)商務(wù),我的事業(yè)不傳代。”他還分析了三個(gè)“不利”:“一是對(duì)你不利,由于我在商務(wù)的地位,你進(jìn)去后必然會(huì)受吹捧,浮在上面,毀了一生;二是對(duì)我不利,父子同在一處工作,在行政上將處處受牽制,如果不能主持公道,就沒(méi)有威信可言;三是對(duì)公司不利,這樣做將開(kāi)極為惡劣的風(fēng)氣,要知道,人人都有兒子,都把兒子塞進(jìn)來(lái),還像什么樣的企業(yè)?”后來(lái),張樹(shù)年只好在一家儲(chǔ)蓄所務(wù)工。晚年的張樹(shù)年回憶父親:“對(duì)于家庭來(lái)說(shuō),他永遠(yuǎn)是一位督責(zé)嚴(yán)格但又愛(ài)護(hù)備至的好父親。”
梁?jiǎn)⒊诮逃优畷r(shí),注意引導(dǎo)他們對(duì)知識(shí)的興趣,又十分尊重他們的個(gè)性和志愿。女兒思莊聽(tīng)從父親的建議,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xué)選了生物學(xué),結(jié)果很是苦惱。梁?jiǎn)⒊ず螅滦排畠海骸拔宜扑]的學(xué)科未必合你的愿,你應(yīng)該自己體察做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話。”他又告訴女兒:“學(xué)問(wèn)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這也正是他一向主張的“趣味人生觀”——“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價(jià)值;若哭喪著臉挨過(guò)幾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了沙漠,要它何用?”梁?jiǎn)⒊瑫r(shí)時(shí)以樂(lè)觀的情懷感染子女:“我平生對(duì)于自己所做的事,都是津津有味,而且還興會(huì)淋漓。什么悲觀咧、厭世咧,從沒(méi)有在我的詞典里出現(xiàn)過(guò)。”幾個(gè)子女也都得到了他的真?zhèn)鳎加馈⑺汲伞⑺级Y、思懿等,或研究火箭,或癡迷建筑,或醉心考古,或從事醫(yī)學(xué),他們愛(ài)己所愛(ài),個(gè)個(gè)都是勝利者。
梁漱溟的兒子梁培恕在談到父親的教育時(shí),說(shuō):“我們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擁有了別人沒(méi)有的最大的自主權(quán)。”這話并沒(méi)有夸大。生活上或?qū)W習(xí)中,梁漱溟從不強(qiáng)迫孩子接受自己的意圖。梁培恕的小學(xué)、中學(xué)、大學(xué)都沒(méi)畢業(yè),梁漱溟的態(tài)度是任其自然。另一兒子梁培寬也說(shuō):“父親對(duì)我完全是寬放的……我在父親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壓力。”的確,梁漱溟從不以端凝嚴(yán)肅的神氣面對(duì)孩子,他認(rèn)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勵(lì)。他不同意的,只是表明意見(jiàn),但從不干涉,更不強(qiáng)求。梁漱溟的這種教育方式貌似對(duì)孩子不嚴(yán),實(shí)際上,他是在潛移默化中引導(dǎo)孩子——自己的事情應(yīng)該自己負(fù)責(zé)。
傅雷的嚴(yán)格施教似乎“殘酷”。在他想來(lái),倘有天資,則成為第一流的藝術(shù)家;倘無(wú)天分,寧做別的工作。他要兒子傅聰做一流藝術(shù)家,所以,他不能容忍早年的傅聰有任何輕慢的言行。不論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細(xì)節(jié)方面,在藝術(shù)修養(yǎng)方面,還是在演奏姿態(tài)方面,傅雷都灌注了大量的心血。為達(dá)目的,傅雷甚至不擇手段,拿“虐待”形容也不為過(guò)。后來(lái),傅雷自己也意識(shí)到了問(wèn)題的嚴(yán)重:“跟著你痛苦的童年一齊過(guò)去的,是我不懂得做爸爸的藝術(shù)的壯年。幸虧你得天獨(dú)厚,任憑如何打擊都摧毀不了你,因而減少了我的一部分罪過(guò)。可是結(jié)果是一回事,當(dāng)年的事實(shí)又是一回事。盡管我埋葬了自己的過(guò)去,卻始終埋葬不了自己的錯(cuò)誤。”好在傅聰也體諒父親的良苦用心。他說(shuō),父親是他最好的老師。
《三字經(jīng)》里說(shuō):“養(yǎng)不教,父之過(guò)。”時(shí)至今天,父親在家庭教育中依然是重要的角色。身為人父,就要承擔(dān)當(dāng)?shù)呢?zé)任,就要讓孩子的身心健康,就要讓孩子的人格健全,也許,這才是“拼爹”的原意。
(柴見(jiàn)薦自《做人與處世》)
責(zé)編:我不是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