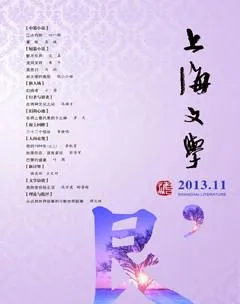從必然世界敘事到可能世界敘事
中國當代文學已經經歷了六十多年時間,其中小說敘事模式也完成了一個重要的轉向:從必然世界敘事到可能世界敘事的轉變。這兩個概念在本文中用來描述一種敘事態度:講述事物(世界)發展的必然性,還是講述事物(世界)的各種可能性?必然世界敘事重在表現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其基本意圖在于證明社會發展的必然性,證明社會必然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可能敘事重在表現事物發展的可能性,因為種種偶然,社會成為了現在這個樣子,還有種種偶然,社會還可能成為其他樣子。從必然敘事向可能敘事的轉變。是對世界、社會發展認知發生轉變的結果。
一、可能世界與必然世界
可能世界概念的提出者是比柏拉圖更早的德謨克利特。德謨克利特認為宇宙萬物是由處于無秩序、無規律運動中的原子偶然巧合組成的,因而存在無數個可能的世界。柏拉圖反對這種宇宙觀,認為宇宙是被按某種理念創造的,有其本原。理念世界靠理性把握,作為理念世界的摹本的現象世界靠感官認識。柏拉圖的理論中包含兩個世界:可知世界和可感世界,不包括可能世界。
德謨克利特的可能世界概念啟發了萊布尼茲,他的理論在18世紀聞名遐邇。萊布尼茲認為,在上帝的觀念中有無窮個可能的世界,上帝在許多可能的世界里選出了這個世界,是因為這個世界所包含的可能的邪惡最少、最適宜、最完滿。一旦這個世界被選出來,其中的所有事物就必然會是過去和現在的樣子。必然世界是可能世界之一。是具有本體地位的那個世界。
可能世界概念被納入形而上學思考之后,越來越多的哲學家開始發展可能世界理論。模態邏輯學家劉易斯的《論可能世界的復雜性》提出了一個很有爭議的觀點:我們的世界只是眾多可能世界中的一個。“事物本來可以按無數種方式與它們現在的樣子不同”,可能世界是某種現實世界,是獨立于我們語言和思想之外的實體。
至今,對可能世界大致有三種不同的理解方式:以劉易斯為代表的觀點被稱為激進的實在論:以萊布尼茲為代表的被稱為非實在論,以亞當斯、卡爾納普為代表的“可能世界語句集論”支持了非實在論,認為可能世界并不與現實世界一樣真實存在,它只處理命題及其真假關系,是一種技術手段;以克里普克的觀點為代表的被稱為溫和實在論,有人稱為“可能世界狀態論”。克里普克的主要觀點是:“可能世界并不是與現實世界并列的真實存在,真實存在的世界只有現實世界,可能世界是現實世界及其各種可能的狀態。”(臧勇《論模態邏輯中的“跨界同一”》)
上述三種觀點各有道理,但是對可能世界最基本的認識卻有一個共識,現在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清理出這樣幾組關系:可感世界一定可能。可能世界未必可感。可感世界一定可知,可知世界未必可感。可能世界必然可知,可知世界未必可能。這幾組概念的關系在哲學理解上已經不存在什么問題,清楚明了。
康德的二律背反理論提出在邏輯上互相矛盾的兩個命題可以同時為真。二律背反現象表明:邏輯也是有限度的,邏輯會導致理性內部的矛盾。現代量子理論的研究發現量子的特性是多種可能同時存在。這一理論大大地豐富了可能世界理論,在現實世界之外,在我們周圍同時存在無數可能世界。現實世界與可能世界同時為真,且邏輯不可能世界也可能為真。量子理論改變了我們對文學的基本態度,世界是平行、多元的,一個文本是多個世界的疊加,“你能看到什么取決于你想看到什么”,“文本的意義取決于批評家所使用的理論工具”(張新軍《可能世界敘事學》)。同理,作家觀察世界并對世界加以描寫,關鍵不在世界本身是什么樣子,而在于作家用什么樣的眼睛看這個世界。文學的作用并非復制再現一個可感(可見)世界。也非描述世界的必然趨勢,也不止于描述邏輯可能世界,而是對多個可能世界的展開。
必然性指世界一定向某個方向發展的趨勢。現在,必然性用來描述在一切可能世界都必然要發生的趨勢。在實際思維操作過程中,必然世界指世界按因果律一定會朝某方向發展的未來世界或按因果律已經成為現實或歷史的世界。必然世界的概念,必須依賴于這樣一條基本原則: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有它存在的原因,并且已存在的物又會成為原因而導致另一個必然的結果。可能世界理論說明正反命題在邏輯上都可以同時為真,必然性只能是在一定范圍內的必然性。換言之,即使對世界是必然還是可能的判斷這一命題本身,都要取決于觀察者的觀察視角和方法。
作家以一個視角觀察、想像世界,他所觀察的世界相當于一個文本,是多個可能世界的疊加,他的理解受制于他的觀察方式。一旦作品被寫出,作品文本又構成一個文本現實,這個文本又可被批評家看作是多個可能世界的疊加,闡釋結果受制于批評家對文本的理解方式。另一方面,不論是作家還是批評家,理解方式不可能不受到他所看到的文本的引導。即是說。觀察者并非一個完全獨立的主體,觀察者的主體性之獲得,是在與他者的關系中被建構、確立的。在現代批評理論中,他者被視為一種可能的世界(王杰、儀平策《文藝美學的學科定位和發展趨勢研究》),世界由無數的他者組成,也就由無數的可能組成。在可能世界理論的燭照下,歷史、現實、未來都不再被理解為必然,而是變得捉摸不定,不再可靠。用可能世界理論審視中國當代文學,會發現一條作家和批評家對世界觀察方式變化的線索。
二、當代初期二十七年文學的哲學基礎
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前二十七年文學在哲學觀念上受制于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從可能世界的觀點看,這個時期的作家和批評家主要按照萊布尼茲的方式理解現實世界和可能世界。按照萊布尼茲的觀點,上帝因為這個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個而選擇了它,這個選擇是依據善的原則,即道德的必然性而決定的。因此,在這個世界中,所有的現實都是必然的結果。當代初二十七年文學的認識論基礎,與這一思想暗合。
1.將現實世界理解為必然世界
這種觀念大約可以追溯到瞿秋白于1923年11月24日寫的《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一文,瞿秋自從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出發,論述了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的關系。按他的說法,一切歷史現象都是必然的,之所以有歷史的偶然,“僅僅因為人類還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所以純粹是主觀的說法。決不能因為‘不知因果’便說‘沒有因果”’(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二卷)。按這種理解,所有成為現實的都是因果的必然。但是,“不知因果”固然不能說“沒有因果”,但也不能說“一定有因果”。既然因果是未知,如何能夠推導出現實世界就是必然世界呢?瞿秋白的論斷在邏輯上犯了錯誤,其理論本原是對世界普遍因果聯系的承認。“沒有因果”和“一定有因果”之說都不存在邏輯上的問題,但又是可以共存的判斷。康德從邏輯上論證了世界是必然的是正確的,世界是偶然的也是正確的,瞿秋白的論證直接武斷地判定歷史是必然的,與萊布尼茲的可能世界理論是一致的。
在必然觀的指導下,中國當代文學花了大量篇幅來論證現實世界是必然的世界。幾乎在所有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中都可以看到這個世界觀的影子,用藝術的手法表現革命的必然勝利,英雄人物也都充分地相信現存世界是必然如此的。《紅巖》中的英雄都抱著革命必然勝利的信念,堅定不移,終于取得了勝利。這個推論邏輯的問題在于:如果勝利真是必然的,那么即使不要信念,勝利仍然會到來。如果需要信念才能取得勝利,那勝利就不是必然的,勝利是依賴于信念的。推動歷史發展的到底是規律,還是人的意志?終點到底在哪里?從這個邏輯推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令人驚奇的現象:英雄成了上帝。按照萊布尼茲的觀點,在眾多可能世界中,上帝選擇了最完滿的世界成為這個世界;在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中,英雄、人民按這一準則選擇了這個世界。革命傳奇小說是一種將“英雄”和“人民”進行神化的思維方式。
假若我們不承認這個神話,將“英雄”和“人民”還原為人本身,我們又可以看到另一種思維模式。因為歷史是關于人的歷史,推動歷史發展的自然也是人,然而人因為存在自由意志,所以人的一切行為都不是必然的行為,而是自由意志支配的行為。按存在主義觀點,人永遠是自由的,人的自由選擇成就了人自身。另一方面,自由意志與現實世界之間有一種交互影響的作用,現實世界會干擾人的自由選擇。馬克思認為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即人與他者的關系是人存在之根本。即使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意志也是互動的二維之一維,另一維是他人的自由意志。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推動歷史的基點是人的自由意志。既然如此,歷史的發展也就不存在必然,而是人的自由意志相互干擾、影響、選擇的結果。把既成事實看作必然結果的思維,或顯或隱地呈現在十七年文學的敘述之中,給人強烈的暗示效應。
《紅旗譜》講述了三代農民的革命道路。朱老鞏的舊式農民革命被敘述為失敗,被理解為他沒找到正確的道路而必然失敗。朱老忠跨越新舊兩個時代,舊時代的農民式革命的失敗也被理解為必然的失敗。他后來找到了正確的革命道路,導致斗爭的勝利也就被理解為必然,因為有新社會這一事實作為最有力的隱含證據。勝利就是必然,現實就是必然。
同樣的邏輯被廣泛地應用于其他小說之中。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靜的成長、解放與幸福,與盧嘉川的黨派身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正是因為有了正確的思想指導,林道靜才可能走出個人生活的陰影,那個正確的前途才會擺在她的面前。在林道靜面前,等待她的就只剩一條路,因為其他道路都在她的嘗試中被逐一否定。因為現實不需要論證,事實勝于雄辯,所以,除了“現實”這個必然性之外,人的解放不存在另外的可能性。
按照可能世界理論,文學虛構都是屬于可能世界的范圍,因為虛構畢竟不是現實。但是另一方面,十七年歷史小說隱含了一個認知前提:無論在哪一個虛構的可能世界中,結果都是不變的現實世界。所有可能世界中都必然要發生的趨勢就是必然性,所以當代初十七年的經典小說大都把虛構的可能世界導向了必然世界。例如《創業史》讓我們認識到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趨勢,《紅日》向我們昭示了解放戰爭的歷史風云和勝利的必然,《林海雪原》展示了英雄的必然勝利,等等。我們之所以會強烈地感覺到這些小說中有一種必然性,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在這些小說中很難看到偶然性,故事情節大都有嚴格的因果邏輯。好人與壞人的分野是由這些人的本質決定的。而不是由人物偶然選擇造成的結果。
將現實世界理解為必然世界的觀念,不僅在小說中有暗示,在對這些小說進行評介的話語中更為明顯。何其芳在《林海雪原》出版后不久即發表評論文章,認為“如果從更高的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要求,就不能不說這部作品雖然正確地反映了我們過去的軍事斗爭的所向無敵、無堅不摧的總趨勢,然而對于當時的艱苦困難還是表現得不夠”。主要原因是《林海雪原》的描寫“常常是自然的困難超過了敵人給與我們的困難”(何其芳《談“林海雪原”》)。何其芳的意思是,描寫軍事題材的作品,總趨勢應該是“所向無敵、無堅不摧”。何其芳時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所長。他對文藝政策的理解很具有代表性,可見對于軍事題材的處理,結局的勝利必須被處理為必然,失敗是不允許的。另一位叫何家槐的評論者則認為《林海雪原》“太少反映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斗爭,太少反映人民的成長和人民的力量”(何家槐《略談“林海雪原”》),這個評論反映了戰爭必然勝利的原因,這已經成為戰爭小說的一種必要的模式,因而戰爭題材小說是不能存在其他可能性的。而對《創業史》等小說的評價則反映了農村題材小說的政策性要求。例如馮牧在1960年發表于《文藝報》上的文章評價《創業史》說:“正是由于他們的性格所決定的他們的思想和行動,使我們生動地看到了農村階級分化和階級矛盾的鮮明圖景,使我們深切地感到了廣大農村歷史發展法則和走向農業集體化道路的必然性。”(馮牧《初讀(創業史)》)李希凡則說:“而這幅畫卷,所以能獲得那樣豐富的藝術形象的表現。那樣有說服力地展示了五億農民必然要走向集體化的生活道路,就是由于作者并不是一般地描寫這個革命群眾運動的過程……”(李希凡《漫談(創業史)的思想和藝術》)如此觀點的評論在對多數的文學作品的評介中均可找到,在此不用更多舉例,對當代文學初期二十七年的文學作品稍微熟悉的讀者都能體會到這種邏輯。
2.將可能世界處理為必然世界
文學作品均可被理解為虛構,哪怕它有寫實的成分。從敘述學的角度看。幾乎所有的小說都可被視為虛擬敘述者的敘述,因而所有小說都可視為虛構。既然為虛構,它表現的世界就只能是可能世界。但是正如上文所述,當代二十七年的小說又幾乎都在用虛擬的可能世界論證一個必然的世界。這個必然世界不僅是如上文所述的現實世界,它還可以是尚未變成現實的未來世界。
從可能世界的觀點來看,未來的世界只能是可能世界,而不會是必然世界。凡是對未來必然如何的預言,其實都只是一種信念,而不是一個真理。畢竟,誰也不敢保證明天太陽會照常升起。
當代二十七年的小說大多數是歷史題材和現實題材,對未來題材涉及相當少。偶有涉及對未來的信念的小說,也一定是對未來之必然性的堅信。對未來題材的拒絕已經證明了當代初期二十七年小說對可能世界的拒絕。而少數涉及未來展望的小說也一定暗示了未來社會的必然趨勢與走向。《創業史》(第一部)和《上海的早晨》都有未完成的特點。但是都預示了未來的必然道路,如孟繁華所言:這兩部小說“雖然題材和書寫的領域不同,但都是試圖通過文學的形式來完整、全面地表現中國城鄉社會主義改造的艱難、曲折、復雜但一定走向勝利的歷史過程和必然趨勢”(孟繁華、程光煒《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即是說,我們按照既定目標進行改造,勝利又是必然,所以未來的社會形態是必然的。這一邏輯支撐了二十七年大部分的小說形態。
趙毅衡認為,中國的未來小說,除了世紀初十年和最后十年有過未來小說的集束出現之外。其他階段幾乎一片空白。現代三十年只出現過老舍的《貓城記》和沈從文的《阿麗絲中國游記》兩部,當代四十年幾乎絕跡。趙毅衡所說的未來小說,是比較嚴格意義上的未來小說,指敘述者的時間立足點在未來之未來,講述在那個時間點已成往事的未來。(見趙毅衡《可怕的不對稱:中國的未來小說》)從這個意義上說,新中國建國初二十七年的小說中確實找不到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未來小說,但是卻有不少小說表達了對未來的展望。凡是沒有結局的小說,都可以看作是對未來的預期。
許多評論者都敏銳地捕捉住了小說對未來的預期,例如顧松明評《創業史》:“只有組織起來走合作化的道路,農民才有光輝的未來,這才是真正的創業史、幸福史。”(顧松明《中國小說漫話》)1995年至1999年間,“紅色經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等社重印,策劃者和出版者稱:“小說中刻畫的林道靜、盧嘉川、江華等一批栩栩如生的青年知識分子形象,象征著中華民族的未來和希望。”(孟繁華、程光煒《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未來和希望”說得并不具體。但是讀者都知道是什么未來和希望。
對未來、希望之可能視為必然,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是在社會發展道路的操作過程中將這些可能過快地變成現實。在大躍進年代直接將必然的信念提到現實層面就是這種“希望與未來”浮出水面的具體表現。
3.對其他可能世界的拒絕
建國初二十七年文學的世界觀。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規定了的世界觀,規定外的可能世界敘事,不受歡迎,這從歷次文學大批判中也可得到印證。
拒絕可能世界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在小說中首先設定正確與錯誤兩條路線,敘述者愿意花費更多的精力去描寫“正面人物”的言行與內心活動以證明其選擇的正確與合理。同時不愿花過多的筆墨去描寫“反面人物”的言行與內心活動,不深入挖掘反面人物或錯誤路線執行者之所以作此選擇的理由。李準的小說《不能走那條路》表現農村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張栓是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形象,他倒騰牲口,失敗后便想賣地。宋老定是在資本主義路線與社會主義路線之間徘徊的形象,想買張栓的地,最終在黨員兒子東林的勸說下放棄了買地行為,借錢給張栓度過了難關。小說對張栓的心理活動描寫很少。而對宋老定的描寫很多,突出了思想斗爭的復雜性,對土地買賣行為的可能性予以否定。
由于反映農業合作化的小說需要給政治意圖一個合理的解釋,因此都不能解釋其他路線的合理性,政治干預是杜絕表現其他可能世界的最重要的原因。趙樹理的《三里灣》、周立波的《山鄉巨變》都表現農業合作化道路中兩條路線的斗爭,落后分子失敗,農村進行合作化改造,農村幸福生活的前景呈現在眼前,文學批評只能以此為標準。
綜上所述,建國初二十七年的文學作品的總體傾向是拒絕對多個可能世界的展開,未來只剩一種可能,這唯一的可能就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傾向。這種模式的最大缺陷是停止了對未來多種可能的有益探索,從而限制了文學想像,文化因此而失去了創新的動力。三、新時期以來文學敘事對可能世界的展開
新時期的思想解放從對“兩個凡是”的批判和真理標準大討論開始。從可能世界的觀點看,這次思想解放的核心在于否定世界發展的必然性,承認偶然性和可能性。批評“兩個凡是”意味著思想向其他可能敞開,倡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意味著鼓勵對可能世界的探索。這次思想解放,把中國的未來向多種可能敞開,為中國文化注入了活力。
可能世界的打開在文學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因為作為虛構的文學作品本就應該是對可能世界的描述,其生命力正是在可能世界中展開想像、探索可能。新時期文學起初努力做到的是對必然世界敘事模式的否定,對按必然性思維推動的社會發展模式進行反思與批評。
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代表了對歷史進行否定的思潮。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的意義在于,它通過文學故事證明,我們曾經認為必然正確的路線與方向,事實上不利于人的健康發展,并不正確。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打開了一個反面的可能世界:按曾經的路線,可能導致一個事與愿違的結果。改革文學的思維模式有質的飛躍,因為改革文學不再致力于證明過去的正確或錯誤,而是提出一系列具體的問題,多種可能擺在面前,做出正確的抉擇反而成了這個時代人的痛苦與難題。改革文學是新時期文學的一次重要變革。因為它開始向未來敞開。張炯的判斷很有道理:“把‘改革文學’與‘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乃至‘尋根文學’等量齊觀,是不恰當的。它將是一個更為恒定的文學現象。它所反映的不僅是過去十年,而且是未來數十年間中國向有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邁進的歷史進程。”(張炯《張炯文存》第3卷)“改革文學”標志著新時期文學對可能和未來的探索、疑惑、展望等主題,是新時期文學真正劇變的開始。蔣子龍是改革文學的開拓者,他的多部小說都貫穿了這一思想特征。《喬廠長上任記》的要點在于,喬光樸在改革過程中面I臨著無數的矛盾,生活極其復雜,未來不會只有一種或兩種結果,而是可能有多種結果。《赤橙黃綠青藍紫》寫出了改革的豐富多彩的特征,表達了人生應有的要義:“人應該是全顏色的,單色不好。”即是說,人應該有多種生存的可能,人與人應該不同,同一個人也可以有多種生存方式。
如果說改革文學展開了現實與未來可能。那么尋根文學則展開了文化可能,先鋒小說敞開了人性可能。此處不得不提及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在1980年代的全面傳播,具有極為深廣的顛覆作用。武俠小說展開了一切可能:歷史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人性可能呈現多種狀態;人的武功可能極為高強:結局可能很難預料。因為武俠小說把現實世界挪移到江湖世界,于是便為現實世界開拓了無窮可能。武俠小說的純虛構性質對現實主義傳統形成了最大的挑戰。因為武俠小說的受眾面遠遠大于同時期其他類型小說,所以其中的虛構情節塑造了文學讀者對可能世界的接受傾向性,以致他們不再愿意被一個必然的未來束縛住想像的翅膀。這導致一個事實上的結果:從1980年代中后期至今,最具轟動效應的小說往往是那些在歷史、現實中不可能的、帶有更多虛構性的小說。歷史成了“新歷史”,現實成了“新寫實”,魔幻成為文學新寵。可能世界敘事在新時期的全面發展,以新歷史小說和未來小說的出現為標志。以魔幻小說的全面興盛為結束。
懷疑現實往往以懷疑歷史為開端。在中國歷史上,通過歷史否定現實的方式常有兩種:一是復古,二是否定。古人常用復古主義,今人常用批判思維。新文學以否定歷史開端,以戲說歷史為其高潮。魯迅是現代文學的一個樣本,以《狂人日記》否定歷史始,以《故事新編》戲說歷史終。新時期以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否定歷史始,以新歷史小說的蓬勃發展終。莫言是這個轉變的受益者,也是推動者。作為新歷史小說的樣本的《紅高粱》(譚偉平的《現代中國文學教程》認為,《紅高粱》是“新歷史主義小說在中國的發先聲之作”),不再致力于宏大的歷史畫卷和歷史必然性的描寫,而是在歷史中還原與人的野性相關的各種細節。莫言的所有小說,都不再被必然世界束縛,而是在可能世界中翱翔。歷史被人性化、魔幻化、民間化,宏大的必然世界被細微的可能世界遮蔽。人被拉人各種可能之中進行嚴刑拷打,逼問其罪惡與偉大,凡人的神性被重新塑造出來。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是新歷史小說的另一個樣本,人物玩世不恭,但他卻能夠用銳利的眼睛觀看世界,質疑歷史,歷史被畫上花臉,供人們取樂、嘲笑、鞭撻,歷史不再神圣,變成了囚徒,成為敘述的一個角色,而不是主體。對待歷史的第三種態度是“戲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戲說歷史漸成風潮,大批古裝電視劇開始重述帝王將相王孫貴族,《宰相劉邏鍋》、《康熙微服私訪》、《還珠格格》、《鐵齒銅牙紀曉嵐》、《漢武大帝》、《戲說乾隆》等“戲說”歷史系列電視連續劇陸續上映,反響熱烈,這類作品揭去正史嚴肅的面紗,給歷史以另外的解釋,帶領觀眾在可能世界中遨游,給歷史抹上輕松的喜劇色彩。
對歷史的考問、嘲弄、戲說、神魔化、細節化,都是對歷史的可能理解。至21世紀,“偶然的歷史”導致如今的現實也被作家思考。何大草《所有的鄉愁》描寫了一個情節,深刻地揭示了歷史的荒誕性: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乃是因為一個驚慌逃跑躲在屋梁上避難的木匠尿急淋熄了清軍的大炮焾子。歷史被一泡尿改變。無數的偶然最終發展為現實的世界,現實中的偶然終將成為令人捉摸不透的歷史,還將發展為更加令人捉摸不定的未來,人類歷史哪有必然?歷史沒有必然,但是有可能。正是今天對可能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會造就未來。沒有人為我們提供可能世界,世人將面臨選項的匱乏,未來也就沒有了可能,對可能世界的探索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
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的幾篇典型的未來小說,是對未來可能的探索,也是對現實世界的諷刺。王小波的《白銀時代》(1994--1997),將敘述時間設定在2020年,講述2010年和2015年的故事。雖說未來敘事很多zl4LjZefphxoyYcJciESKg==時候只是玩了一個時間游戲,想說的仍然是關于現實的隱喻,但是時間畢竟設定在未來,它講述的一定不是真實的故事,而是一個關于可能的故事。《白銀時代》關心的,不是未來世界將如何美好光明,而是對未來烏托邦的反動,“是在完成一個關于烏托邦的描繪及批判”(韓袁紅《批判與想象:王小波小說研究》),“都是秩序混亂的反烏托邦”(趙毅衡《可怕的不對稱:中國的未來小說》),即是說,關于未來烏托邦之必然,被王小波用既輕松又嚴肅的故事盡數瓦解。未來不美好的可能敲響了現實的警鐘。如果說魯迅用沉著的態度預言了未來必然不美好,那么王小波則用輕松的態度預言了未來可能不如意,如趙毅衡所言,“既然能夠找出原因,走向未來之路,并非絕對不可改變”(趙毅衡《可怕的不對稱:中國的未來小說》)。即是說,魯迅的絕對悲觀導向必然絕望的世界,而王小波的可能絕望的世界引領人們改變現實以避免進入魯迅預言的未來。同樣是對現實的悲觀,兩位文學家卻采取了相反的敘述態度,這是對未來世界的兩種認知方式在文學上的呈現。
王力雄的《黃禍》(風云時代出版公司,1991年)以匿名方式發表,表現未來生態災難,中國成為世界中心,中國的解放使全世界有了未來,中國為世界提供發展模式,與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遙相呼應。梁曉聲的《浮城》(花城出版社,1992年)虛構1999年的故事,一座中國沿海城市漂向大海,城內失控,各色人等上演謀私利丑事。浮城漂向日本,日本拒絕城中人登陸。中國軍艦來救,城人拒絕回國,因為他們相信浮城正在漂向美國。《浮城》類似科幻小說,諷刺上世紀90年代出國熱潮。喬良《末日之門》(1995年)是一部軍事外交未來小說,設想中國軍隊有強大的未來作戰能力,所有強國在混亂中都不得不向中國求救,中國軍官成為世界級的大英雄。虹影的《康乃馨俱樂部》、《來自古國的女人》、《千年之末義和團》作于1993年至1995年,寫的是1999年的上海。三部小說合稱“女子有行”,以“我”的視角審視中國女性在未來世界的命運。曾經的“實踐的烏托邦,榨干了中國作家的想像力”,但是20世紀90年代的未來小說卻集中地體現了中國作家想像力的大爆炸,“未來小說之功用,恰恰是荒唐背后的認真,在不可能世界中構筑某種可能。”(趙毅衡《可怕的不對稱:中國的未來小說》)
“在不可能世界中構筑某種可能”是未來小說的基本思維模式,在現實世界、虛擬世界、歷史世界中構筑可能遂成為1980年代以來小說敘述模式的最大變化,玄幻小說是這個敘述模式變化的產物。在玄幻小說中,一切不可能都成為可能:時空可以穿越,人類可以修仙,歷史可以改寫,現實可以改變,未來可以預知。在玄幻小說中,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一切皆有可能,其中包括邏輯不可能。玄幻小說正是“可能世界”大爆炸的產物。
對于潛心表現現實的小說。也沒有被必然世界的敘述模式束縛。現實的多元取代了一元,生活突然變得無比豐富。鄧曉芒評論新世紀作家的創作時說:“對使他們困惑的問題,他們可以以性命相拚,但更多地是訴之以清醒的理智和邏輯,是創造語言去建構一個超越現實之上的‘可能世界’,是堅持‘應有’而不和‘實有’相妥協。”(鄧曉芒《論21世紀中國文學的前景》)這大約就是新世紀文學家對世界最基本的認知態度。底層文學被新世紀批評家賦予了最具現實精神的稱謂,但是多數底層文學作家從來沒有認同一個“實有”的世界。一方面,底層文學展示了現實世界中多元化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底層文學家展開了對現實生存空間最強有力的批判態度,堅持“應有”的生存空間,以期鼓勵人們探索未來生存空間的可能。
對于新世紀小說而言,時間不再是重點。小說的功用,不僅表現為批判、影射、設想、娛樂、教育等常規功能。小說已成為解放人自身最有效的方式。
四、結論
總而言之,新時期以來文學的最大變化,就是無論在時間還是空間維度上,都逐漸允許多種可能性的并存。這個轉變可以視為對可能世界的認識論從萊布尼茲模式向劉易斯模式和量子論模式轉變的結果。因為世界本來可以有很多形態。所以想像力可以被無限挖掘。又由于觀察視角與方式不同也可能導致事物呈現出不同形態,所以現實世界與可能世界是“并在”的關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可能世界敘事的興盛,打開了國人的眼界、思維,在建構新的文化形態、引領我們走向未來的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可能世界敘事不僅是認識論,也是本體論: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方式,決定了我們的本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從必然世界敘事向可能世界敘事的轉變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嬗變的核心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