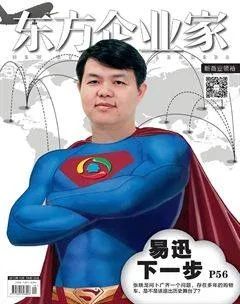多看:“倒戈”亞馬遜



多看位于北京五環外媒體村的辦公室里,每個人都忙忙碌碌。等在公司前臺的訪客幾乎占滿了整個房間,沒有一間辦公室可以空出來為下次可能的商業合作談判提供場地。
4月與小米合并的消息傳出,多看即浮出水面,多看品牌因小米盒子而為眾人所知,卻沒有太多人了解,這支團隊最初的方向和未來最倚重的業務都是數字閱讀,好在,近一年的數據讓他們對這個方向開始有信心。
金牌書
根據多看提供的數據,2012年底,多看閱讀的安裝量600萬,付費用戶只有3萬。而2013剛剛過去半年的時候,多看安裝量數據翻了一倍,付費用戶卻同時增長到了14萬,日銷售額接近5萬元。這本來是多看期望到今年年底達到的目標,提前半年達成,過程順利得讓團隊覺得出乎意料。
但仔細想來,這一切的發生并非沒有先兆。過去的這一年當中,不止是多看,亞馬遜、豆瓣等擁有資源優勢的平臺紛紛開始做起了付費閱讀的生意,長期以來存在于數字出版領域,關于“中國用戶對內容沒有付費習慣”的論斷也被證偽。一切發生的源頭,是傳統強勢的內容資源壟斷方出版社調整心態,將同步的新書、好書版權,逐漸向數字閱讀平臺開放。
多看書城第一批上架的書只有79本。“我曾經為了拿一本書的版權,給出版社管版權的小姑娘送過兩張電影票。”回憶最初與出版社談合作的過程時,多看閱讀負責人胡曉東說。還沒人知道多看是誰時,每拿一本書的版權,都十分困難。而現在,多看6月已經擁有了7800多本書,7月就上萬,而且每一本書都經過精致排版,被稱為“金牌書”。
將制作“金牌書”的過程從手工化轉為流程化和工業化的同時,又不影響書的細膩感和體驗,在過去一年當中,花費了多看團隊最多的時間和精力。從前一本書花十幾人團隊一兩個月時間,現在一年開發兩三萬本新書也不算難事。
可如果僅僅是將簡單的紙質書電子化,并不能代表數字閱讀。此類嘗試很早就在公共圖書館和文獻數據庫領域有所成就。多看想要做的數字閱讀的形態,是將人與屏幕文字的聯系變得更加平等、人格化、個性化,利用屏幕的特質,引用更多類似視頻、超鏈、查詢和搜索等元素,建立真正符合屏幕閱讀的內容體系,從根本上改變做書的方式。
在多看出品的雜志上,便充分體現了這樣的思路。多看的所有雜志都是紙上看不到的,用胡曉東的話說,“多看在做所有內容提供商的試驗品。”
比如,與《人物》雜志的合作,會有直接嵌入文本的視頻,以前紙質雜志的解決方法是放一張光盤;將“36kr”上的內容制作一本全部用超鏈的雜志,內容可以相當于紙質雜志的20倍;與《北京紀事》的合作,是拆開了上百本過刊的內容,重新整理,再分《北京紀事之收藏篇》、《北京紀事之胡同篇》、《北京紀事之老北京胡同篇》。
也有不少由這樣的思路誕生的新書策劃,最經典的一個案例是在電影《西游降魔篇》上映前,多看就與上海貝貝特合作策劃了一本之前并不存在的書《兒歌三百首》,貝貝特三天之內提供了內容,第四天,新書就上架。
因此,多看和豆瓣等數字閱讀的平臺商為電子書的定價嘗試著一套完全不同于紙質書的體系。沒有紙質書最基礎的印制成本和發行成本,電子書最在意的是能夠覆蓋到的人群的數量,而非單本的定價。只要滿足出版方的限價,數字閱讀平臺上,即使是新書,定價也只有紙書的三到四折,動態的收益再與出版方三七分成,這幾乎是行業內最高標準,但對單個平臺而言,仍屬于合理價格區間。
結束“寄生”
多看最初的成名只局限于小范圍內。當時,亞馬遜的Kindle一直沒有以正式渠道進入國內,流傳在市場當中的Kindle原生系統又非常不好用,多看團隊就在破解原生系統的基礎之上做了可以在同一設備之上獨立運行的多看系統,并推行“精品閱讀時光”的概念。但當時,團隊行事低調,很大程度上,也因對未來處于迷茫期。
曾有一段時間,他們想完全定位于技術開發,委身于出版社,做紙質圖書電子化方面的技術支持。但在溝通過程中,發現他們所秉承的精品閱讀概念,強化閱讀體驗的點都很難得到認同。
后來,他們看到了利用多看系統在Kindle系統上看書的用戶不止對內容有需求,還有強烈的評論、參與、和作者交流的意愿,他們認為,移動設備會讓閱讀行為從個人行為轉化為社會化行為,所以有了后來“多看書,多交朋友”的口號。
這樣用社會化閱讀的概念閱讀之后,很多事情發生了變化。技術之外的環節,多看把握著“信息”和“話題”兩個關鍵詞在移動互聯網上做推廣和營銷,沒有在廣告上花過一分錢,就達到了很好的效果。
“棱鏡門”事件爆出之后,多看馬上重做了一套奧威爾的經典書,其中包括《1984》和《動物莊園》,不僅這套書每天都能有幾百本的銷量,還同時帶火了涉及到民主和制度整個一大類的書。
這批自稱國內“最了解Kindle、最熟悉亞馬遜模式”,卻走向與亞馬遜模式完全相反的路徑時,受到不少質疑。雖然他們認為,Kindle上的電子書不僅內容來源受限,它的發展方向也與人類的閱讀習慣發展相反。屏幕讓人在獲得體驗方面得到了與之前太多不同點,從黑白到彩色、從單一媒體到富媒體是不可逆的習慣,更關鍵的是,現在的屏幕設備越來越易于攜帶,會讓Kindle變得越來越小眾。
數據證實了他們的判斷。自今年4月與小米合并之后,有了在小米手機上的預裝,多看的App激活量大概有小米手機銷售量的三分之一。但這并不是增長最主要的來源。從去年12月起,每個月近1萬元的銷售額,來自iOS平臺的用戶占50%,另外50%則是Android與其他所有平臺的總和。現在多看每日平均5萬元的銷售額,70%來自Andriod手機、20%來自iOS系統,web端與Kindle的總和只剩下10%。這樣的增長,也與移動支付技術的日臻成熟十分相關。
而多看就將自己定位于數字出版新的產業鏈當中的技術環節,堅持完全不碰內容和版權,只為合作伙伴的內容提供其他方面的支持。胡曉東說:“對于版權方來講,獨立犯錯不容易,技術投入大;對于多看,獨立做內容開發成本也高,但是如果兩方聯合,試錯的成本就會變得很低。與做人的道理一樣,自恃過高會做出盲目的判斷,自視過低則會市區機會,逐漸消亡。做準確的判斷才是最重要的。”
胡曉東將多看形容為數字閱讀的“不可知論者”,用完全不同于做紙質書的思維創造的新模式,有可能會為出版業帶來新的繁榮,并且開創一個比紙質閱讀大得多的市場。但從今天的視角判斷明天的市場會容易犯錯,因此,多看不做超過3個月的規劃,只按照對于大趨勢的判斷,把事情一件件做好。
對于所謂的“競爭”,多看也并不關注。事實上,今年京東、淘寶和當當等平臺做電子書的嘗試,反而對多看的銷售有了正面促進的作用。用戶的需求被創造出來之后,往往會來選擇多看的產品,他們的技術更成熟,有近萬本書的選擇余地。
按照現在的增速,到今年年底,多看會超過50萬付費用戶,日銷售額做到20萬元。“一旦模式建立起來,從50萬到500萬也只會是時間問題。”胡曉東說,“這一天什么時候來,不知道,我們能做的,就是有錢,堅持活到那個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