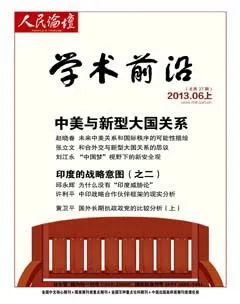中美與新型大國關系
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格局醞釀深刻復雜變化。主要大國間的交往與合作日趨頻繁,但誤解、摩擦、指責、紛爭也不時交替。傳統大國關系理論由于在化解大國沖突矛盾、增進互信共識上功效甚微,已經不能滿足時代需求,亟待反思超越。
習近平主席在6月7日的中美元首會晤中明確提出,中美兩國要走出一條不同于以往“大國之間必然對抗沖突”的新路,雙方應該努力建設新型大國關系。
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需要找準突破口與“演練對象”。中美兩國聯系緊密,利益交融,是不同形態、不同制度、不同發展階段的典型代表。兩國在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基礎上開展“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尋找共同利益匯合點,不僅能豐富大國關系理論體系,而且還為其他大國發展處理雙邊關系奠定理論基礎與實踐經驗。
中國的國家利益、政治制度和戰略走向決定了中國不會重走“大而求霸”老路,不會處心積慮與既有強權為敵。中美關系本質是互利共贏而非零和對抗。共同面臨的機遇合作與風險挑戰,使雙方形成 “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同體關系。
傳統國際關系理論認為崛起國必然通過戰爭手段挑戰既有霸權,而霸權國必定以暴制暴,雙方激斗不休,從而陷入 “大國政治的悲劇”。這種思維邏輯,是建立在狹隘的二元對立分析基礎上,過分關注自身利益,忽視大國道義責任,心態猜忌偏執,極易引發兵戎戰禍。
在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傳統大國影響力相對式微的歷史背景下,維護世界和平、處理全球問題,需要大國攜手合作和共同行動。各國在應對經濟危機、處理共同威脅、打擊恐怖主義、開發新型能源等諸多領域擁有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間。同時,新興大國與傳統大國之間根本性利益沖突日趨減少,合作空間日益拓展。不同社會制度和發展水平的大國互相提供發展機會,實現全方位、多層次的互利共贏,這已成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內在動力與前提基礎,而合作共贏也成為大國之間處理彼此關系的共同蘄向。
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需要以和平方式實現大國認知和定位的變化調整。其中成敗關鍵又取決于能否實現由基于戰爭沖突的“權力政治”向基于制度機制的“規則政治”轉變,尤其是各國在相互磨合和博弈過程中能否遵守已有共識和基本原則。首先,必須要確立努力方向;其次,要探索實現路徑、充實理論內涵和完善互動形式。各國應在深化合作的基礎上,尊重相互關切,尊重對方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權力,不以一己之價值理念強加于人,倡導平等多樣,不斷增進理解、凝聚共識。
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對先前大國關系的修正與提升,順應人類社會發展趨勢,符合國際成員共同利益。只要大國摒棄“一家獨霸,有我無他”、“國強必霸,兩強必爭”的霸權思維與猜忌心理,真誠理性地對待一切后來者與競爭者,不失風度地營造包容開放、雙利共贏的環境氛圍,摒除“意氣之爭”,抓住合作機遇,則大國合作與機遇之路,必然越走越寬,利益福祉自然可期。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編輯部
在中美共同利益推動下,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具有現實可能性。在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進程中,中國應將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構想,運用到處理與發展其他大國關系中去,并通過與其他大國構建新型關系推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建立。
——趙曉春
“和為貴”、“保合太和”的理念根植于中華民族文化土壤,直接影響了中華民族對外交往的思維和方式。實現國與國的和合,人與人的和睦,人與社會的和處,人與自然的和諧,人類社會才會實現共同繁榮,中華民族才會實現偉大復興。
——張立文
可持續安全不僅重視國家安全,而且重視公民安全。可持續安全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強調安全環境與生態環境的統一性、國內穩定與國際和平的統一性、國家主權與公民人權的統一性,是建立在世界多樣性和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安全模式。
——劉江永
西方中心觀念、意識形態化的冷戰觀念、傳統的“霸權轉移”觀念,都是反時代潮流和反進步的,勢將走向沒落。美歐日終將認識到,21世紀不再是一國能獨霸世界的世紀。中國既無能力、亦無欲望通過武力統治世界。
——潘 維
對于儒家王道理想的回望,是要通過對于王道與霸道的爭議的回顧,使道德和正義重新成為判定社會秩序優劣的基準。重提儒家的王道理想,發掘儒家思想的普遍性面向,是建設新的中國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部分。
——干春松
對于儒家王道理想的回望,是要通過對于王道與霸道的爭議的回顧,使道德和正義重新成為判定社會秩序優劣的基準。重提儒家的王道理想,發掘儒家思想的普遍性面向,是建設新的中國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部分。
——干春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