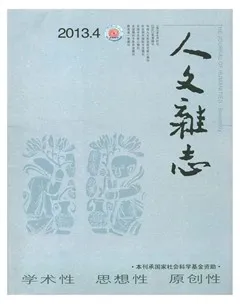蘇格拉底“舍生取義”之處境
內容提要 蘇格拉底因虔敬而決斷,畢生踐行神的使命,以討論知識為手段,旨在驗證神的讖語,由于實踐或行為的必然性與知識或邏輯的必然性相沖突,他背離了公眾意見或知識所建構的規范,因而陷入孤獨而赤貧的處境之中,而公共知識強大而隱蔽的力量注定了蘇格拉底必死的命運,蘇格拉底對于死的泰然任之并非功利或價值選擇意義上的“舍生取義”,而是虔敬處境中對神旨的遵從,對于我們現代人有意義的,是其對人的有限性的透徹領會。
關鍵詞 處境 決斷 公眾意見 虔敬
〔中圖分類號〕B5022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3)04-0014-07
蘇格拉底事件通常被描畫為“舍生取義”的典范,據稱他曾得罪過民主派和寡頭,更重要的是,他為了追求“美德”、“正義”、“勇敢”等“定義”而與眾人辯論,因樹敵甚眾最終被判以死刑。按照傳統哲學史的一般描畫,他對定義的追求在柏拉圖那里轉化為更加客觀化的“理念”或“相”,到了中世紀和近代又被轉化為對更一般化的“共相”、“類”,最終直至“規律”、“普遍性質”等知識的訴求。因此,蘇格拉底追求定義就是近代追求普遍知識、尋求確定性之肇始。比如尼采抨擊現代性而提到蘇格拉底時就是這樣認為的,因此才有他所謂的“偶像的黃昏”。在知識論背景下理解,蘇格拉底事件起因于追求真理,而真理本身到了近代同樣被知識化,“科學”的形式是本來就客觀存在著的真實,“哲學”思辨的形式是人類無窮建構并接近著的理想,蘇格拉底就是為了弘揚正義或追求這樣的真理而喪命。同樣的解釋我們也給予布魯諾,說他為近代科學而獻身。然而,這是否只是“我們”的“事后”解釋,而一切科學研究都只能是密西發的貓頭鷹,黃昏時才起飛?決定蘇格拉底之死是否還有其他“因素”,而這些“因素”不是事后知識性分析和解釋所完全能夠涵括,但又具有其非邏輯、非知識的、當下的某種必然性,就像古希臘人所懼6bb3f9718accee3e2b81a1185d930bc5怕或崇拜的命運。列奧斯特勞斯曾說“任何一部柏拉圖對話中的討論,都只是對話的一部分。討論、言語、logos(邏各斯),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則是ergon(行)、行為、行動、對話中所發生的、角色在對話中所做的和所遭受的。logos可以結束于沉默,而行動則可以揭示言語所遮蔽者”。①我們根據通常排在柏拉圖對話最前面的《游敘弗倫》《蘇格拉底的申辯》《克力同》三篇,被認為是蘇格拉底本人的思想,緊扣文本,進入蘇格拉底在事件中的當下“處境”,或許能夠發現更多。
一、蘇格拉底的孤獨處境
《申辯》篇的第一句話,甚至第一個詞,就為我們暗示出一種孤獨無助的處境。“雅典人啊,你們如何受我的原告們的影響,我不得而知;至于我,也幾乎自忘其為我,他們的話說得娓娓動聽,只是沒有一句真話”。②③⑤⑥[古希臘]柏拉圖:《蘇格拉底的申辯》,嚴群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51、67、67、68、58頁。第一個詞是用希臘語的呼格表達的:“雅典人啊”。這樣的一呼,勢必產生一問,蘇格拉底本人是誰?他不是雅典人嗎?后面他也緊接著說:“至于我,也幾乎自忘其為我”。由此可見,此時要對雅典人申辯的蘇格拉底,已經超離于雅典人之外,而雅典人是一個政治概念,這就意味著,他本人已不再是雅典城邦公民了。我們知道,西語“政治”一詞就來自希臘語“polis”,即,城邦,原本就是指城邦中的公民參與統治、管理、斗爭等各種公共生活行為總和,簡而言之,與大家一起生活,作為公民而不僅僅是個人。在這種共同生活中,人們建構各種狹義的政治制度、倫理規范、知識體系等公共的框架。而這種知識化建構一旦形成,各種具體事件、情況或對象只有在符合建制的情況下,才可以得到解釋和把握。傳統哲學作為存在論,只不過更上一層,從所建構的知識整體體系出發解釋具體事物之存在。亞里士多德把人定義為“政治的動物”,就是說,人首先是城邦的動物,符合公民標準,比如到一定的年齡,認同并遵守城邦的倫理、法律、政治規范和宗教信仰等,廣而言之,被公共知識所規范者,我們將其認定為人。這就是人的社會化,同時也可以說是知識化的認定。
申辯的蘇格拉底既然自絕于城邦,那么他是誰呢?他自稱是馬虻,與雅典人對立的人,“象馬虻粘在身上,良種馬因肥大而懶惰遲鈍,需要馬虻刺激”。②然而,這個令人討厭,不合規范的馬虻,與雅典城邦和雅典人對立,卻是為了讓整個城邦警醒而不至昏睡,“你們如果殺了我,不易另找如我之與本邦解不解之緣的人”。③但如果誰要與城邦、與公眾保持這種若即若離、藕斷絲連的微妙關系,他所面臨的一定是與眾人對立的孤獨,以及與財產無緣的貧窮。如果我們聯想一下柏拉圖的洞穴比喻,我們就會意識到,這樣的人無非就是類似于逃出洞穴的自由人,或者說,哲人。這里要注意的是,哲人切不可理解為我們現代人腦海中分工了的專業哲學家。哲人“單獨”走出洞穴看到了真理,他的處境是孤獨的,但是幸福的,他本不愿意回到洞穴中與陰影或只識陰影之人為伍。而如果他突然又意識到自己的公民身份,毅然返回洞穴試圖解救囚徒時,就必然遭受囚徒們的懷恨和敵意。《理想國》中描述到:“要是把那個打算釋放他們并把他們帶到上面去的人逮住殺掉是可以的話,他們不會殺掉他嗎?”——“他們是一定會的”。[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275-276頁。脫離了眾人的孤獨者還必然要與貧窮相伴,因為社會關系本身就包含著與物的各種法權關系,脫離社會關系同時就意味著不得不與物、與財產無緣,淪為真正的孤獨,絕對的赤貧。柏拉圖《理想國》里面所對哲人王的要求,就是缺衣少食,沒有財產,甚至無妻無子的絕對孤獨者,據傳,與蘇格拉底的實際生活所不同的,無非就是有妻子和兩個兒子。因此,當他為自己被誣陷與智者辯護時,蘇格拉底說“告我的人……說我索要報酬。我想,我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我說實話,那就是我的貧窮”。⑤那么,蘇格拉底處境為什么如此孤獨呢?因為他背離了城邦和大眾,不顧家庭、城邦等公共性的義務而進行了一種本真的決斷,“為了這宗事業,我不暇顧及國事、家事;因為神服務,我竟至于一貧如洗”。⑥這就和柏拉圖所描寫的最終意識到自己的公民身份,深明“大義”而返回洞穴,“試圖”或“為了”解救囚徒的哲人王略有不同。而蘇格拉底以獨特方式所踐行的、直至為之獻出生命的所謂“事業”,以廣義知識眼光看,恰恰可能是不務正業,那就是:敬神,以實際行為去侍神。
二、虔敬所導致的被動決斷
蘇格拉底受審前,在王宮前廊遇到了游敘弗倫,據說是一個經常被人譏笑的占卜者,《游敘弗倫》篇就是向此人討教“虔敬”,因為蘇格拉底被指控的首要罪名就是慢神。按照通常的說法,本篇中蘇格拉底是在追求虔敬的“定義”或知識,并且和其他對話一樣無結果。但實際上我們認真閱讀就不難發現,對話中恰恰處處表明,虔敬根本就不是知識,雖說其中也談到:“虔敬是事神之術”,⑧[古希臘]柏拉圖:《游敘弗倫》,嚴群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0、31頁。“我懂得,似乎是指對神的侍應”。⑧但本篇主要傳達的是一種神人感應的關系,以及人在這種關系中雖有主動,但主要是被動的處境。游敘弗倫對蘇格拉底何為“虔敬”的第一次回答絲毫不假思索,斬釘截鐵:“我說虔敬就是做我方才所做的事”。②③[古希臘]柏拉圖:《游敘弗倫》,嚴群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7、13、15頁。也就是,此時此地,當下所做之事,用不著思考,無需邏輯。遺憾的是:按通常傳統的知識性理解,蘇格拉底對話最初的答案往往最不具“真理”性,就像黑格爾《邏輯學》的第一個概念“存在”是最抽象、最貧乏的。可是在《游敘弗倫》篇里,討論“虔敬”最關鍵的部分,則首先引用“攜者與被攜者,引者與被引者”之間的關系,意在表明攜著與引著,較被攜著和被引著的優先關系,由此引申神人感應關系中神人的不同角色。神在這種關系中處于絕對的主動地位,這表現為“見喜于神者”先于“神所喜者”,意思是:神所喜愛的東西,不是因為那東西本身,或其某種性質、功能而招神的喜愛,這樣,神的意愿將被外物所牽而處于被動,而是反過來,只因其被神所喜愛,所以那個東西才是招神喜愛的,或者說,那事才是好的、善的等等,這樣,神具有完全的主動性。這里和康德《實踐理性批判》中的思路一致,并非某事物因本身之善惡而決定意愿,相反,是理性決定了意志之所指是善還是惡。于是,人的虔敬是否被神所喜愛,人自身毫無決定權,人只能以虔敬的實際行動,消極地承受神之喜愛,在這方面,人完全處于被動。但對話中同時,甚至更早地也強調了另一方面,當下的“虔敬”先于“見喜于神者”,這就把人的主動性彰顯出來了,就是說,人,不因神喜,或首先不考慮“為了”見喜于神而虔敬,我直接就“能”以實際行動而虔敬,這是“見喜于神”的前提,而不用挖空“心思”、動用“理性”去討好神。但這種主動無疑是以前面提到的被動為前提的,換句話說,我也“只能”主動地虔敬,是否最終真的“見喜于神”,則絲毫不取決于自己。
除被動特性之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在神人感應關系里面,從神的角度看,神所喜歡的東西沒有道理可講,嚴格說來,不是因為……而喜歡,而是無緣無故,那東西被神喜歡,同時就“是”其所喜歡的東西,這里雖然也可以、甚至通常用“因為……所以……”這樣的關聯來“表述”,但并不是嚴格的邏輯的、知識性的推論,正如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一樣。另一方面,人的虔敬本身就具有獨立價值,并不是考慮“因為”虔敬是神所喜者,“所以”我虔敬,那樣就成了康德所謂的“偽侍奉”。虔敬就是無因果的虔敬行為本身,人切身地、直接地、當下地“進入”或“處于”這種處境之中,不做功利的、價值的、倫理的,一句話,知識性的考慮,先思考、后行動,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喜見于神。進入或處于這種處境,對于人來說就是一種決斷,而且是“被動的主動”決斷,盡管決斷本身從人本身“下決心”方面意味著主動,但比起人的日常知識性主動建構來,決斷更多的是被動的、虔敬的,是實際的被動―主動的“辯證”行為本身,而個體的實際行為有時與公共性的理論思考或規范相悖,顯得不近常理或不合邏輯。
三、背離大眾知識與知識的隱蔽力量
全部這三篇蘇格拉底對話中,或許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就是“大眾的意見”,從公眾意見中抽離出來,就意味著反常,而抽離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恰恰就是決斷,這種決斷在蘇格拉底那里由虔敬所引導。柏拉圖洞穴比喻中的囚徒們譏笑返回洞穴的自由人,說他弄瞎了眼睛,看不見“最真實”的東西——陰影,判斷不出最通常的規律。《游敘弗倫》中也描述到:“我了解了,蘇格拉底;因為你說神時常降臨告誡于你,他便指控你革新神道,到法庭誣告你一番,他曉得這一類誣告易入大眾之耳。我呢,當我在公庭上說些有關神的話,或預言未來的事,他們便譏笑我,說我發瘋了”。②“發瘋了”就意味著不近常理、反常;“在公庭上說”就意味著常理是公共性的、大眾的,因此“易入大眾之耳”,宣稱“神時常降臨”就意味著“神”道道的。按照《游敘弗倫》篇中的描寫,當蘇格拉底得知游敘弗倫控告其老父時,就連他這個不近常理者也驚嘆到:“你的父親,你這個好家伙”!——“海辣克類士!確實大多數人不知義理何在;我想此事常人不能做的恰如其分,唯有大智高識的人才能”。③這段對話背景是,游敘弗倫的父親將一個醉酒殺人的兇犯綁起來投入溝中,并及時差人去上報,請示上方如何處置,結果兇犯意外死亡,而游敘弗倫卻因此“大義滅親”,控父殺人,這完全違背希臘倫理甚至我們現代人的一般常理和知識。于是,愛“智慧”的蘇格拉底才認為游敘弗倫一定有過人之處,認為他虔敬的無以復加,纏著他追問何為虔敬,“你對虔敬與褻慢如沒有真知灼見,就不至于為一個庸奴,控告老父殺人”。[古希臘]柏拉圖:《游敘弗倫》,嚴群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5頁。他認為,游敘弗倫既然切實地做出為子訟父這種不可思議、知識和邏輯無法企及的事情或行為,一定是有一種另外的力量,盡管叫做“真知灼見”,但肯定不同于一般知識,是不是對神“虔敬”使然呢,由于他自己被控不敬神,所以希望了解一些與知識不同,但卻比知識更真實、更直指人心的某種力量。
決斷的力量雖然對于個體真實而有力,但這樣的“切身”行為背離了大眾所辛苦或苦心建構的知識及其社會規范,相比之下,大眾意見力量強大無比,與大眾知識對抗將付出慘重代價。《克力同》篇描述蘇格拉底入獄并即將行刑前這樣說:“但是你瞧,蘇格拉底,大眾的意見也不得不顧,當前的處境顯然證明,他們能為祟,匪小極大,如蒙他們關顧一下”。⑧[古希臘]柏拉圖:《克力同》,嚴群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99頁。任憑蘇格拉底申辯,通過民主表決最終還是消滅了他。除了力量強大之外,公眾意見還有隱蔽的身份,這使其更加可怕。《申辯》篇中描述得入木三分,“在你們以前,積年累歲,已有許多對我的原告,說些毫無事實根據的假話。安匿托士等固然可怕,這批人更可怕,我怕他們過于安匿托士等,……請你們記住,如我所說,有兩批原告,一批最近的,一批久遠的;再請你們了解,我必須先對第一批答辯,因為他們先告我,并且遠比第二批強有力”。④⑤⑨⑩[古希臘]柏拉圖:《蘇格拉底的申辯》,嚴群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52、52、52、55、56、68頁。第二批是安匿托士等人,那么,第一批究竟是誰呢?他們神秘莫測:“他們單方掛了案,作為原告,從不到案,因為沒有被告的另一造出來答辯。最荒唐的是,他們的姓名不可得而知而指,只知其中有一個喜劇家”。④這里深刻地描述了公共狀態的奇特狀況,我們日常生活中往往會聽到一些什么,“大家”都那么說,于是人們紛紛效仿,股票、綠豆、搶鹽等等,但當你問究竟誰在說時,只能聽到這樣的回答,“人們”都那樣說。用蘇格拉底的話:“既不可能傳他們到此地來對質,我又不得不申辯,只是對影申辯,向無人處問話”。⑤但這種“影子”和“無人”絲毫不削減其強大的力量。這里太容易讓我們想起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所描述的常人:“常人怎樣享樂,我們就怎樣享樂;常人對文學藝術怎樣閱讀怎樣判斷,我們就怎樣閱讀怎樣判斷;竟至常人怎樣從‘大眾’抽身,我們也就怎樣抽身;常人對什么東西憤怒,我們就對什么東西‘憤怒’。”⑦[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三聯書店,1999年,第147、149頁。在這種共同生活中,我們有共同的價值取向,比如說蘇格拉底慢神、腐化青年,但這個常人不是任何確定的人,“每個人都是他人,而沒有一個人是他人本身。這個常人,就是日常此在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這個常人卻是無此人,而一切此在在共在中又總已經聽任這個無此人擺布了”。⑦但“人們”是誰,我們卻從不過問。
四、借知識驗證神的讖語以自知自己無知
蘇格拉底切真地“感受”到了神人感應關系,義無反顧地進入到虔敬之處境中,無視公眾意見的強大力量,“萬福的克力同,我們何必如此關注大眾的意見?”⑧于是,就給自己惹了禍。他堅信神是全知,可是神說“蘇格拉底最智”,而“我自信毫無智慧,他說我最有智慧,究竟何?按其本性,神決不會說謊”。⑨為了證明神的讖語,“此后,我——去訪,明知會結怨,滿腔苦惱、恐懼,可是必須把神的差事放在首要地位”。⑩蘇格拉底申辯的主旨,就是“論證”或表白他的所作所為乃服從神的指示,他確實是敬神的,而非被誣告的慢神。但虔敬“感”又非知識所及,只有以實際的行為來表現自己的虔敬,因此,申辯并不是蘇格拉底對于自己的行為事后加以前因后果的邏輯分析,不恰當地說,是對自己實際行為本身的“現象學描述”。可是,事情恰恰又被拋了回來,遵守神的旨意而驗證“無人智過于蘇格拉底”,卻只能在實際生活中進行,在各階層人士中,借討論“正義”、“勇敢”、“節制”等概念或知識進行,于是近代做哲學史的人就說,蘇格拉底追求定義或知識。盡管如此,必須指出:知識之討論,后于虔敬之行為,或者說,只是服務于后者的手段,行為或決斷“本身”無可爭辯或討論。《申辯》中明確宣布:“我要向你們提供強有力的證據,不是空話,是你們所尊重的實際行為”。對于虔敬的蘇格拉底而言,相對于實際行為,知識甚至只是些“空話”。
蘇格拉底的所有對話最終都沒有結果。但這種無結果往往被知識化地理解,從哲“學”之超越性角度解讀,理想超越現實,理念超越意見,在追求的過程中顯現,并在此過程中無窮接近,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這種說法盡管思辨,但仍然持理念優先的思路,最終仍不過樂觀地認為,雖然我們沒有得出最終的結論,但我們對所要探究的“勇敢”、“正義”、“美德”等知道的更多了,更接近了,知識更豐富了。我們完全不否認這方面的解讀及其意義,西方傳統的哲學史就是這樣解讀過來的,但能否換一種思路,或許從中能領會更多的話外之音。其實,我們現代人不妨“頭腦簡單”一點,蘇格拉底的對話沒結果,這情況沒有那么復雜,只不過表明,作為人,本來就知之甚少。這一點,蘇格拉底自己說得再清楚不過了:“由于這樣的考察,雅典人啊,許多深仇勁敵指向我對我散布了許多污蔑宣傳,于是我冒了智者的不虞之譽。在場的人見我揭穿了他人的愚昧,便以為他人所不知我知之;其實,諸君啊,唯有神真有智慧。神的讖語說的是,人的智慧渺小,不算什么;并不是說蘇格拉底最有智慧,不過藉我的名字,以我為例,提醒世人,仿佛是說:‘世人啊,你們之中,惟有蘇格拉底這樣的人最有智慧,因他自知其智實在不算什么’”。②③④⑤[古希臘]柏拉圖:《蘇格拉底的申辯》,嚴群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57、70、66、68、71頁。很明顯,這里的蘇格拉底只是“人”的代表,不是蘇格拉底比常人意見知道更多,更接近知識,蘇格拉底的方法也并非所謂的“真理越辯越明”。這里只要求一種簡單而直接的自知之明,要求“人”或我們說“人類”“自知其智實在不算什么”,由此而進入一種虔敬狀態,以便接受另外的“真知灼見”,而“接受”本身就意味著被動,進入一種被動的處境中,警惕日常的、主動的、過分的知識性建構。這里,真正對我們現代人有意義的忠告就出現了,那就是:正視人的有限性。有限性反對人們“接近真理”的知識論想象,哪怕謙虛一點,說“無窮”接近也罷。可見,即便蘇格拉底追求定義或知識,也并非其最終目的,他不想知道或接近這些知識本身,對于他來說,更重要的或第一位的,是因真正“侍神”而驗證神的讖語,通過其畢生、直至獻出生命的行為,或者說,通過他被處死這件事本身,指出或彰顯出整體人類知識,或人類本身內在的無知或根本的有限性。只因此,對話對象“無論老少,愿聽我談論并執行使命,我不拒絕,我與人接談不收費、不取酬、不論貧富,一體效勞”。②
五、處境之必然性
處境中的決斷無法知識性地分析和拆解,就如同康德意義上的實踐理性,實踐非知識,理性直接決定意志,無需中間環節,無所謂因果,無以言表。但這并不妨礙決斷行為層面上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甚至強于邏輯必然性,在蘇格拉底那里,特定地表達為受神的引導:“你們要明白,這是神命我做的事,我認為,我為神辦此差是本邦向所未有的好事”。③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我們不能把這種引導理解為“因為”神引導,“所以”我如此這般行為,行為直接受引導,引導直接導致行為,無需思維介入,正因為如此,人們才譏笑蘇格拉底和游敘弗倫經常提“神”,“其緣因,你們聽我隨時隨地說過,有神降臨于我心,就是邁雷托士在訟詞上所諷刺的”。④因為這種不假知識的直接性,從知識角度看就是神秘的,甚至可以誣以“裝神弄鬼”。出于同樣的原因,后人褒獎蘇格拉底時,如果僅從知識角度,贊美他熱愛智慧,崇尚理性,這樣做,其實和從知識角度對他的諷刺、直至訴訟一樣,都沒有進入蘇格拉底本人接受神旨的處境之中,沒有領會蘇格拉底處境中的必然決斷。“我相信,此事是神之所命,神托夢啟示我,用讖語差遣我,以種種神人感應的方式委托我。雅典人啊,此事是真,否則易駁”。⑤蘇格拉底用了“相信”一詞,以遠離“論證”,并直接強調“此事是真”,“否則易駁”。反過來說,如果不“信”此事為“真”,而以知識眼光看,則“易駁”,即有口難言,無以申辯。在克力同最后探監時,蘇格拉底說他做了一個夢,“白衣麗人示現于我”,克力同說:“怪夢,蘇格拉底。”他堅決地說“不,對我顯現明白得很,克力同”。[古希臘]柏拉圖:《克力同》,嚴群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99頁。因為這種清晰明白,“我們絲毫不必考慮大眾怎么質問我們,只要注意那明辨是非邪正的一人和真理本身是怎么說的。……固然可以說,大眾能置人于死地”。②⑦[古希臘]柏拉圖:《克力同》,嚴群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04、102-103、98頁。這充分顯示了處境之必然性對抗邏輯必然性的強大力量。“親愛的朋友克力同,我仿佛真聽見這些話,象崇奉渠貝壘女神的人在狂熱中如聞笛聲;這些語音在我心中不斷回響,使我不問其他的話”。②“狂熱”中的崇拜者,其信仰的力量遠大于邏輯的力量,定會使其“不問其他的話”。
另一方面,從現實的處境來看,蘇格拉底也不得不死。控訴他的兩項罪名:慢神——引進新神和蠱惑青年——最大的智者,某種意義上講也沒有冤枉他。盡管他極力申辯其敬神,“雅典人啊,我信神非任何告我的人之所能及”,④⑤⑥⑧⑨⑩[古希臘]柏拉圖:《蘇格拉底的申辯》,嚴群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73、70、76、80、65、56、56、67頁。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像通常所說的那樣,蘇格拉底引進什么理性之神,或者基督教意義的上帝,因為上帝恰恰是絕對確定性的符號,但由于其所敬之神并不明確,并且以與人爭辯的獨特方式表現,不合傳統信仰形式。從知識角度而言,處境的神秘性,完全可以任意被解釋為引進了另外的信仰。蠱惑青年方面,蘇格拉底自己坦言:“如有人,無論老少,愿聽我談論并執行使命,我不拒絕,我與人接談不收費、不取酬、不論貧富,一體效勞;我發問,愿者答,聽我講。其中有人變好與否,不應要我負責,因為我不曾應許傳授甚么東西給任何人”。④我們可以看出,蘇格拉底確實將辯論術展示給所有人,而柏拉圖后來則極力主張青年人不易過早學習辯證法,因為辯證法和智者的詭辯在形式上一樣。“其中有人變好與否,不應要我負責”則表明,確實有他的追隨者淪為智者。此外,蘇格拉底對話無結論,本來是驗證人的智慧有限,但從知識角度看,卻和智者們的相對主義、動搖真理結果上一致;就連其證明自己不是智者、不收費而赤貧時的申辯:“可是我沒錢,除非你們肯按我的支付能力定罰款的數目。或者我付得起一個命那銀幣,我自認此數”。⑤也遭到怨恨,被認為蔑視法官,自尋死路。再加上他以實際行動曾得罪了民主派和寡頭們,也注定了他必死的命運。
六、處境之中對死的泰然任之
面對必死之命運,蘇格拉底自知、認命,并因此表現得無畏。“所以,我的遭遇絕非偶然,這對我明顯得很,此刻死去,擺脫俗累,是較好的事”。⑥克力同也贊美到:“我當時感覺你平生盡是樂觀,現在愈覺得,當你大禍臨頭,還是如此寧靜,泰然處之”。⑦但如果這種不畏死被解釋為大義凜然,舍生取義的話,就過于片面了。前已表明,蘇格拉底與人爭辯“正義”并非追求其知識或價值本身,或許后來的柏拉圖更偏重于此。舍生取義者往往是以義為先,生為后,“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這里明顯做了一種價值上的比較,先知而后行,“思考”之后決定以舍生為“代價”而取義,與茍且偷生相比,取義被“公認”為理性的、高尚的決定。但蘇格拉底面對死亡這種最不欲的,令人害怕、畏懼的事情的獨特態度,不能片面理解為知識、價值層面的高尚選擇。他在多處強調,畏死之關鍵是由于把死當做了知識,而不是切身的事件:“諸位,怕死非他,只是不智自命為智,因其以所不知為知”。⑧對死的知識性無端猜測,使每個人都怕死,即使猜測死后升天,也由于“前途”之不確定而使人恐懼。從知識層面上講,蘇格拉底并非不怕死,雖說“可是必須把神的差事放在首要地位”,⑨但畢竟“此后,我——去訪,明知會結怨,滿腔苦惱、恐懼”。⑩在《游敘弗倫》中,蘇格拉底也表現得和常人一樣忐忑:“如果他們認真起來,除非你未卜先知,此案伊于胡底莫能測也”。[古希臘]柏拉圖:《游敘弗倫》,嚴群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4頁。作為正常公民,蘇格拉底也幾乎竭盡全力地進行了申辯,盡管結果不盡人意,因不合知識而適得其反,甚至落得“胡言亂語”意在“舍生取義”以“沽名釣譽”之嫌。“雅典人啊,我此刻的申辯遠不是為我自己,如有人之所想,乃是為你們,使你們不至于因處死我而辜負了神所贈的禮物”。類似這樣的“邏輯矛盾”申辯中比比皆是。
海德格爾把死稱為“此在最本己的、無所關聯的、確知的、而作為其本身則不確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三聯書店,1999年,第147頁。這里所說的不確定,也是指知識層面上死亡事件的不確定性,而“確知”,則只有實際向死的處境中才會昭然若揭。蘇格拉底的坦然無畏,就是對于不由知識,而由處境所必然決定的赴死行為而言。但與海德格爾的無神論不同,他的這種無畏還是以敬神的話語表達的。“從幼年起,就有一種聲音降臨,每臨必阻止我想做的事,總是退我,從不進我”。②③④[古希臘]柏拉圖:《蘇格拉底的申辯》,嚴群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68、78、78、78頁。在本來就簡短的《申辯》篇另外一處又說:“我遇一件靈異的事。經常降臨的神的音旨以往每次警告我,甚至極小的事如不應做,都要阻止我做”。②可見,神的意旨更多是消極的阻止和否定,即對一般公眾意見說“不”。“你們眼見,當前發生于我的事,可以認為,任何人都認為最兇的”,死被公認為最壞的事,“可是這次,我清晨離家,到法庭來,發言將要有所訴說,神的朕兆全不反對。可是,在其他場合我說話時,往往中途截斷我的話。在當前場合,我的語言、行為,概不干涉;我想這是什么原因呢?告訴你們,神暗示所發生的事于我是好事,以死為苦境的人想錯了。神已給我強有力的證據,我將要去的若不是好境界,經常暗示于我的朕兆必會阻我”。③這里,“以死為苦境”是以不知為知造成的,而神給予的“證據”并不是邏輯的根據,不保證蘇格拉底去“好境界”。 蘇格拉底清楚,死:“或是全空,死者毫無知覺;或是如世俗所云,靈魂由此界遷居彼界”。④他肯定不贊成“世俗所云”,那么對于知識而言,死就是全空,是絕對的無,最高的阻止和否定。但這種“無”在行為層面上對每個人都是最真實的,神的暗示通常是阻止,對知識說“不”, 死不從知識角度看,則無所謂苦樂,在蘇格拉底的當下處境中,神的旨意無比真實地對他啟示:不阻,正是這種真實,海德格爾所言的“確知”,使得他面對死亡“如此寧靜,泰然處之”。蘇格拉底不是為了正義,故意激怒審判官和陪審團,不是“思慮”長遠,為哲“學”之興盛、為造就柏拉圖而獻身,泰然任之是行為層面對命運和人之有限性的認可。
總結
蘇格拉底的舍生取義不是為了理想或理念,而首先是出于對神的虔敬,因為侍神而決斷。而決斷必然造就孤獨和赤貧,因為孤獨的處境背離公共知識,顯得古怪而反常,于是申辯本身在知識面前顯得蒼白無力。他為了驗證神的讖語,說明人的知識之有限而借助“知識”進行辯論,在后人的知識解釋視野中顯得是在追求知識或真理,尤其是沿著對柏拉圖主流解釋的方向,順理成章是柏拉圖的先驅,于是追求普遍性、確定性的殊榮就被加在他頭上,以至于被公認為西方的“道德”典范。但通過進入他的切身處境,我們也可以清晰地體會出另外的東西,追求知識只是作為現實可行的手段,服務于他侍神的事業,敬神本身就意味著對人的有限性,或者說人的知識建構之有限性的徹查,要求人自知自己無知,蘇格拉底以切身行為踐行其對神的虔敬,力求“見喜于神”,行為先于知識。這種行為之決斷無法真正進行辯解,并且由于履行侍神的義務同時造成了現實的后果,因此蘇格拉底之死就成為必然,而他也通過死,完成了他虔敬的一生,直到最后,也是他最后的一句話,他還是堅信:“那么,克力同,就這樣罷,就這樣辦吧,這是神所指引的路”。[古希臘]柏拉圖:《克力同》,嚴群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03頁。處境所決定了行為之必然性,其強烈程度遠大于邏輯所論證的知識之必然性,在蘇格拉底的特定處境中,神的指引使他視死如歸、安泰恬然。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哲學系
責任編輯:張 蓬
* 本文受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項目資助(項目號:NCET-10-0559)。
① 論柏拉圖的《游敘弗倫篇》,施特勞斯,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433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