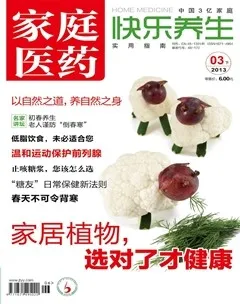湘西邊城的純美生活
湘西,因為沈從文的小說和謝晉的電影而聞名全國。今天,活在電影、小說和畫中的湘西已不復新鮮,在游玩湘西時用自己的視角和大師們作對比,體驗不一樣的湘西逐漸成為一種時尚。
一條馬路兩條街,喇叭一聲響全城
抵達古丈的時間是深夜,我們只能通過高低起伏的路面,感知已到大山腹地,到達賓館后來不及查看地形,倒頭便睡。
熟睡中突然被音樂聲驚醒,初以為是隔壁的旅客忘記關電視,可聲音又不是從房間傳出的。從窗口探出頭搜索,發現所住的旅館原來是改裝過的吊腳樓。樓建在半山中,腳踩在小河里,而從山頭電線桿上的高音喇叭里傳出的民族風音樂踩著水波呼嘯而來,如同雄雞打鳴,提醒遠道而來的旅客,別忘了早起領略晨霧中湘西古城的生活氣息。
這個場景,勾起了我兒時的記憶:一個普通的小山村,正中央豎起的電線桿上也綁著幾只大喇叭。老爸關心喇叭中播放的國家大事、時事新聞;我關注的是評書、相聲、歌曲。
家鄉的喇叭早在30多年前就停止了廣播,沒想到在古丈縣城,廣播還能堅持到現在。
一條馬路兩條街,喇叭一聲響全城,這是小城古丈的真實寫照。在喇叭悠揚的音樂聲中,小城蘇醒過來。街市開始了忙碌和鬧熱,買早點的、晨練的、上班的,在街上穿梭往來。也有不少人,頭戴斗笠,背著背簍往小城四周云蒸霧罩的山里鉆,就如同武俠小說中的采藥人。
我也背起背包開始了一天的旅行。古丈是一座連紅綠燈都沒有的小城,牛羊可以在大街上漫步。我們也操著和牛羊一樣悠閑的步伐在街上閑逛,末了跟著戴青箬笠、穿綠蓑衣的采茶女步入山林,去尋找傳說中的古丈毛尖。
山路蜿蜒,每一個路口都立著一個巨大的招牌,這是宋祖英演唱《古丈茶歌》時的劇照。宋祖英出生在古丈,是古丈人的驕傲,于是,她就成了古丈的形象代言人。
從縣城出發,步行10分鐘后,回首一看,小城已經在薄霧中隱去,眼前山野蔥蘢,但空山不見人,卻聞伊人聲:綠水青山映彩霞,彩云深處是我家;家家戶戶小背簍,背上藍天來采茶……
芙蓉鎮:
掛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鎮
一條奔騰的酉水河,分開了古丈城和芙蓉鎮。河東河西,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傳承。
全國知名的芙蓉鎮,一條5千米長街就是全部。在濕漉漉的石板街上,我們每個人吃了一碗“劉曉慶米豆腐”。沒有想象中那樣柔軟,入口濕而硬的感覺和眼前這石板街異曲同工。也許,離劉曉慶做米豆腐的時間太久,米豆腐和做米豆腐的人都不再如豆腐西施那般柔軟水靈。
米豆腐店和芙蓉鎮姜糖的招牌占據了古鎮最重要的門面。我卻再也沒有食欲,直到看到一幅“古丈毛尖”的幌子。
茶館是一位名為瞿大掌柜的土家族人所開。茶館里除了茶葉之外,擺得最多的是瞿大掌柜的劇照——瞿大掌柜愛好演戲,每當有劇組到芙蓉鎮拍戲時,瞿大掌柜總要去戲里跑跑龍套。
十里長的芙蓉鎮老街,瞿大掌柜就開了3家茶館。生意好時,他就在3家茶館之間來回奔波;生意清淡時,他就搬把竹椅,沏一壺古丈毛尖,翹著二郎腿躺著飲茶。
芙蓉鎮有“掛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鎮”之稱。芙蓉鎮的石板路蜿蜒在懸崖之頂,瞿大掌柜的茶館則一邊近石板街,一邊臨懸崖。就在瞿大掌柜的茶館家前方不遠處,一條本和石板街平行的河流突然轉了個彎,一個跟斗翻下懸崖,成為一條巨大的瀑布。而瞿大掌的茶館則是最佳觀瀑點。
瀑布就如同分隔牛郎織女的銀河,把芙蓉鎮一分為二。瀑布之上,是連綿十里的石板街,街兩岸是青磚黑瓦的房屋,街道上熙來攘往的是旅客與商賈,這場景就是電影《芙蓉鎮》的翻版;瀑布之下,是一排錯落有致的木屋,飛檐斗拱,就山勢河形而建,“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斗角”,很得阿房宮之古風。一瀑之隔,差距為何這樣明顯?
瞿大掌柜長嘆一聲:“一邊是平民百姓的市井生活,一邊是獨霸一方的土司行宮,差距能不明顯么?”
聽了瞿大掌柜的話,我恍然大悟。剛才在石板街上閑逛時,路經民俗風光館時,參觀了一名為“溪州銅柱”的文物。銅柱記載的是五代十國時期,湘西少數民族代表、土家族始祖彭士愁,與漢族勢力代表、湘西南楚王馬希范相議和解,立銅柱記事的故事。一根銅柱,給湘西帶來800年和平,也開創了湘西彭氏土司800年基業。瀑布下面的亭臺樓閣,就是昔日的土司王宮。
猛洞河:
漸行漸遠的土家漁歌
長街盡頭,是一個高大的城門,城門外便是奔騰的猛洞河。城門外到河岸有幾十級高大的臺階。每一級臺階上都站滿了等著溯源猛洞河的游人。游船一靠岸,游客一哄而上,游船走遠,整個碼頭就清靜了下來。如今的芙蓉鎮碼頭,只為游客而存在。
芙蓉鎮最興盛時,是在土司時代,那時芙蓉鎮還叫做王村。王村是土司行宮所在地,也是整個湘西最繁華的地方。王村因水而盛,成為了猛洞河上的交通樞紐。
年邁的土家族歌王黃太坤依稀還記得當年王村碼頭的繁盛:那時沒有公路,整個王村的交通全部依賴碼頭外的猛洞河。每到過年之時,王村外的碼頭上就會停泊著大大小小船只,土司家奴們排著隊往土司行宮中搬運年貨。貨物白天搬不完,就在長街上每家門口點上一盞馬燈,家奴一邊勞動一邊唱歌,石板街就成為了一條會唱歌的火龍。
隨著土司王朝的消逝,碼頭也失去了往日的繁榮,會唱歌的土家族人也變得越來越少。昔日號子悠揚、漁歌回響的猛洞河開始變得悄無聲息,唯一會唱土家漁歌的歌王黃太坤幾乎成了土家文化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