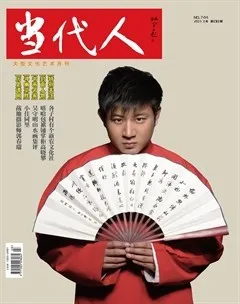京劇的道白
道白,又稱念白。歷來京劇行有“三分唱,七分念”之說,可見念白在表現力上的重要性。雖然對于一般觀眾來說,可能對道白不如對唱腔那么重視,但無論如何也不可小視此點。
京劇的“白”,又有人解釋為“說”。籠統地講,沾邊,但還不足以說明問題。“白”有京白和韻白之分。京白如丑角、花旦等一般使用,謂其“說話”也是屬于“藝術的說話”,跟平時人們的說話比仍有一定講究;至于韻白,一般為老生、青衣等使用,不僅具樂感,在用韻上亦按傳統規范。
曾見有人說道白類似鼓詞小說中的敘述。而唱詞是其中的韻文部分。我以為這種類比是不妥的。京劇中的道白絕不是僅僅用來敘述,也不僅是一種過渡或“過門”。它在很多情況下實際上是起到了唱詞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言其具有畫龍點睛之妙也不為過。
一提到京劇之念白,比較熟悉的朋友很自然會想起京劇的丑角。不錯,丑角是以念白取勝的。信舉幾例:《法門寺》中的太監賈桂有一段讀狀子的“貫口”,可謂長篇訴狀一氣呵成,是一種真功夫。還有京劇老丑,如《女起解》中的崇公道,《烏盆記》(又名《奇冤報》)中的張別古,都不乏精彩的道白。如解差崇公道出場時的念白“你說你公道,我說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等等。張別古與含冤鬼魂(烏盆)的對話,也都是很有意趣的。但道白絕不是丑角的專屬,在“正工老生”和“正旦”口中也有不少“四兩撥千斤”的念白。我記得當年看馬連良先生的《四進士》,當那贓官說了句:“宋士杰,你好一張利口!”“宋士杰”馬上回了句:“老爺,你好厲害的板子呀!”與說這話的同時,演員那不屈的身段配合著不屑的聲腔,極富表現力地塑造出人物的鮮明性格。還有我年輕時在濟南看周信芳和老旦劉斌昆演的《清風亭》,風燭殘年的老夫婦在孤貧交加中等待他們的養子張繼保回來。他們相互扶持,相互撫慰,相互呼喚。彼此只念兩個字,卻情重千鈞,內涵豐厚。反復地念,觀眾即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悲憫、同情、壓抑、郁悲交織,臺上臺下融為一體,氣氛極為肅重。凈行的道白有的也很傳神,如《法門寺》中的大宦官劉瑾,念白中滲透著角色的跋扈、專斷卻又富于生趣,他叫賈桂時那一口一個“猴崽子”,充分道出主奴(或大奴小奴)間的微妙關系。而賈桂則更有意思,當主子叫他坐下來說話,他答曰:“我站慣了。”一句話幾個字,便將其奴才本性活脫脫地勾畫了出來。所以說,有些道白能起到畫龍點睛之功效是很切實的。
京劇道白中有些文學性是很強的,不啻于小說中精彩的對話。如《女起解》中崇公道與蘇三在“途中”的邊唱邊說,蘇三訴說她的“九十恨來十一恨”,崇公道為她排解的一些話語:“衙門口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衙門的大堂上一不種谷子,二不種高粱……”說皮氏賄賂縣衙,“連我老漢還分了一雙鞋錢。”當蘇三沖撞了他,使他不悅,而蘇三又好言相慰,最后他說:“你看這小嘴有多甜,氣也把我氣死,可樂又把我樂活啦。”生動、詼諧,極具生活化與戲劇性。
前輩的名丑如蕭長華、馬富祿等堪稱語言大師,對京劇語言的豐富與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應該說,他們在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影響是可以擴及京劇圈以外,乃至相聲、現代戲劇也從中吸取了有用的養分。
迤至今天,也沒有減低京劇念白的重要意義。然而恕我直言,今日的許多演員更不必說票友們,對于唱功的重視程度、下的力氣肯定要勝過念白許多。原因也許是唱功在觀眾方面更容易獲得青睞。對此,也許我孤陋寡聞,至今在舞臺上還沒有聽到當年馬連良、周信芳先生或瀟灑飄逸或厚重味濃的念白。
作為觀眾一方,也應該領會并習慣欣賞演員的精彩道白,它與唱腔同是美的享受,而且是一種別有韻味的享受。對于出色演員的出色念白,也應學會與對精彩唱腔一樣給演員以鼓勵。我記得少時看戲,一些會聽戲的觀眾,不但為演員的動聽唱腔鼓掌,同樣也為他們有滋有味的道白鼓掌。現在看來,這是一種風格,也是一種欣賞層次。
(責編:郭文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