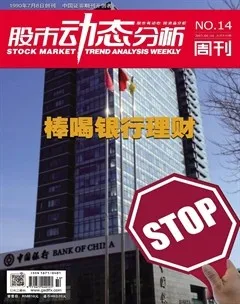新常態下的投資思路
現在和十年前比有什么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國經濟的競爭力正在迅速削弱。過去十年我們取得了越來越大的國際經濟貿易的市場份額,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低成本,而這個成本優勢在今后5到10年內很可能會被大幅度削弱甚至喪失。
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有五個:一個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一個是環保成本的上升,一個土地成本的上升,一個是資源和能源成本的上升,再加上人民幣匯率升值。這些因素在過去5年、10年中不斷地累積,在過去兩三年中進一步加速。為什么近年來的宏觀調控越來越頻繁、越來越短期化?原因之一就是在成本升高后,幾個調控目標之間越來越難以兼顧,一放松通脹就抬頭,一收緊經濟就不行,政策騰挪空間越來越小。
今后5到10年,我們的內在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比過去十年大幅度降低了。另一個就是通脹,由于成本上升,在今后十年中通脹也會比現在高,也許是4%、5%甚至更高,“滯脹傾向”這個趨勢是不可逆轉的。就是今后5-1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放慢到7%以下、通貨膨脹上升到4%以上的這樣一種傾向。這種成本升高之后的“滯脹傾向”也可稱之為中國經濟的“新常態”。這個新常態就是成本更高,通脹壓力更大,經濟的內升潛力更低。
還有消費,沒有投資增長和出口增長帶來的收入增長,消費是沒有辦法自己加速增長的,特別在我們現在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還沒有進一步完善、中產階級還沒有形成之前,希望消費能貢獻3-4%以上的GDP增長是不現實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留下的抓手就是投資。投資中40%是工業投資,但是工業投資在今后5-10年里再指望它快速增長也不太現實。為什么這么說呢?過去20年的工業投資和產能擴張的大背景是中國從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經濟體轉變為世界工廠的開放式經濟體。如今,成本大幅上升之后,包括耐克和Coach這樣的品牌商都在把工廠搬離中國,外商投資的迅速增長很難指望了。同時,由于環保因素,今后幾年落后產能淘汰的力度必將大幅加大,再加上各種成本的上升和出口增速的下降,國內的工業產能擴張速度也會大幅放緩。
剔除出口、消費和工業投資,只剩下基建投資和房地產投資了,三駕馬車現在只剩下一架的三分之二還可以跑,其他的好像看不到。現在中國經濟的出路往哪里走?有人說,不是還有經濟轉型和新興產業嗎?經濟轉型是一代人的事,遠水解不了近渴,指望新興產業和經濟轉型能在5-10年內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是“大躍進”式的一廂情愿。所以,在2020年前,要想經濟增長“保7”,基建和房地產投資是僅存的動力。而且,從人口紅利和儲蓄率的角度看,今后7、8年是中國提升基礎設施的最后機會了,之后,很難找到足夠的基建工人和足夠的低成本資金了。
換一個角度,從供給層面來分析,經濟發展的三大推動力一個是人口的增長,第二是人均資本(包括土地)的提升,第三是人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創新和改革長遠看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是改革的初期不見得能立竿見影。例如,水電油氣要素價格的改革,長期看有助于理順機制、節約資源和增加供給,但是改革的初期卻更多體現為要素價格的提升,提高經濟運行的成本。
我們現在人均GDP是6200美元,在成本上升的情況下要克服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城鎮化。現在關于城鎮化的爭論很多。從經濟發展的三大推力上看,城鎮化首先能夠延續城市的人口紅利,農村總的人口可能沒增長,總的勞動力人口也許不增長了,但是城鎮化可以進一步推進城市的人口增長了。其次,通過農村土地的流轉實現土地資本的貨幣化,人均資本就能夠增加,剩下的農業土地集約化使用,留在農業的勞動力的人均土地增加。第三,勞動生產率。過去這幾年民工工資增速較快,也正體現了他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城鎮化與新興產業相比,我們的地方政府更知道怎么做城鎮化,相比之下,新興產業大干快上反而造成了更多的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
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關鍵就看能不能在今后5-10年執行好城鎮化的戰略,實現投資與消費的良性互動,促進城鎮人口增長、人均資本增加和人均勞動生產率提高,供給層面的這三個改善才是真正應對成本上升的最佳路徑,而不是依靠收緊貨幣政策、地產調控。
在這種大背景下,今后5-10年的投資思路是什么?
首先,從資產配置的角度來講,股票比債券好。你現在拿著債券可能有5-6%的收益,覺得不錯,但是扣除今后5-10年的通貨膨脹率后就所剩無幾了,也不排實際收益為負的可能。今后10年的“新常態”下,名義GDP增長仍然有10%以上,對有定價權的股票而言,實現利潤的兩位數增長并不難,這些股票在12倍以下的估值買入比債券更有吸引力。同時,由于工業投資下來了,實體經濟對資金的需求下降,剩余流動性反而有可能更好,股市反應的主要是剩余流動性。
第二,從商業模式上看,高利潤的模式優于高周轉模式,有定價權的公司會好于有成本優勢的公司。A股大多數公司的資源優勢和技術優勢是靠不住的,因為他們并沒有真正的資源或真正的技術。接下來你要靠什么?在這種低增長、高通脹的新常態下,靠成本優勢的企業比較難以維系,靠高周轉的企業會發現周轉成本越來越高,靠規模優勢的企業有從規模經濟變成規模不經濟的風險,除非規模大到接近寡頭壟斷的地位。相比之下,寡頭壟斷和品牌優勢在新常態下是最能持續的。關鍵還是看定價權。
第三,從投資風格上看,價值股好于成長股。其實,低增長、高通脹的新常態對成長型企業是不利的。原因很簡單,繁榮的經濟、充裕的流動性更有利于企業拓展新業務、新產品,相反,經濟低迷、通脹升高的背景下,企業舉步維艱,哪有余力去創新?現在大家追捧的所謂“成長股”,十有八九是炒主題、炒概念的“偽成長股”,在逆境中生存的能力特別弱,這一點只要看一下過去兩年中小企業的利潤下降的比例就清楚了。
但是,市場仍然熱衷于“成長股”而拋棄銀行、地產、白酒等低估值藍籌股,認為它們是夕陽產業。其實,中國有14億人,任何一個大行業,你只要把握住行業的龍頭地位,再發展20年、30年是沒有問題的。更何況,地產是個很有定價權的行業。前幾天有人在爭論說政府是否曾經把地產當成中國的支柱行業,這個爭論就好比爭論米飯是否是中國人的主食一樣沒有必要。事實證明,過去兩三年那么嚴厲的政策變化都沒有改變銀行、地產行業的利潤持續快速增長。目前市場對政策變化很可能過度反應了。
簡單說,低估值的、有定價權的藍籌股,這就是我們新常態下的投資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