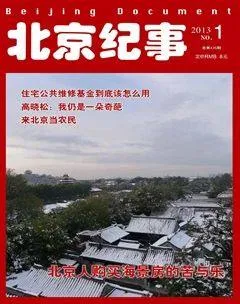為“更好的教育”號號脈
習近平總書記在新一屆政治局常委見面會上表示,“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著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話里的10個“更”,從語法修辭上,夠語文老師給我們講一氣了。總之,這一席話語讓人感到暖洋洋的,就像那天有些寒冷的夜晚,踏入簋街,走進東直門附近的“聚點串吧”。平民氣息和時尚氛圍融合成最真實親切的感覺,令人欣喜,憋不住用點酸詞——柳暗花明又一村。
“聚點串吧”的老板是我朋友的朋友,據說他們這圈子是清華大學餐飲總裁班的路數,通過一次學習建立了友誼。所謂世事難料,烤串在我眼里是吃喝中問題最多的。2012年夏天,我路過豐臺成壽寺,街邊的燒烤已經有燎原之勢,肯定為北京PM2.5的升高貢獻不少。亦莊北京經濟開發區街道安靜規矩,時不時被人稱為“西方小鎮”。可路口經常把生意做到后半夜的燒烤“游擊隊”,還有那些開著寶馬奔馳過來、騎著小馬扎的吃客,以及清早路人眼里的遍地狼藉,又讓人不得不信這里“最中國”。
聚點老板說,自己就是把街邊的玩意搬到屋里來。說歸說,開了6家連鎖店,有一家甚至還開到了河北廊坊,絕對得有實干精神。屋里最大的好處是食物安全,大冬天讓那些喜歡燒烤的人有個念想,讓我這個不沾邊的人偶爾為之也有了些感想。終于知道那些老少爺們兒大姑娘小媳婦,或站或蹲圍著的麻辣燙湯鍋里,確實有特殊的味道。
簋街讓我聯想到美國西雅圖的派克市場——國內游客的必經之地。它的前身就是個農村集貿市場,始建于1907年。這里有上百個農業產品攤位,一年有幾百場商業和手工藝展示,隨處可見各色鮮花、新鮮糕點,當地的干酪、蜂蜜、葡萄酒,還有各國口味的餐館、進口商品店、古董收藏品店等。這里最著名的是魚市,我好奇的不是魚的品質和價格,而是賣魚人真誠的工作態度和搞笑的銷售行為,把有些辛苦乏味的過程變成了快樂,并感染著經過這里的每一位游客。
說這些和教育有關系嗎?吃喝是人的基本需求,解決了溫飽,最讓有兒有女之人糾結的問題就是教育。老祖宗的事不必說,教育是中華民族得以繁衍發展的根基,近代特別是民國以后,真正留下的遺產可以說就是教育。100年前,魯迅先生進北京進教育部的事,正在阜成門附近的魯迅博物館展覽,其實就是民國最好教育史的回顧。
1917年12月25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和教授李石曾、李大釗、沈尹默、馬幼魚、馬叔平等,在北京東城方巾中巷“華法教育會”會址,創辦了一所新式學校——孔德學校。他們希望把法國的實證主義介紹到中國,因此以法國近代實證主義哲學家孔德的名字命名,辦學資金則是華法教育會利用庚子賠款的退款。學校有領先全國的教室、禮堂、科學館、操場、乒乓球館、圖書館等。解放后,學校圖書館的6.4萬冊圖書給了首都圖書館,大卡車拉古書整整拉了三天。早期,學校有不少北大子弟,比如蔡元培的女兒,胡適、錢玄同、李大釗、沈尹默、周作人的兒子。另外,還有大學的知名教授兼課,自編教材并開注音字母教學先河,提倡科學教育、藝術教育,特別注重實踐。1952年,孔德學校改名為北京市27中學,1978年合并北京市169中學(延安中學)。總共54個班,3000人,其中有我和二弟。當年,27中號稱是北京市人數最多的中學。
三弟上的是北京市166中學,前身是由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創辦的貝滿學校,創始人是傳教士艾莉莎。貝滿夫人,1864年在北京設立貝滿女子小學,1895年有了4年制的女子中學,校址在北京東城燈市口大街北面。早先,這里是明代權相嚴嵩之子嚴世蕃的府邸,清朝為順治皇帝的佟妃——康熙皇帝母親的家人的居所。學校最初的50多年,基本是外國傳教士在領導,教師也多是美國傳教士。《圣經》是必修課,學生每周要去教堂做禮拜,由公理會的牧師“講道”。
1929年,貝滿經北洋政府批準立案定名為北平私立貝滿女子中學。1949年北平解放,1951年,改名五一女中。1952年,改名北京市女12中。上世紀70年代,改名北京市166中學。在學校,三弟遇到了一個非常優秀的音樂老師——李增嚴。他是中央音樂學院的高材生,也是李雙江的同學。三弟跟他學了美聲唱法,李老師還給三弟畫了一幅小小的油畫。老師已經去世多年,畫還在我家老屋的書柜上。藝術熏陶對現在的三弟好像沒什么意義,他在生意場上漸行漸遠。可回顧學生時代,在考學之外,總還留下些不功利的色彩。
值得一說的是,166中如今的辦學理想——秉承育人本真,構筑教育生態,為師生的一生幸福服務。學校提出培養學生文化特質的一個核心,即學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以成就學生健康、自主、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為本;六個素養,即道德素養、科學素養、文學素養、藝術素養、信息素養和健康素養。
目前,166中成立了中小學特色教育聯盟(如與史家小學、府學小學、匯文小學、北京一師附小等學校的戲劇、管樂、體育和科技教育聯盟)、與高校的教育聯盟(如與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北京師范大學、中央戲劇學院、美國威爾斯利學院、美國曼荷蓮學院等的科學、藝術、文學教育聯盟)、與科研院所的聯盟(如與美國冷泉港實驗室、中國遺傳學會、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國家交響樂團、國家大劇院等的科學、藝術、歌劇、體育、文學教育聯盟)。不是替166中在吹牛,只想知道這是不是最好的教育。
筆者手里有兩本反映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的舊書。
一本是1975年7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七·二一”道路放光芒》,說的都是上世紀70年代初,工廠辦大學的事。理論依據是毛主席的話:“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現實依據是上海機床廠兩個年齡相仿而經歷不同的技術員案例:一個是上海某大學的畢業生,畢業后又專門學了一年外語,再去外國留學4年,得了一個“副博士”的學位。1962年,到磨床研究所實驗室擔任技術員。像這樣一個在學校里讀了20多年書的人,過去由于理論脫離實際,又沒有很好地同工人結合,所以長時間在科學研究方面沒有作出突出的成就。一個是工人,他14歲當學徒,18歲被保送到上海機器制造學校學習4年。1957年,擔任磨床研究所技術員。1972年4月,由他擔任主任設計師,試制成功了一臺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為我國工業技術的發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填補了我國精密磨床方面的一個空白點。看這段歷史,除了“左”的東西,也要看到時代變化,至少承認教育的重要性,思考如何學習。學習的最終目的是要用,這些問題到今天其實還是沒解決好。
另一本是《改革——教育的出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發行,北京市政府文教辦公室、北京市教育局編的北京市中小學內部管理體制改革經驗匯編。當時的副市長陸宇澄在序言中說:“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發展教育的極端重要性正日益廣泛為社會各方面所認識。然而,不少朋友比較注意教育經費和教師待遇。以為只要把這兩方面抓上去,教育自然而然地就會上去。在我看來,兩者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與改革結合起來,教育發展中長期困擾我們的種種困難和問題依然得不到解決。改革的實踐告訴我們,要把教育搞上去,必須采取“雙管齊下”的方針,也就是:一方面要靠各級政府增加教育投入,發動社會各方面關心、支持教育,為教育的發展不斷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必須針對現存教育體制和機制進行有計劃有步驟的全面變革,以逐步建立適應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新體制和新機制,只有把內因和外因結合起來,教育的戰略地位才能得到落實。
20多年過去了,現在北京無論是小學、中學還是大學,除了打工子弟民辦學校,政府的投入不斷增加,校長的權力越來越大,老師的工資大幅度提高。可我們的教育為什么仍然問題多多?為了有更好的教育,我們不能忘記魯迅先生,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魯迅研究專家孫郁說,“今天,我們紀念魯迅先生仍然有著重要意義。現在,很多中國人瞞騙、說假話,魯迅是最真實的一個中國人。另外,我們現在的文化語境里,漢語表達越來越粗糙、無趣,而魯迅是充滿智慧并且有趣的。魯迅身上還有那些大愛的東西、批判的精神,這些都是當下缺失的。”
編輯/麻 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