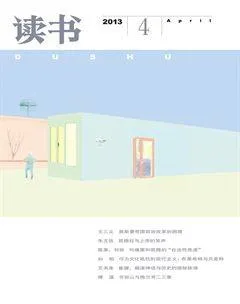“創新”的悖論
在當代中國,“創新”無疑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之一,它已被提高到了事關民族復興的高度。創新常與“源泉”、“動力”、“靈魂”等打動人心的詞語聯系起來,充斥了各種媒體。推進創新這一重大的責任,除了政府之外,再也無其他組織能夠承擔。于是,政府自然在推動創新上居于核心位置。近年來,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研究,國家的投入都有了巨大的增長,而這些投入往往是以“創新工程”、“創新計劃”為名的,人們不禁感慨,與“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八十年代相比,科學研究的物質條件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可是,與此形成對照,是我國的創新能力依然偏低的事實,很難否認,創新力并沒有和GDP那樣取得令人驚嘆的增長。而且,越是涉及“核心競爭力”的尖端領域,成果也就越少。這無疑將影響國家發展的后勁。
人們往往把這種情況歸咎于我們對創新重視得還不夠。似乎還要再加大對創新的投入,政府也一再強調這一點。可是,政府投入的加大,也就意味著對創新研究干預力度的加大,而過分的干預對創新的影響卻是消極的。以至于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狀況:對創新的大力鼓吹和干預,恰恰是導致創新能力偏低的重要因素。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越提倡創新,越扼殺創新。
為何如此呢?根源在于,創新活動作為人類向未知領域的探索,有著獨特的性質,它需要的是個人的自由意志和選擇權,而非政府的集中控制。對此做出最透徹分析的,當屬自由主義的大師哈耶克。在《自由憲章》一書中,哈耶克對人類知識增長和進步的論述,可以理解為對“創新”的詮釋。在哈耶克看來,人類社會的知識是如何增長起來的,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這種復雜性體現在:首先,創新往往并不具有明確的目標,而是人們不斷摸索和試錯的一種活動,在這種活動中,人的目標時常會發生變動。推動人們從事未知事物研究的,常常也不是明確和功利化的目標,而是對研究本身的興趣,所以,蘭米爾(Langmuir)說:“在研究工作中,你不能計劃發現,但你可以計劃工作,而工作卻或許會導致發現。”其次,人們不知道在這一過程中會用到什么已知的知識,以及需要何人的協作,政府很難為創新活動提供它所需要的幫助,常常是事倍功半。第三,在研究結果出來以后,能否以及如何被社會理解和接受,也是很難預測的事。這種復雜性是人類理性不可能準確預測和掌握的。因此,對于創新的集中計劃和指導,恰恰違背了創新活動的本質。創新的最有效方法,是把更多的自由留給個人,由“自生自發秩序”去決定誰的成果能推動社會進步。在這種秩序的作用下,所有的人類發明都需證明自身的價值,無效的被拋棄,有效的被保留,社會就這樣不斷地產生新的目標,知識也一步步增長起來。
哈耶克說過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正因為我們每個人知道的東西都很少,尤其是我們不清楚誰知道得最多,所以我們相信人們獨立的、競爭性的努力會使我們得到一經見到就想擁有的東西。”
國家操控創新活動的最大問題,就在于它規定的目標過于確定化。近年來,種種所謂“創新計劃”,都有極為具體的目標,并有對成果的明確要求和完成期限。在這種指揮棒的帶動下,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研究人員所從事的活動,也失去了創新活動所應有的復雜性和不可預測性,而是全力集中于發表論文這一極為明確的目標了。成果的發表本來只是研究工作的一個環節,但現在卻成了全部。在這種扭曲的機制下,低水平的“成果”自然遍地開花,而剽竊、抄襲之風也是愈演愈烈,更具有諷刺性的是,這些成果往往是被冠以“創新”美名的(現在各種科研項目的申報表上,必不可少的一欄就是“該項目有何創新之處”)。它的害處在于:由于掛了創新之名,就有了更大的欺騙性,其造成的損失也更不易被覺察。
創新活動還有一個特點:越是能對人類社會產生重大作用的創新,越要依賴于個人的天賦、努力和不可預知的偶然性,而不是集中的控制。并且,越是有價值的創新活動,也就越脆弱。因為,重大的發明往往在很多方面超出了人們對已知事物的理解,而集中的控制所依據的,恰恰只能是這種理解。正如哈耶克所說:“多數人的行動一般是限于嘗試過并確知的事情。”因此,對創新活動的統一指揮很可能摧毀極有價值的機會。遺憾的是,我們可能已經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卻渾然不覺——因為這種損失是隱形的。如果愛因斯坦沒有創立相對論,人們無疑也一樣照常生活,絲毫不知道他們本可以取得更大的進步。
中國歷來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傳統,這使我們辦成了不少崇尚個人自由的國家無法辦到的事。對那些目標明確的事情,我們幾乎無往不勝,我們在很貧窮的狀況下獲得了“兩彈一星”這樣的成就,我們難免為此自豪。但是,這也許掩蓋了另一面:這些成果的取得,可能是以喪失更有創新性的成果為代價的。科研人員只能根據國家的需要來從事研究,而國家集中控制下的研究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它只能著眼于那些目標明確的、已知的項目,說得更清楚一些,就是模仿和趕超,而離我們現在所提倡的“自主創新能力”還是有很大距離。在物質條件極為匱乏的建國之初,這樣做當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在現在的環境下,我們需要的是超越而不僅僅是模仿,這就需要一種更加靈活、更能發揮個人潛能的機制了。當然,崇尚個人自主并不是排斥合作,正如哈耶克所說:“擁護自由并不是反對組織,其實組織也是人類知識進步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應當反對具有特權的壟斷性組織。真正有效的組織,是建立在人類自愿結合基礎之上的。而國家由于具有強大的權力,在干預創新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對個人的強制,從而扼殺創新的機會。
“創新”的悖論還讓人想起了法國大革命——那是另一個悖論。它以自由之名扼殺自由,恰如以創新之名壓制創新。與革命的悖論相比,創新的悖論并不是血雨腥風的,但造成的損失也許更為嚴重,而且這種損失是隱蔽的,就更不能等閑視之了。
也許有人認為將二者相提并論并不合適。但是,二者卻有著相似的本質,它們都是強制性地使整個社會朝著一個向度,而這種向度都是以一個美好的詞語加以裝飾的,法國革命是“自由”,現在是“創新”。如果有人敢于抗拒這種向度,就會被邊緣化。當社會形成一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單向度時,它就同時拋棄了自由與創新兩種精神。因為,二者都是以人的獨立意志和思考為基石的。
這種單向度毀滅了人的獨立性,并使人分成了三種類型:一種是發號施令、主宰他人的人,大革命的領袖以“自由”為名操縱了生殺予奪的大權,而現在以“創新”為名的各種計劃、項目,也是以行政權力為基礎來施行的。掌握了權力的人事實上只是以“創新”為口號來爭奪資源、顯示政績,并不真正關心創新能力的進步(事實上也沒有這個能力,因為創新本不是能用政治權力加以控制的)。二是隨大流的人,法國革命中的群眾就扮演了這樣的角色,跟著掌握大權的人高呼革命與自由,而現在的“創新計劃”也有眾多這樣的應和者。他們有著雙重性質:一方面是推波助瀾,其中不少人是企圖以“積極”的表現來改變自己低微的身份;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在這一過程中真正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意志,是一種犧牲品。第三種是少數堅持獨立意志而又無力抗拒時勢的人,這樣的人在法國革命中擺脫不了上斷頭臺的命運;而在現在“創新”的浪潮中,也很可能被埋沒和扼殺。
當然,從某種意義來說,官僚制度和理性化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宿命,馬克斯·韋伯早就指出了這一點。比如,以論文數來評價研究人員的工作業績,就是國內外通行的方法,盡管它并不與創新精神相符,卻不得不然。因為,現代的科學研究已不可能是純粹個人的事業,而是涉及方方面面的協作與利益的分配,因此,就必須有一個易于操作的評價標準。但是,“創新悖論”的出現,卻不是科層制度的必然結果,而是科層制度大大膨脹并與中國傳統的官本位觀念結合的產物。科層制度有著明顯的消極性,它的權力本應受到嚴格的控制,但在創新的悖論下,它的權力卻大大擴大。這就使得“創新”事實上淪為一種權力的游戲:眾所周知,現在我國迅速增加的科研投入往往是根據申請者的“位子”而不是“實力”加以分配的。“創新”話語在這個過程中成為一種“語言藝術”:當申報項目時,“創新”是進行自我推銷的最佳詞語,而在對平庸的成果進行評估時,“創新”又成為文過飾非的絕好用語。
近來,有些學者把創新能力視為一種“軟實力”,這是很貼切的。因為這個“軟”字恰到好處地揭示了創新的關鍵:創新能力的進步,依靠的不是“硬”性的措施和命令,而是要有賴于有利創新的“軟”環境的建立。無疑,這是一個長期、艱巨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