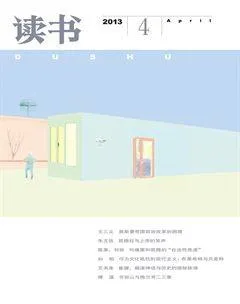奧斯曼帝國政治改革的困境
奧斯曼帝國歷史上大張旗鼓地改革始于一七九二年,即塞利姆三世當政的第四年。而局部的革新,比如引進西方的技術、購買西式武器、創辦技術學校,前任蘇丹阿卜杜·哈米德一世就嘗試過。至于學習歐式的建筑,模仿歐洲人的生活方式,在“郁金香時代”(一七零三——一七三零)就開始了。奧斯曼帝國改革的大體路徑與其他后發國家的改革并沒有差別,首先是軍事改革,接著技術引進,稍深入就是經濟改革,最后是政治改革,即仿建西方的政治制度。改革目標是富國強兵,改革內容是學習歐洲經驗,改造傳統社會。雖然富國強兵的愿望始終未能實現,但軍事改革和經濟改革多多少少都有成果,社會習俗和年輕人觀念的變化之快,更是不以統治者的意志為轉移。改革遇到問題的還是政治改革,因為政治改革遠比技術引進和經濟改革的難度大。
政治改革是改變制度,改變制度意味著權力再分配,一般情況下,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總是最激烈,所以政治改革總是阻力大,改革幅度小,難見成效,而且風險大,弄不好要出亂子。不過,奧斯曼帝國政治改革的具體情況卻有所不同。塞利姆三世(一七八九——一八零七)在改革軍隊方面做了努力,沒來得及進行其他改革就被廢黜。馬哈茂德二世(一八零八——一八三九)的軍事改革、經濟改革均取得成效,政治改革只邁出第一步,把帝國各級衙門改換成西歐模式的政府部門,設立咨詢和審議機構,并致力于革除官場陋習。可惜,由于希臘人鬧獨立,埃及總督挑戰蘇丹權威,俄國軍隊入侵,帝國的改革讓位于維護國內穩定、保衛國家主權。一八三九年馬哈茂德二世病逝,新蘇丹阿卜杜·麥吉德上臺,立即頒布改革法令——“古爾汗法令”,高調門向本國臣民和歐洲使節宣示:奧斯曼帝國要掀起一場全面的改革運動。隨之產生了一個專門術語“坦齊馬特”(指一八三九年開始的改革和整頓)。十幾年之后(一八五六)又頒布新的帝國改革法令,這個法令比第一個法令更具有可操作性。奇妙的是:帝國政治改革一開始遇到的阻力并不大。改革派代表如雷希德帕夏、富阿德帕夏都是實權人物,了解西方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也是實干家,說改就改,行政管理、財政、軍事、司法、教育,幾乎就是全面鋪開。以前的改革總是受制于舊軍隊,如今帝國的新軍(一八二六年取代舊軍隊)是歐洲式的軍隊,軍事將領大多屬于新派軍人。資料顯示,宗教界權威人士也沒有反對。廣大農村和牧區是否歡迎政治改革,不得而知,但城市里的市民在“古爾汗法令”頒布后表現出歡欣鼓舞。不管出于何種理由,至少說明“人心思變”,政治改革順應了部分“民意”。歐洲人希望看到保守的奧斯曼帝國出現政治變革,所以對“古爾汗法令”一片叫好聲。
“古爾汗法令”和一八五六年的帝國改革法令中,關鍵的內容,一是明確宣布保障所有臣民的生命、榮譽和財產安全;二是承諾頒布維護人民利益的新法律,宣稱新法律對所有的臣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平等的;三是在納稅、服兵役等具體方面,各階層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當改革家描述改革前景時,上自蘇丹,下至普通穆斯林都感到帝國富強和進步有希望,恨不得馬上就改出個名堂來。一些人甚至認為,法令要是早點頒布、早點推行,許多難題早都解決了。等真正實踐起來,好處并不怎么明顯,缺點倒是暴露無遺,于是連起初支持改革很堅決的人,也起來攻擊改革,幾乎要把事情整個兒推翻。“坦齊馬特”時期三十七年,兩任蘇丹阿卜杜·麥吉德和阿卜杜·阿齊茲全力以赴支持改革派搞改革,除了打仗(克里米亞戰爭)和借債,從未輕言放棄改革,而支持改革的臣民逐漸減少。由于國內矛盾加劇,一八七六年五月,阿卜杜·阿齊茲在政變中被廢黜,一年內連換了兩位蘇丹,后一位蘇丹就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一八七六——一九零九年在位)。
新蘇丹剛一上臺,政府就宣布實行憲政。一八七六年,奧斯曼帝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頒布,接著推選代表,召開議會,像模像樣地搞了一場歐洲式制度的演練。經過前面幾十年的改革實踐,奧斯曼土耳其人逐漸明白,西歐國家的強大不僅僅靠經濟和軍事實力,奧斯曼帝國僅僅學習西方的技術還不行,還要模仿英、法等國的政治制度。既然如此,為什么不盡快在奧斯曼帝國實現歐洲憲政呢?說立憲就立憲,說選代表就選代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一八七六年八月登基,十二月就頒布了憲法,第二年就召開了議會。不過,到第三年就解散了議會(總共召開了兩屆議會),在一九零八年革命之前有整整三十年(一八七八——一九零八)再沒有召開議會,經濟、文化領域的改革沒有停止,而政治上回到蘇丹專制。
總體來看,奧斯曼帝國的政治改革,無論出現挫折還是倒退,問題并不是遭遇反對派的強大阻力,也不是“改革不徹底”(比如沒有發動民眾等),不在于改革派軟弱不軟弱。恰恰相反,政治改革的起點高:一八三九年破天荒地要把“權利”、“平等”以法令形式固定下來,一八七六年快速地制定憲法,雷聲才響,雨點就落下來(議會召開了)。奧斯曼帝國史相關資料顯示,幾乎各階層都支持改革,看好改革。我們很難猜測,奧斯曼帝國各階層怎么那么容易達成“共識”?我們知道,奧斯曼土耳其人后來成功地走上西化道路,主張西化的一派坐了江山,對歷史上的改革有所夸大。不過,奧斯曼帝國歷史上對改革達成“共識”的情況也是有的。比如一七九二年塞利姆三世提出要改革軍隊,那一次的御前會議上各個政治派別確實達成“共識”,臣民也是支持的,因為俄國人已經打到黑海了,此前奧斯曼帝國與俄國打了一個世紀(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末)的仗,沒有贏過一次,再不改革軍隊,就要亡國了。一八三九年和一八七六年的政治改革實踐,我們排除史料夸大的成分,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奧斯曼帝國國內形勢很嚴重,外患迫在眉睫,非改革政治制度不可;國內各階層的利益都在受損,不支持改革不行。
不管怎么說,奧斯曼帝國的政治改革啟動勢頭很猛,最高統治者蘇丹本人決心大,改革派大臣支持強勁,反對力量弱,但是,隨著改革措施的展開,情況就發生了微妙變化,不支持的多了,反對的意見多了,改革漸漸停頓,最后的結果,不是蘇丹被廢黜(如阿卜杜·阿齊茲被廢),就是蘇丹驅逐了立憲派(如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做法)。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為什么僅僅推行了兩年憲政就停了呢?理由很簡單:建立議會,實行選舉,就是要讓議員們參與國策;政府發揮獨立行政職能,政府首腦就要行使國家行政權,宮廷就不再是整個國家唯一的權力中心了。這也就意味著,國家大事,不能由蘇丹一個人說了算。蘇丹此時才明白,原來所謂的憲政,就是限制蘇丹的權力,國家的權力中心要從皇宮移向政府、議會所在地。這怎么行?蘇丹無論如何不能忍受議會、政府與皇宮的并行,不能忍受蘇丹本人與議長、政府首腦之間權責的劃分。于是這位蘇丹解散議會,推行獨裁統治三十多年。
其實,自馬哈茂德二世的政治改革起步,到后來的“坦齊馬特”,前后幾位蘇丹都面臨著同樣的困惑:不引進西方的制度,單純的技術引進和局部改革不足以富國強兵,但西式的制度就要限制君主的權力;倘若蘇丹權力弱化,行省和屬地就會鬧獨立,蘇丹必然失去權威;只有加強中央集權,才能防止地方勢力分裂割據,但這樣做與西化的目標背道而馳。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幾任蘇丹的辦法是:改革要進行,蘇丹的權力不但不能受限制還要強化。結果是,經濟、法律、教育改革取得許多“標志性成果”(編制國家預算,建立國家銀行和私人銀行,廢除包稅制,改革土地制度,發展商業;設立混合法庭,頒布民法典、商法典;頒布教育法,開辦新式中小學和大學),但政治上加強了對地方的控制,比改革前更加集權,以至于被后人批評為“獨裁式的現代化”。
再看奧斯曼帝國各階層對待政治改革的態度。就算各個階層起初都支持改革,并且熱情很高,為什么后來又變得不熱心甚至反對呢?首先,帝國改革的兩道法令涉及政治權利方面的東西,并沒有落到實處。改革派描繪的改革藍圖,依然停留在紙上。經濟、法律、教育等領域的改革,得到實惠的畢竟是少數人。理想與實際的反差,澆滅了一部分人的政治改革熱情。其次,需要進一步探究的是,西方人和后來的土耳其人評價很高的“進步原則”(法令中提出的“權利”、“平等”)倘若落到實處,有多少人需要,有多少人歡迎?
“坦齊馬特”時期的法令頒布后,享有特權的穆斯林的反應是:非穆斯林(基督教徒、猶太教徒等)怎么能和穆斯林平起平坐呢?有的穆斯林認為把特權給予非穆斯林是不合適的。穆斯林知識分子援引“沙里亞”(伊斯蘭法)說,把權利讓給基督教徒,是與神圣的伊斯蘭法則相違背的。落實改革措施的過程中,宗教界人士也必須納稅(本來除了宗教義務“天課”外不向政府納稅),政府堅持征收人頭稅,宗教界人士嚴厲指責改革。在舊制度下獨享特權的穆斯林包稅人、商人也批評新政策。連那些普通穆斯林青年,也覺得讓基督教徒加入政府軍隊不合適。服兵役是穆斯林尤其土耳其穆斯林的神圣權利,新法令宣布“服兵役是帝國所有臣民的義務”,土耳其穆斯林不樂意接受。傳統奧斯曼社會的臣民劃分是:穆斯林、迪米人、非穆斯林、外國人。改革引進新的社會群體劃分方式,不以宗教信仰來劃分民眾,而以“奧斯曼人”取代傳統的劃分,也讓特權階層不高興。
法令宣稱提高非穆斯林(如基督教徒等)的地位,也沒有使他們滿意。他們的愿望,并不僅僅滿足于在法令上與穆斯林平等,他們需要與經濟地位相適應的政治地位,哪怕保持舊制度也能維護特權。比如希臘基督教徒,在奧斯曼帝國多年的“米勒特”制度下,他們在基督教社區中享有特權,一旦“平等”,優勢和特權就喪失了。所以,非穆斯林的真實愿望,要么是保持傳統特權,要么取得新的特權,總之要保持優勢地位,維持“不平等”才對他們有利。巴爾干半島的基督教徒就不甘心當帝國境內“平等成員”中的一員,歐洲國家不停地向蘇丹施壓,要求“妥善處理帝國境內基督教徒的地位問題”,民族主義者在煽動“自治”和“獨立”。
對企業主、商人而言,新政策確立了新規則,限制了他們獲取利益的途徑。以前他們通過尋求上層“保護傘”來獲取壟斷利益,往往不存在這個“準許”那個“規則”的,一旦失去特權,他們的利益會受損。另一方面,改革法令允許外國人在蘇丹管轄的范圍內持有、購買、處理不動產,這也沖擊了國內富有階層的“固有領地”。
可見,政治改革的目標沒有問題,但改革的措施真正推行時,不僅特權階層反對,連普通民眾也有意見,因為大家發現:“平等”原來不是個好東西!事實上,“平等”并不是所有人的愿望;每個人真正的愿望是自己始終高出別人、優越于別人。奧斯曼帝國的臣民在土耳其人的皇權統治下生活了幾百年,等級固化,意味著利益分配方式固化,這就是一八七八年之后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推行獨裁三十年的民眾基礎和社會基礎。
看來,“限制君權”,蘇丹不高興,實行“平等”,各階層有意見,那就只能退回到皇權時代,維持“不平等”,大家相安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