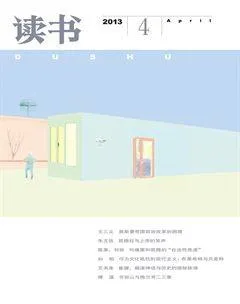法國“新社會學派”的啟示
二零一零年,我曾訪問位于巴黎的法國高等研究院。我認識的朋友伊莎白和麥港,都是社會學家,屬于法國“新社會學派”,又名“前蘇格拉底學派”,即表示研究在“理論”之先(因西方在蘇格拉底之前沒有理論一說)。所以第一件事,不是講一個“片兒湯”(不管它是本國還是外國的)理論,而要先講一個故事(最好還是歷史故事),然后一層層講出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理論”。既不是“理論先行”,也不是僅僅跟在材料后面,“實事求是”,說什么“眼見為實”,不敢越雷池一步,其他“唯心”的、“直覺”、“悟性”……都不能談。
這次造訪法國高等研究院,才使我進一步了解這一主流“新社會學派”的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直揭文字材料的表層以下的東西(這是我的理解)。在歐洲的思想學術史上,“實證主義”、“唯物質主義”已經統治了一個多世紀,現在,恰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了。
我在自己的課堂(特別是“方法課”,它也許是我職業生涯中講得最好的一門課)上,也在批“考據學派”,講“直覺”、“悟性”等等。簡單說吧,就是告訴學生,所有的史料其實都是“有限”的、“表面”的,不能做一個“爬格子”動物,僅僅跟在文字記載后面走。先說古代典籍,有一句話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為此呂思勉先生曾揭示出古書(如《史記》)是怎樣書寫的,談到要盡量保留原檔案的文字,而自己不做評價。所以面對這種書籍、文字,沒有一定的“準備”,是讀不來的。再舉《水滸傳》的例子,按錢穆先生的說法,不讀“金圣嘆點評本”,那里頭許多重要的意思(如對宋江的看法),你根本就看不出來(“僅知其事,不識內里之情”)。這里面的問題,在當代社會就更嚴重了(它把一切都“直白”了,而且是白而又白,像“白開水口號”一樣,白得非讓你表態接受了不可)。
也許,這正是我們的相合之處吧。
或許,這正是當代學術史、思想史上的一個大問題,應該引起有識之士的足夠重視。問題可能正是在于,怎樣才能識別文本的真正含義?
錢穆先生曾說:古人主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略道己意而止;其未盡者,則待讀者聽者自加體會,不以言辭強人必信;中國人自居必知謙恭退讓,故其待人則必為留余地。則無可盡言,無可詳言,并有無可言之苦,實即無可言之妙。抑且有心之言,則心與心相通,亦不煩多言。故中國文學務求其簡。
古人這些沒有寫清楚的地方,是不是可以依賴“考據學”去發現它的“真實含義”呢?許多人都是這樣主張的,章學誠卻持有不同意見,他說:“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需要依靠他所說的“性靈”、“神解精識”或所謂“高明”之處,否則就可能弄不明白。
在盡量保存史料本來面目的同時,我也曾多次強調,尊重當事人的“歷史意見”,不做過分的解讀;對于后世人的“時代意見”,不妨多多益善,并列保存,不贊成以“教師爺”態度,居高臨下,賣弄聰明,以為真理都在自己手中;承認歷史解釋很多都屬“猜測”,未必都能有硬實的史料支持;主張“吹牛”也要有“膽識”,有時寧可走在“刀鋒”之上。
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我通過近日的學術交流,也體悟出,當今世界其實是一個“二相社會”。進而言之,在上層政治與下層社會之間,有意無意上下相蒙,“貓膩”盛行,形成表里不一的“二相社會”(“假天下”與“真實世界”同時并存)。我也曾給吳思寫信說,你的“潛規則”和我的“反行為”,背后可能都存在這樣一個層面。所以我常常說,“當代史”最難治(盡管它已成為學術熱點)。我們治學問,不勘破這一層怎么行呢!
余英時先生曾指出,分別“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是宋代儒家的新貢獻。其關鍵即為不為感官(見聞)所限而別具一種更高的抽象認知的能力。如程頤所謂“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如王陽明所謂“良知”,也是一種“超知識”的性格。至乾嘉考據學派出現,則反過來認定“德性之知”必須建筑在“聞見之知”的基礎之上(《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取決于“功力”大小;只談“道問學”,于“尊德性”則置之不論了(《論戴震與章學誠》,或即魏源所說,“不必下學而自能上達,此尊德性多于道問學者也”)。
在我看來,所謂“德性之知”就是基于一種“悟”和“信仰”的“知”了。往往會產生“不期然而然”的不尋常的效果。
而章學誠所說的“性靈”、“神解精識”、“高明”云云,也可以說是對戴震等人的一個委婉的批評(章氏自詡“高明”以對“沉潛”,以“悟性”來對“記性”,可能都使考據學者難以言對)。
其實,司馬遷早說過,“《書》缺有間矣……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史記·五帝本紀第一》),哪能光靠什么書本子呢。
最近我又想到,無論我們怎樣面對所謂“純客觀”的“史料學派”(其實現在已沒有這種不帶“主觀性”的研究),過去所說中國“史觀學派”與“史料學派”之爭,恐怕還不能涵蓋所有這些問題(《余英時英文論著漢譯集》)。
讓我們再回到剛才的批評。我以為,其第一點涉及兩個問題,第一,就是所謂學問可能來自“當身之時代”,而不是一般的文字史料。
第二,就是不贊同與當下毫無關聯的“死學問”、“假學問”,只“為稻粱謀”,不管身外事,無意間成了孔夫子所說的“小人儒”。
前者,有如錢穆先生所說:“夫為學人之新材料者,莫過于其當身之時代。時代變,斯需要變;需要變,而學人之心思目光,宜亦隨而無不變。故誠能深入時代之淵海,則其周身所遭遇之材料,無一非新。否則昧乎時代之變,而徒求材料之新,豈不亦淺之乎其所謂新哉?”(《學龠·古史摭拾錄》)
回想我平生治史,多非因于新的材料,而是別有“依恃”。如研究清代經濟政策,為前人所未言及(參見《從清代農業政策看當代農村變革》,載《炎黃春秋》二零一一年第五期)。對清代糧政和糧食問題的研究,所用材料多出于《實錄》,人人可見,并非難得的檔案史料,但別人似乎并沒有這樣的感受,也就沒有寫出那樣一塊文章。其實,材料早就擺在那里,大家“視而無睹”罷了。
我于《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政府政策》一書“前言”中,曾經說道:我開始選擇這一題目時,可能只是“靈機一動”,但明眼人可以看出(在美國即曾經友人指出),它有著時代的影響,也與作者的個人經歷有關,這些都是無須諱言的。因此書中雖講的是十八世紀的中國,但它與二十世紀的今天,彼此間仍有密切的關聯,許多東西在今天也沒有失去意義;或許,正是因為處身于這一時代,也有一些切身的感受,我們才可能重新認識這段歷史和有關的文化傳統?
如何才可做到這點呢?錢穆先生說:要“先做一個時代的人”(《中國史學名著》)。錢穆先生進一步說,對于社會史研究,“應該從當前親身所處的現實社會著手”;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實為最真實最活躍的眼前史”,可稱之為“無字天書”;現前與歷史,“此兩者本應連系合一來看”(《中國歷史研究法》)。
有同學問,自己應該怎樣做呢?借用錢先生的話,就是:“學問應該從自己性情上做起。”(《中國史學名著》)我想,辦法之一就是發掘內心,找到自己“感興趣”而“有意義”的問題。當然,它首先是一個“當代史”和“當下”的問題。
與很久以前發生的歷史不同,“眼前史”是對我們能力的一種考驗,它不但離不開敏銳的眼光,還需要迅速的判斷,而且往往就在不久之后即可得到事實的檢驗——它不再像一般歷史研究方法那樣是一種“逆斷”,從結果來分析原因,而是相反,從前往后“順著來”——而且隨時可能受到每一個讀者不客氣的批評。
錢先生還說:做學問,須要做“活的學問”,若絕對與現實政治、外交、國家、社會、民生沒有絲毫關系,那就成了“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