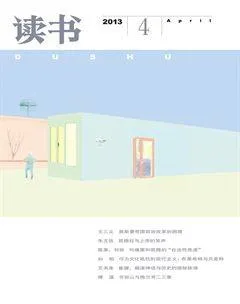歷史的敘事與行走
早在二十多年前,李開元先生在北大任教時就呼吁新史學、倡導史學變革。將歷史寫活、寫美、寫得好看是作者縈繞在心頭幾十年的夢想,也是他努力的方向。三十年來,作者致力于秦漢史的研究,他在幾十年史學修煉的基礎上完成的《復活的歷史:秦帝國的崩潰》(以下簡稱《復活的歷史》)一書自然不能被毫不經意地散落于當下火爆的通俗歷史讀物的展臺上。
敘事與行走是本書寫作的兩大特色,也是作者多年來的史學理念付諸實踐的努力。
中國歷史亙古連綿,中國史學博大精深,歷史材料浩如煙海。但涉及某一具體歷史事件時往往卻是史料匱乏,文言文體又講究精煉,而疏于細節,因此歷史的描述只能是只言片語,語焉不詳。事件與事件之間也因此而斷裂,缺乏整體性。作風嚴謹的史學家力圖逐一考證、挖掘史實。但任何完備的史實記載、史實考證都不可能窮盡生活。因此,專業的史學著作在講故事方面都顯得力不從心。對于歷史學著作來說,嚴謹與好看總是難以兼得。《復活的歷史》野心勃勃,它試圖兼得嚴謹與好看。
《復活的歷史》以宏大敘事的手法再現了大秦帝國的崩潰、風起云涌的農民起義以及后戰國時代的波瀾壯闊。歷史總是延續的,今天的故事早在昨天乃至更早的時候就在編寫草本。劉邦是這段歷史的重要人物,作者必須追溯他早年的歷史以及在塑造劉邦氣質方面產生深遠影響的更早年代。但是,對于平民出身的漢帝國締造者劉邦,當時社會的記錄者不可能預見他后來的飛黃騰達,因此,也不可能把寶貴的筆墨灑向一介平民。歷史上對劉邦早年生活的描述來自后者的追憶,一方面過于簡略,另一方面由于皇者至尊,難免有為尊者諱的嫌疑。作者想象豐富,依據《史記》中關于劉邦誕生的近似于神話的記述,再考察劉邦的個性與其兄弟之差異、劉邦不為其父親所愛,結合民俗學的研究大膽推斷劉邦是其母與人野合的產物。在尋找劉邦游俠氣質形成原因時,作者摒棄專業論文所常用的要點式,代之以講故事的方式,描述了戰國時代的游俠社會,尤其交代了信陵君、張耳等對劉邦的影響。不經意的描述間,游俠社會的由來、組成、氣質與政府政治社會之關系已在故事中躍然而出。
作者愿意把自己比作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和克里斯蒂筆下的波羅。史料就如作案現場留下的蛛絲馬跡,所以歷史的敘事就如案件偵破,依據有限的資料,利用發散式的推理和點觸式的聯想復活歷史。再者,歷史學家做結論又如老吏斷獄,材料不足、推理不暢,寧愿存不而斷。在論述陳勝張楚政權的先遣軍周文部隊為何在即將攻陷咸陽卻止步戲水時,作者顯示了其平衡老吏的嚴謹與偵探的大膽推理之間的能力。從后世的眼光來看,戲水之戰可視為我國第一次農民起義的轉折點。陳勝、吳廣的先遣軍在周文的帶領下,揮旌西進,一路勢如破竹,攻陷函谷關,抵達戲水,關中平原唾手可得。就在此時,周文卻未能渡水西進,千載難逢的戰機轉瞬即逝。司馬遷記載這個重大歷史事件時,只有寥寥十六字,歷史的謎團有如戲水上的煙霧,經久不開。作者從秦軍建制入手,結合秦國兵力在全國的分布情況,汲取秦始皇陵兵馬俑的研究成果,推斷周文止步于戲水,“不是不進,而是不能,之所以不能,當是遭遇到了無法西進的意外阻擋”(122頁)。這個意外阻擋就是進駐在首都咸陽郊外,固守京城外圍的京師軍的一部——中尉軍。作者還根據秦始皇陵兵馬俑的陳列、史料記載復活了秦軍陣形,為我們展示了兩千多年前最精銳軍隊的恢宏氣勢。
敘事的手法寫活了歷史,寫美了歷史。但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是謬誤。劉邦少年雖然讀書,卻沒有平日里記事的習慣。歷史人物的心理本來就難以揣測,史料上又沒有關于劉邦心理的記錄。作者卻將推理無限放大,為劉邦安排了初次入秦的切身感受。作者依據的是荀子在論著《強國篇》中對關東六國人初次入秦的感受。歷史是一幕劇,歷史事件的上演草蛇灰線,伏脈千里。上述諸多事件環環相扣,伏筆叢生。從重要歷史人物心理活動的角度來分析歷史現象是當下歷史學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人物心理的角度更是歷史敘事繞不過去的一道坎。因為歷史是以故事的形式論述的,故事都是由人來完成的,重要歷史人物的心理活動對歷史的影響毋庸置疑,所以歷史敘事要將歷史人物寫活、寫得有血有肉,它繞不過歷史人物的心理活動的描述。這也是作者冒著巨大風險揣測劉邦初次入秦感受的深刻原因。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司馬遷二十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游,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從這個意義上講,《史記》是用腳寫成的。以“歷史的行者”自居的李開元先生無論是從精神上還是從實踐上都繼承了太史公的衣缽。
《復活的歷史》一書的封面即是作者游歷多次的驪山秦始皇陵,封面上的人物是作者自己:一身旅行裝,手持地圖與電筒,脖子上掛著相機,雙肩背著旅行包,一副旅行歸來的模樣。不似歷史學家,更像旅行者。
專業類的歷史學著作中,作者往往都盡力藏在文字的背后,力圖向讀者展示出客觀性。李開元則反其道而行之,從文字背后走出來,閃亮登場。他帶著讀者走進歷史的現場,訪古問舊:訪豐縣龍霧橋、駐驪山、游灞上鴻門、觀戲水,考察兵馬俑遺跡;又經邯鄲、走臨漳、過成安、兩渡漳河、吊殷墟、望鄴城、登金鳳臺、信步于趙王城……作者拿起相機,拍下歷史的遺跡,試圖盡可能地為讀者透露歷史事件的現場信息。情不自禁處,作者慷慨抒懷,嘆息歷史,恍然間似乎已穿越了歷史,與古人相往來。
人類的生活受著自然環境的深刻影響,激進的歷史學家甚至有“環境決定論”之說。所有的歷史都在一定的時空中展開,中國歷史亦掙脫不出自然環境的束縛。研究歷史事件發生的空間,自然是歷史學研究的應有之義。文獻整理與實地考察相互印證當是此項研究的根本方法。此種方法可見《復活的歷史》一書對劉邦豐西澤中亭舍犯法釋眾之后,為何藏身于芒碭山的解釋。作者親臨現場、實地考察,結合文獻研究,得出結論:“芒碭山有山有水有樹林,便于藏身,地區偏僻,行政界于芒縣和碭縣、泗水郡與碭郡之間,屬于統治薄弱的邊緣。芒碭山與沛縣間,雖說隔了郡又隔了縣,距離卻不過二百余里,正是這種行政的分割和隔離,地理的有利和近便,使芒碭山中的劉邦集團既能躲開沛縣當局的追究,又始終和沛縣吏民保持著聯系。當天下有事的時候,沛縣吏民能夠想到招他,他也能夠迅速返回沛縣,終于成就偉業大事。芒碭山武裝割據,不僅是劉邦集團的起點,也可以說是漢帝國的起點。”(58頁)
但在當下,進行實地考察一定要細心謹慎、火眼金睛。人類歷史雖然至少已有十萬年,但這十萬年對地球來說,只是極小的一段。地球山川大勢在工業革命以前變化并不大。但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改造自然的力度、速度飛快提升。自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改造自然的進程也大大加快。諸多歷史遺跡在此進程中消失,諸多曾經極大影響歷史事件的山川河流改變了面貌。《復活的歷史》一書中的漳河曾經水流湍急,在巨鹿之戰中,是項羽攻擊王離軍的一條天然障礙。但今天的漳河,河水平淌,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崢嶸峻險。因此,現場考察時自然要對環境的變遷做一番梳理,方能深刻理解歷史。
作者是歷史的行者,當他行走在歷史當中時,我們從他按捺不住的激情中明了,歷史在他心中復活了。但作者應該花較大的氣力繪畫出自己行走的路線圖,與歷史地圖相對照,并闡述影響歷史走向的重要自然環境的變遷。唯有這樣讀者才能更加深刻理解歷史的現場,在作者心中復活的歷史,才能在讀者眼中復活。
(《復活的歷史:秦帝國的崩潰》,李開元著,中華書局二零零七年四月版,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