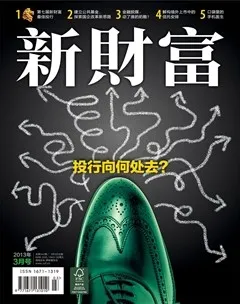解構境外上市中的信托安排


借助信托這一工具,實際控制人就可以在境外上市時,一方面通過轉換身份等方式繞道實現重組,另一方面又保證資產倒手過程不失控。此外,還可以悄悄地把部分人作為酌情信托受益人隱藏在背后而無需披露,真是一個完美的布局。
“房姐事件”一不小心牽出了潘石屹的陳年舊事,使得境外家族信托這一神秘領域,再次曝光在媒體之下,成為熱議焦點。前段時間另外一位房地產大鱷龍湖地產主席吳亞軍,在與丈夫蔡奎離婚事件中,也讓我們看到了家族信托的妙用,蔡奎家族信托的“銀地”(Silver land)最終漂離了吳亞軍家族信托的“銀海”(Silver Sea),僅一紙協議就解決了夫妻分家問題,連公告都不用發,避免了通常通過股權分割析產帶來的稅負成本及交易成本,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對上市公司的沖擊。
實際上,在境外上市過程中,信托安排屢見不鮮,早已經成為企業跨境重組及資產規劃的一個利器。那么,境外上市中典型的信托結構通常是如何安排的呢?2012年末在港上市的中國白銀集團(00815.HK)就給我們詳細演繹了這一過程。
中國白銀集團的境外信托架構
中國白銀集團在中國境內的運營公司主要是江西龍天勇有色金屬有限公司(簡稱“龍天勇金屬”),其股權分別由陳萬天(66.18%)、吳文勇(15.64%)、陳萬龍(7.27%)、陳榮(7.27%)和萬成來(3.64%)持有,其中實名股東陳萬權及陳萬成作為代名人,代表陳萬天及配偶周佩珍持有部分股權。
為了完成上市重組,大股東陳萬天的配偶周佩珍選擇了變換國籍方式,意圖繞開《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俗稱“十號文”),并自2011年9月起成為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國民(也就是媒體爆出的俏江南主席張蘭選擇的國家)。其重組方式可以簡單概括如下:周佩珍女士在境外設立了Rich BVI、中國白銀集團(開曼)、中國白銀(BVI)和中國白銀(香港)等一系列中間控股公司,又通過中國白銀(香港)在境內設立了一個外商獨資企業(WFOE)“浙江富銀”,進而又用這家WFOE收購了國內的“龍天勇金屬”及其他相關運營公司,從而完成境內權益置入境外的重組過程。
但是緊接著問題出現了,原股東把所持股權都轉移到了周佩珍手上,利益怎么保證呢?于是周佩珍(作為財產授予人)設立了五個酌情信托,即陳氏家族信托、WWY信托、CWL信托、CR信托及WCL信托。這五個信托分別為原“龍天勇金屬”五位股東陳萬天、吳文勇、陳萬龍、陳榮和萬成來的家族信托,各自信托在擬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也與原股東持股比例相同。
我們進一步看,在信托結構具體安排上,各信托均以周佩珍作為財產授予人,均以瑞士信貸銀行信托有限公司(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作為受托人,而五位原股東分別為各自信托的保護人,五位原股東及其配偶、子女等為各自信托的受益人。
財產授予人在授出財產后,根據五項信托,概無擁有保留權力。而受托人則擁有受托人慣常獲賦予的權力,包括:動用信托基金及其所得收入的全部或任何部分用于為任何受益人維持其生活、教育、發展或其他方面的利益;為受益人的利益支付或轉讓信托基金及其所得收入予任何其他信托的受托人;為受益人的利益持有信托基金及其所得收入。
特別需要關注的是信托的保護人。受托人僅可在獲得各自信托的保護人同意的情況下行使若干受托人酌情權,其中包括:1)厘定終止信托的日期;2)更改信托的正式規管法律;3)向受益人指派收入;4)于信托終結時向受益人指派資金及收入;5)一般指派及預付權;6)剔除受益人;7)增添受益人;8)更改信托權力及信托的條文。只要各信托保護人仍然在職,受托人將不獲授予任何投資或管理資產的權力,包括干預公司業務的管理及股份所附帶表決權的權力。各信托的投資及管理資產的權力僅授予該特定信托的保護人。各信托的保護人亦有權委任或罷免該特定信托的受托人。
中國白銀集團的上述安排,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境外上市過程中借助境外信托完成跨境重組及境外資產安排的案例。其核心要點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步考量:變換身份完成重組
首先,從完成跨境重組需要出發,為了繞開十號文限制,會選擇由原股東或其配偶轉換國籍。其依據是十號文第11條規定:境內公司、企業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設立或控制的公司收購其境內關聯公司,需報商務部批準(而商務部也不會給你批)。換句話說,如果換了國籍,非境內自然人,再來收購境內關聯企業就無需商務部批準,按照審批權限,地方商務部門也可審批。也就是說,十號文關聯并購限制,只管中國人,不管外國人。
目前市場上比較流行的目的國就是本案例中提到的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就該國而言,通常花20萬-40萬美元(視方式不同),大概4-6個月時間,就能夠取得該國國籍(不僅是居留權)。而且這個國家一個重要優勢是,非來自當地的收入采取免稅制;此外,對某些人更好的是,該國跟中國尚未建交。
但是為了符合十號文第11條,取得境外國籍的同時必須放棄中國國籍,這對類似張蘭女士這樣的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企業家來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而且出入境也越來越不方便。所以一般情況下,大股東不愿意自己轉換身份,而是讓自己的配偶或父母去轉換身份,并以配偶名義在境外設立公司并收購國內運營公司。就如同在SOHO中國的案例中,境內各公司賣給了潘石屹配偶張欣所控制的境外公司,當然不同的是,張欣自始就是外籍,而非臨時買來的。
第二步考量:境外信托重新分配權益
在利用配偶或者親屬變換國籍以便繞開十號文完成重組的同時,也造成了原股東與配偶或父母的利益安排如何實現的問題。通常情況下,這么大額資產完全放在配偶一方名下,不少人是睡不著覺的;放在父母名下,也還可能出現兄弟姐妹爭產問題。那怎么辦呢?這個時候,信托就派上用場了。
在重組完成后,配偶或父母會簽署一份授予協議(Deed of Gift),將其所持全部股權,無償轉讓給一個受托人(Trustee)專門設立的一個SPV公司,即以授予人身份(Asset Contributor & Settlor,國內信托法上通常稱為委托人)設立一個信托(Trust),股權即歸屬于信托,從而不再屬于授予人,通常授予人也不再保有其他權利。這樣配偶或父母轉換身份,設立境外公司并收購境內公司的歷史使命就光榮完成了,旋即就可以卸任股東身份,交還給信托。而原股東及其家族成員等會作為受益人(Beneficiaries)享受信托利益。信托受托人通常會由一家聲譽卓著的金融機構擔任,以確保其可靠性;當然,在境外受托人不必是持牌金融機構,任何機構和自然人都可以作為受托人,只要授予人和受益人信得過。
而受托人會嚴格按照信托契約(Deed of Trust)約定行事,掌管財產并將收益按照信托文件約定派發給受益人。
第三步考量:信托架構的微妙設置
通過信托來處置財產,這其中信托契約設置就很關鍵,特別是受益人如何安排,收益如何分配等事項。根據受益人及收益分配安排不同,信托可以分為酌情信托(Discretionary Trust)和固定信托(Fixed Trust)。酌情信托中,受托人有權決定受益人名單上哪位受益人可獲得若干金額饋贈,其他信托資產或其他利益。發放資產的時間、形式亦由受托人酌情決定。而固定信托中,則注明各受益人、各人可得的饋贈,饋贈時間及方法亦清楚注明,受托人只能按照此約定分配收益。
很顯然,酌情信托中受托人權力是非常大的。在英美法系下,信托是一個非常靈活的制度安排,按當事人意愿自治的空間非常大,只要不違背所謂的“公序良俗”,任何條款都可以設定。比如假定授予人與受益人是配偶關系,授予人可以在信托契約中限定作為受益人的配偶不得離婚,否則喪失受益人地位等。比如在著名的郭氏兄弟紛爭案中,作為受托人的鄺肖卿(郭得勝的夫人),就因為大兒子郭炳湘的緋聞女友干涉公司事務,而把他剔除出受益人名單之外。
為了制衡受托人的權利,英美法系信托制度中還有保護人這一角色,這在中國的信托法里面是沒有的,而保護人的權利也可大可小。在中國白銀集團的信托安排中,保護人的權利就相當大,這樣受托人就成了所謂的被動受托人,而保護人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掌握生殺大權的“老板”。這樣的制度安排,在境外上市重組中是非常有價值的,如同中國白銀集團的案例一樣,通常原股東會作為保護人出現,掌控整個信托安排的重大事項,不僅避免自己的利益受損,而且將其他受益人的利益分配權掌握在自己手中。
也正是因為如此,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 章)第XV部的規定,信托保護人作為廣義的“成立人”(即授予人)范疇,也視同于權益股東(beneficiary owner)對待,這樣一來,反而滿足了公司上市中有關股東持股連續性的要求。而根據前述香港法規規定,酌情信托的受益人則反而不用披露自己的權益,這樣又恰好滿足了當事人保密的需求,無需詳細披露到底哪些受益人存在及每個人有多少份額等細節。也正是因為保護人的特殊地位及酌情信托受益人無需披露權益,因此,在境外上市架構中的信托安排,通常會采取酌情信托。
回過頭來看,借助信托這一工具,實際控制人就可以在境外上市中很好地實現跨境重組安排和境外的資產規劃安排。一方面通過轉換身份等方式實現了重組,另一方面又保證資產倒手過程不失控。此外,還可以悄悄地把部分人作為酌情信托受益人隱藏在背后而無需披露,真是一個完美的布局。從這一角度看,潘石屹也可以合法地作為張欣設立的酌情信托受益人而無需讓外界知曉,同時張欣又可以反過來在信托契約中設定若干條款約束潘石屹的行為(當然這只是理論上成立,并無八卦揣測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