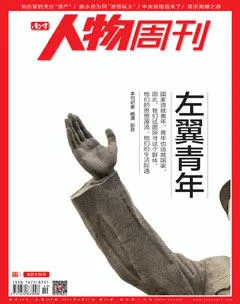勞動、尊嚴與夢想
一般的經驗是,值得一看的劇目要么是經典、名家之作,要么名字里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詞語。《我的勞動、尊嚴與夢想》,幾個很不時髦的字眼放在一起,實在不像一出戲的名字。
小劇場里,所有演員幾乎都沒有舞臺經驗,來回串場顯生澀,臺詞的頻率忽高忽低。觀眾也動來動去,發出干擾的聲響。實在不像一出戲。
怎樣才算一出戲?演員們其實并不確知。她們全是家政女工,每周休息一天,閑暇時聚在一家名為“打工妹之家”的公益組織,參加業余活動。在中戲教師趙志勇的指導下,她們演出了這場戲,講述自己的生活。
沒有一個主要的戲劇沖突貫穿全劇,每一幕是一則小故事,演員們輪流主演,有的被業主無故刁難,有的和業主情同一家,有的在疲憊中思念家鄉,有的計劃辭職回家后組織姐妹一同養老。這種并列的戲劇結構并不符合起承轉合的戲劇規律,卻是導演有意為之,把故事和講述故事的權力最大限度地交給女工本人。導演的加工主要在于調動多樣的戲劇手段,為講故事的人提供表達的形式——小品式的表演、獨白、舞蹈、紀錄片,架好機器、遞上話筒、搬來椅子、披上紅綢,在形式的變換中,讓她們練習自我表達。她們平時哼唱的小調,最后也進入劇本,成為抒情的部分。
講述——不同形式的講述,成了這出戲的中心,象征著家政女工的主體性自覺。套用一句濫俗的廣告語,她們為自己代言。尤其在紀錄片訪談中,演員們談起各自的職業史,勾連起國企員工下崗、城鄉分離等時代大潮。作為市場化、城鎮化的后果,她們的離鄉背井早被認作是發展的代價和必要的犧牲。勞動曾被機器替代、被資本剝奪,尊嚴誤認為也可以拿來買賣,夢想只是維系生活、讓下一代獲得夢想的權利。劇名中的這3個詞語如今已被那些并不真正需要它們的人過度使用了,偏是這出簡陋的小戲,顯得如此切題。
其戲劇性首先來自于時代,這恐怕也是許多導演起用非職業演員的原因——真正的生活就附著在這些人的身上,不需要表演的過濾。最動人之處,就是看演員們坐成一排,靜止、凝視,再行走、轉身,她們的沉默,本身就是敘事。
研究民眾戲劇的印度年輕人坐在臺下觀摩,很是激動,幾次搶過話筒——他很關心這出戲的后續效果。有觀眾甚至擔心,這些家政女工把遭遇表演出來,會不會影響工作?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對戲劇的褒獎,因為只有足夠接近生活的藝術,才有可能影響生活。如果她們演的是不痛不癢甚至連劇名也讓人看不明白的戲,那么大概不會有人替她們捏一把汗。事實上,一個戲劇的夜晚并不能改變社會,但它影響生活,哪怕觀眾第二天就把她們忘了,但有些演員——家政女工的性格已經悄悄發生了改變,她們不再內向,開始樂于與人交談。沒有人能否認,這才是戲劇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