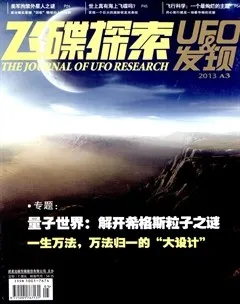飛行科學:一個最絢爛的主題

“1802年6月,洪博爬上當時公認的世界最高峰,也就是秘魯欽博拉索山的火頂山,海拔6267米。盡管危險,洪博還是明察秋毫,注意到一般人容易忽略之處:‘在雪線之上,也就是5000余米的高處,有些巖石上仍有苔蘚。上一次,我們在比那里低780米之處看到綠色苔蘚。龐普蘭德(洪博的伙伴)在4500米的高處抓到一只蝴蝶,我們在比那里高800米之處,看到一只蒼蠅……’”這是在《旅行的藝術》一書中,提到科學旅行家(或說旅行科學家)洪博獨到之處時的一段描述。
如同對作家艾倫狄波頓旅行主題作品的評論,如果這趟旅行的背后有一個靈魂,絕不是馬可波羅和麥哲倫,而可能會是達文西或達爾文;絕不是哥倫布和鄭和,而可能會是洪博或法布爾;絕不是凱薩和狄亞士,而可能會是帕斯卡爾或蒙田……這種旅行,不見得是指一般所謂田野調查和實地觀察性質的科學工作與正規實驗,而是由一種親身經驗啟發的科學思考與情懷。
一晚在素食餐廳,暑假迷上西游記卡通的兒子和女兒看到墻上的一幅《八仙過海》圖,開始好奇地問起一些直白而好玩的問題,例如為什么孫悟空可以飛那么遠而唐三藏卻不能(或者不要)?八仙中為什么有的這樣飛有的那樣飄?甚至我還必須從頭幫他們復習:其實在超級英雄的正義聯盟中(超人、蝙蝠俠、蜘蛛人),真正會飛行的只有超人,蝙蝠俠算是滑翔,蜘蛛人算是擺蕩和跳躍。《八仙過海》圖的俗世重點,當然在于“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小孩們對這些仙人騰空過海的法寶與技術,是充滿好奇與欣賞的。同樣,飛行之旅的重點,也是自己稍微用心對于掙脫(或利用)地心引力與飛行科技的一種提問與觀察。
人類和飛行之間,或者應該說人類和地心引力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奧妙與糾結的,不要說夢想,就連夢境,都可以說“飛行”是一種可正可邪的事物。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和記憶:自己做過的好夢與噩夢中,都有以飛行為主題的,一種例如是自己展現一股小小的飛行超能力,神氣活現地“飛”奔,瞬行百里;另一種同樣是騰空,不過加入一種“失控”的元素,毫無著力地被拋離地表,身體不知會飄落何方,感覺到一種莫名的恐懼!這樣可正可邪的飛行夢境記憶與經驗其實在提醒我們一件事:飛行的本質一定并非完全貼近虛幻、夢想與浪漫,而應該比較趨向現實、生存與科學,但兩端之間又充滿重合與混雜。
(熱)氣球是航天器的一種,在飛行科技分類的位階上屬于單純利用空氣浮力的無動力浮升器。它的飛行原理也可以說是最簡單的,它配備填充氣體的袋狀物,當充入氣體的密度小于其周圍環境的氣體密度,且由此壓力差產生的靜浮力大于氣球本身與其搭載物的重量時,氣球就可浮升。氣球作為一種交通工具可用來運載觀測儀器和乘客,只裝載設備的無載人氣球經常用于對高空大氣環境的科學研究,有時也用于測定宇宙射線。很多人不知道,其實熱氣球最早是由中國人發明的,稱為天燈或孔明燈,在公元二三世紀被發明,用來傳遞軍事信號。知名學者李約瑟也指出,公元1241年,蒙古人曾經在李格尼茲戰役中使用過龍形天燈來傳遞信號,而歐洲人直到1783年才向空中釋放第一個內充熱空氣的氣球。
到了18世紀,法國造紙商孟格菲兄弟在歐洲重新發明了熱氣球。他們受碎紙屑在火爐中不斷升起的啟發,用紙袋把熱氣聚集起來做實驗,使紙袋能夠隨著氣流不斷上升。1783年6月4日,孟格菲兄弟在里昂安諾內廣場做公開表演,一個圓周為33米的模擬氣球升起,飄然飛行了2.4千米。同年9月19日,在巴黎凡爾賽宮前,孟格菲兄弟為國王、王后、宮庭大臣及13萬巴黎市民進行了熱氣球的升空表演。同年11月21日下午,孟格菲兄弟又在巴黎穆埃特堡進行了世界上第一次載人空中航行,熱氣球飛行了25分鐘,在飛越半個巴黎之后降落在意大利廣場附近。這次飛行比萊特兄弟的飛機早了整整120年。在充氣氣球方面,法國的羅伯特兄弟則是最先乘充滿氫氣的氣球飛上天空的。
“飛機是怎么飛的?”這個看起來基本通俗的問題,其實有著非常復雜深奧的答案,甚至是現今科學還沒有辦法做完整解釋與掌握的,至于早期教科書上提到的白努利定律與傳統流體力學,例如“由于機翼的上方是彎曲的,其上方距離會比下方來得長,因此被分成上下兩股的空氣為了要同時匯流在一起,通過上方的空氣速度就必須要加快才行;這樣一來,根據白努利定律,由于上方的空氣速度變快了,因此其壓力降低。于是在機翼的上下之間就產生了壓力差,使得機體被由壓力高的地方往壓力低的地方推,也就是由下往上推;而這,就是飛機之所以能飛起來的原因”之類的說法,不是無法全面解釋,就是被后面的現實觀察與科學研究給推翻了。正如我的一位機師朋友說:“自己駕駛客機都已經有好幾年的經驗,卻無法完全搞懂飛機到底是怎么飛的?!”
人類科技和天然生物之間的競合相長、愛恨情仇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的。比如一般流傳萊特兄弟的飛機創作是受到鳥類飛行的啟發,就連兄弟倆的意見都是不同調的,韋伯·萊特在自傳中堅持認為鳥類是他們教育的一部分,而另一位奧維爾·萊特則認為鳥類飛翔的觀察只給了他們靈感。而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有數百家從事研發、制造并販賣飛機的小公司。據航空工程師與名作家諾威估計,那段期間共有10余萬種不同的飛機在天上飛來飛去。后來,許多飛行員都撞了機,許多航空公司也都破了產。在這10余萬種形形色色的飛機中,大約只有100種存活下來,形成今日航空的基礎。飛機的演化過程活脫脫就是達爾文的演化流程,少數存活下來的飛機,全都極為穩定、經濟又安全。
當我正仰望著天空,追蹤飛機的來處去向時,幾只樺斑蝶和鳳蝶又從面前翩翩飛舞而過,加上稍早遇到的眾多紫斑蝶和善變蜻蜓,以及手邊剛好有一篇《科學人》雜志標題為《蜘蛛吹氣球》的科學新聞,提到一些初生蜘蛛可以利用“蛛絲氣球”進行播遷,讓人不得不又驚想起這些不到0.01克的小東西,無論在飛行模式、細微構造與遺傳信息各個方面,依然著實地展現出浩瀚天地、宏偉生命的精妙與感動。
哲學家尼采曾提到“豐富人生”這個語匯。1873年的夏天,他寫了一篇論文,來區分搜集事實與運用已知事實:前者像是探險或研究,后者則是內在或心靈的充實。他認為前者沒有什么,而贊揚后者,并且表示以近乎科學的方式去搜集事實注定徒勞,真正的挑戰是利用事實“豐富人生”。
我喜歡欣賞飛行,探究飛行物不是沒有原因的。一向給人以樂觀甚至調皮形象的科學家費曼曾表示:“我們很幸運,能活在一個還有很多新發現的年代。這就像發現新大陸一樣——你只能發現美洲一次。我們這個年代是發現大自然基本定律的年代,這個日子永遠不會再來了。”我寧可相信他這句話是開玩笑的,因為這樣的觀點有些消極。我相信,單是“飛行的奧妙”及其延伸的問題探究與衍生的科學趣味,就絕不是哪一個年代哪一個地區或哪一群人,甚至不是人類可以獨占與窮盡的!
在這些年參與或聽聞科學工作與科技教育的日子,我深深感受到科技進步帶來的方便與效率,但這樣的背景有時會造成在不必要或不適當的時候,科學脫離切身與現實,科技疏遠觀察與生活。藝術家羅斯金曾說:“科技使我們輕而易舉地到達美景跟前,但美的擁有和欣賞不是可以簡化的……我教畫的目的,是希望我的學生學著去愛大自然,而不是教他們盯著大自然去畫畫。”
其實不單是藝術與美的欣賞,科學科技本身亦然!飛行是一個好主題,因為“飛行”對眾生而言是一種長遠歷史的創新,多元發展的傳統,不退流行的經典,無邊無際的發現,永不褪色的探尋!而在其他相關事情上的一個實踐,就是鼓勵科學家與科技人去旅行,不單是為了放松,而是一種融入生活與自然的旅行,實踐強度越高越好,結構差異越大越好,形式限制越寬越好。這就如同帕斯卡爾在《沉思錄》中寫出的:“如果我們對實物不以為然,畫得再怎么像、再如何令人激賞,也沒有用!”
早先為洪博立傳的史瓦振博格,為這部傳記取了個副標題——《一生能夠締造的成就》。他將洪博那不尋常的好奇主要歸納為五個領域:“①對地球及其棲居生物的知識。②找出支配宇宙、人類、動物、植物、礦物的更高自然法則。③發現生命的新形態。④發現罕為人知的土地,以及這些土地的各種產物。⑤了解新的人種,包括其習俗、語言及文化發展脈絡。”洪博的一生都在興奮地證明:“我們應該向這個世界探詢正確的問題!”
用心旅行就是一場最華麗的實驗!飛行科學就是一個最絢爛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