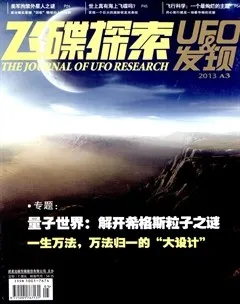UFO報道:美國主流媒體為何避而不談?
事情可以從10余年前發生的一件事說起。
2002年11月26日,北美防空指揮中心收到許多報告:在加勒比地區的特克斯和凱科斯島嶼有不明物體在空中留下的凝結尾流現象。幾個空軍機場出動了戰機對不明物體進行攔截,但卻沒有發現任何物體。隨后,一些民航駕駛員在佛羅里達和印第安納也發現了空中的凝結尾流現象。
此次令人激動的報告并沒有在美國媒體界引起些許關注。對剛剛經歷過“9·11”苦難、將國防安全時時掛在嘴邊的美國人來說,這的確顯得有些不同尋常。一個不明物體居然可以在美國領空四處亂竄,而主流媒體卻視而不見、報道寥寥,這使得很多人感到疑惑。那么,該如何來解釋這種媒體缺失好奇心現象的根源呢?
事實上,主流媒體對UFO報道的缺失由來已久,并不值得大驚小怪。主流媒體早就秉承了一個傳統理念:有關UFO的報道只能當做花邊新聞。這一觀點是如此根深蒂固而又廣泛流行,以至于當有些編輯和記者想要嚴肅對待、精心研究UFO現象時,他們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被同行孤立了。
在外界,對UFO現象有一個普遍流行的誤解,那便是看到UFO的人要么缺少文化素養,要么是精神方面有問題的人,要么就是為了個人私利而胡編亂造的混混。因此,許多人認為,那些對UFO感興趣,想報道UFO的記者也可列為同類。即使是那些曾經遭遇過UFO的記者和編輯,也會被眾人質疑其作為媒體人的誠信度。
2005年2月24日,當ABC電臺播出彼得·詹寧斯的節目《UFO:眼見為實》時,UFO界曾看到一些希望,以為UFO報道將會與其他報道一樣被同等看待。但事與愿違,此節目不是對UFO現象進行客觀報道和分析,而是喋喋不休地充斥著對UFO的臆想和猜測,似乎這就是對UFO的唯一解釋。而對于那些一直活躍在UFO研究領域的人,ABC維持了媒體對待UFO現象的一貫固定思維模式,觀點也大同小異。
目前,媒體對待UFO現象的態度依然是頗不以為然,在媒體看來UFO一點也不神秘。即便遭到質疑,媒體往往認為只需發個措詞油滑、確不知情的掩蓋聲明即可。然而,事情并非總是如此。在20世紀40年代,主流媒體會定期發布UFO報告。當時,UFO現象還不為大眾所了解,也沒有像五六十年代那樣被狂熱分子所玷污。后來,由于在研究UFO的問題上沒有取得什么實際進展,或者說有力證據稀少,所以,大多數媒體顯得有些灰心喪氣。
到了70年代,有關UFO的報道一般都被放在靠近后面緊鄰著星座的頁面位置。除了一些地方性小報,報紙很少報道UFO目擊事件了。即使是小報登了,也會被認為是個故事,沒人當真。在大都市的報端,偶然見到的有關UFO報道的豆腐塊文章,也是被放在娛樂板塊的。
但有時也會有例外。2006年11月7日,在芝加哥的奧黑爾國際機場發生了UFO目擊事件,數千人目睹到一個巨大的UFO飛越機場。但直到2007年1月1日,《芝加哥論壇報》才決定刊登一篇有關奧黑爾機場事件的文章。當文章發表后,人們驚奇地發現,文章寫得非常客觀,即沒有嘩眾取寵,也沒有像往常的UFO報告那樣發表任何編輯觀點。
勇敢的心
但還是有一些記者勇敢地迎接挑戰,嚴肅認真地研究起有關UFO的問題。遺憾的是,許多人為此在事業上遭遇挫折,剩下的人不是被冷落了就是被排擠了。有位記者偏不信邪,她就是50年來一直敲打白宮的資深記者薩拉·麥克林頓。作為一名自由記者,薩拉以尖銳和煽動性的提問而聞名,在業界樹立起了獨斷自信、堅強不屈的形象。
1998年,薩拉在她的報刊專欄和電臺評論節目里代表UFO學者和熱心人士向政府呼吁,希望能解禁UFO并召開一個全球性的UFO科研大會。她說:“uFO的蓋子正在被逐漸打開。有個倡議在全國發起百萬人聯名簽字的活動,請求召開針對政府公務員證人的公開的國會聽證會。”1998年3月30日,薩拉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指出:“UFO——這個多年來在每個州都出現過的無法解釋的空中不明飛行器的術語,實際上是外世界來的訪客。它們相信一個由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組成的社會……對美國甚至整個地球而言,真正的危險在于政府隱瞞了如此多的秘密。那些知曉這個秘密的人雖然明知事情千真萬確,卻苦于此話題屬于禁忌,無法傾訴。還有的人盡管相信UFO是外星人操控的智能飛行器,但是非常擔心會因他們所持的觀點而被嘲笑和誤解。此情況在媒體從業人員中更為突出。因此,美國實際上是在舍棄弄懂UFO的更多機會,或者說并不鼓勵對此進行研究。而事實上,對UFO進行討論本身于美國也是有益的。”
也有一些記者甘愿冒險去報道UFO,但卻發現他們的努力遭到意想不到的挫折。
最近,記者格雷戈·波恩寫了一篇題為《媒體掩蓋UFO:更多的證據》的文章,談到了他當年在紐約的《波基普西》雜志工作期間,由于報道UFO現象而發生的一段經歷。1985年8月25日,波恩和其他幾位記者從一位攝影師口中得知,一個巨大的回旋飛鏢狀UFO正緩慢地飛越他們上空。攝影師說飛船在向南飛,也許可以從三樓以上的窗戶中看見。波恩和其他人蜂擁至窗口,驚奇地看到離地面約30米處有一個黑色形狀的物體正向他們緩緩飛來,同時發出黃色和紅色的光。這個烏黑發亮的物體很大,寬度至少有60米,從他們頭上12米處飛過。波恩及其同事興奮異常,認為他們遇到了世紀話題。他們聯系了美聯社、《今日美國》、《甘尼特》等經常來往的報社,得到的回答是不予報道。從高層傳下來的話是:一個字也不許提。有數以千計的人看到了實實在在的物體在空中盤旋,而且還有攝影師拍到的照片,但卻找不到關于這件事的任何報道。
媒體封鎖
盡管政府和軍方不承認,但其在很多時間里確實對封殺UFO報道負有責任。在美國,并沒有嚴格的政府法令禁止報道UFO,但一些禁忌仍然存在。1996年,某位BBC的高層說漏了嘴,透露說在媒體報道黑色三角形UFO方面上頭有道“D令”(指國防機密通知:封鎖)。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管,曾是BBC深受歡迎的科學節目的制片人。他告訴一位調查者說,黑色三角形UFO是英國當局“很看中的D令”,因此,即使有很多證人提交了報告,BBC也不會報道這個奇怪的UFO。
這位前制片人認為,政府對報道UFO緊閉大門的原因是:政府事先已告知BBC此飛行器是軍方新秘密武器實驗計劃的一部分,按照保密法應予以保護。
而在美國,媒體對有關UFO現象的調查報道已經有了“自律”的行規習慣。主流市場上的大型媒體登出來的都是些愚蠢到底的UFO故事,正當的、合乎情理的與UFO有關的事件非常罕見。即使登了頭條,記者也十有八九會加上一些個人觀點,以引發一種“玩笑因素”。
不過是個大笑話?
這方面最好的一個例子是科學作家李·戴1998年7月1日在ABC新聞網上發表的專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勞倫斯·洛克菲勒資助的一項呼吁重審UFO有關證據的研究。這份50頁的報告是由國際知名的九位科學家聯合研究的成果,領頭的是斯坦福大學的天文物理學家彼得·斯特羅克教授。他們主要研究了UFO事件中的各種物理現象,比如照片、雷達、生物效應等等。
戴寫道:“無論報告的措詞如何謹慎,最終獲益的是那些相信我們被外星人訪問過的人。這當然并不是報告的主題,但通過呼吁對這種觀點進行更為科學、周密的細察,斯特羅克和其他科學家將自身暴露于‘玩笑綜合征’之下。下一次當他參加科學座談會走進屋子時,他肯定會聽到幾聲傻笑。
“在研究結果發表后與記者交流時,斯特羅克說也許整個宇宙充滿著生命,但大多數物理學家并不相信能從一個星球飛到另一個星球。大多數物理學家?那他呢?他情愿說讓我們再換一個角度看待UFO證據吧。OK,但千萬別笑。”
很顯然,在此問題上戴加入了他的個人觀點,他并沒有客觀地闡述事實,而這正是在公正報道UFO時所要碰到的潛在問題。許多記者感覺到事情太過荒謬離奇,因而無法保證其會有所得,不值得去調查。更有甚者,大多數記者會偏離軌道,將事件轉而描繪成幽默故事,盡管每個事件的相關者都誠信十足,卻仍然肆意對他們冷嘲熱諷。
擔當責任
湯姆·伯奇在一篇題為《假冒的新聞》的文章里寫道:“UFO現象具備新聞價值,理應得到專業報紙的青睞。在UFO學科中,還有許多方面的東西是媒體并未認知的,這一事實本身也有力地證明了媒體從根源上就忽略了有關UFO的事件。比如,媒體沒有認識到在UFO問題上矛盾之處很多,比僅是回答外星人是否真的造訪過地球還要復雜得多。而倘若答案是肯定的話,那這個答案對我們所有的人都意義深遠。這并非UFO調查人員所問的唯一問題。”接著,伯奇寫道,“UFO持續的矛盾性也是富有新聞價值的。有關UFO的論戰有利于新聞報道,因為爭論雙方都是善辯誠實的科學、工業和學術界之人。在辯論中,各方都有觀點需要闡述,各方都有強項和弱項。UFO矛盾的雙方應該有個大眾論壇,給予相等的發言時間和機會。美國人民應當提供渠道,而公眾的確有權知道這一切。”
坦率地說,對媒體而言有關UFO報告的研究充滿了困難。為了提供公正而準確的故事,記者必須有具體可靠、經得起檢驗的證據。正如任何富有責任感的UFO研究人員會跟你說,要獲得堅實的物理證據是很難的。盡管幾十年來收集到了千千萬萬個目擊報告,但能夠解釋得通的證據則寥寥無幾,更多的像是奇聞異事。有時即便是有確鑿的證據,例如從墜毀的飛碟上獲取的神奇金屬部件,而且已經被送到著名的電臺談話節目主持人阿特·貝爾手上了,但仍然有許多無法解釋的問題令大多數記者對這種矛盾的題材敬而遠之。
也許這一天終將會到來:勇敢的報紙記者、編輯、國家電視臺的導演以及其他媒體人員團結起來,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對UFO進行研究,并提交一份真正意義上的、客觀的UFO調查報告。而在此之前,主流媒體用來轟炸大眾眼球的仍將是那些不痛不癢、插科打諢的有關從外星球上來的小綠人的故事。在適當的時候,小綠人總會碰上對它們感興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