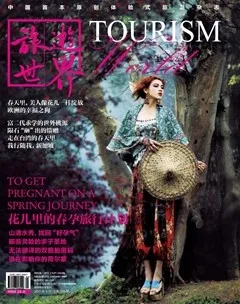交錯風景“798”
誕生于偶然,沒有規劃的“野蠻生長”
“798”原是上世紀5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在北京東郊酒仙橋、大山子一帶軍工電子企業的代號。作為工廠,這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時代產物。而作為藝術園區,其誕生則有些偶然,屬沒有規劃的“野蠻生長”。
90年代末,臨時搬到酒仙橋地區的中央美院承接巨型雕塑的創作任務,急需較大的創作空間,雕塑系主任隋建國便在此租用了大型廠房。而此時的798也正逢“轉方式,調結構”的關鍵時期,傳統工業面臨窘境,大量廠房閑置。2001年,隋建國以及日本“海歸”藝術家黃銳,拍北京胡同著稱的攝影家徐勇,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傳媒作家洪晃,穿行在音樂和文學之間的藝術家劉索拉,特立獨行的藝術家趙半狄,設計師林菁、蔣朋,藝術網站版主兼出版人“老美”羅伯特·伯納歐等藝術圈的人為圖房租低廉逐漸聚攏過來,開辦屬于自己的個性化工作室。在工人老大哥仍占廠區絕大多數的情形下,這個小小的藝術部落顯得新奇怪異,勢單力薄。
各種創意激烈碰撞,新與舊“盤根錯節”
而隨后數年間,這一切發生了根本改變。原本屬于藝術界“小圈子”的這些草根藝術家們,再也按耐不住寂寞,逐漸走出象牙塔,將他們的藝術成果就地與大眾分享。神秘的798逐漸熱鬧起來,人們用好奇的眼光來到這座特殊的廠區,看畫展,聽演唱會,參加文化沙龍……這里遂成為頗具規模的藝術創意園區,并成為打造“世界城市”的北京乃至中國和世界重要的藝術地標。2003年,798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全球最具文化地標性的22個城市藝術中心之一。
我有過10年紡織廠的生活經歷,學生時代也參加過“學工”,紡過紗,織過布,在大食堂里打飯,到大澡堂里泡澡,對工廠特有的一切并不陌生。而真正進入“798”,頓感震撼。在這里,藝術、創意與工業元素激烈碰撞,舊體制與新概念、老傳統與新時尚盤根錯節。后工業時代的廠房粗狂,破舊,笨拙,甚至有些粗陋,車間、煙囪、澡堂、水房、食堂、操場,以及那些變壓器、水暖管道、龍門吊、巨型齒輪、臺鉗、閥門等工業設備,尤其那些大紅油漆涂在水泥墻上的文革標語,勾起人們漸漸遠去卻也閃回的記憶。所有這些,似乎與藝術和創意不沾邊。
是藝術成就了“798”,還是“798”成就了當代藝術?
如果硬要探究原來的“798”與藝術的聯系,只有在那些一排排的鋸齒形廠房建筑里尋找答案。“798”最初由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前民主德國援建,因而具有典型的包豪斯建筑“血統”。所謂包豪斯,是據德語Bauhaus直譯,由bau(建造)和Haus(房屋)兩詞合成,源于1919年成立的德國包豪斯設計學院。該學院在20年代形成了現代建筑中的一個重要流派——現代主義建筑,即主張適應現代大工業化生產和生活需要,講求建筑功能、技術和經濟效益,創造簡潔、清新、明亮、樸實并富有動感的建筑形象。通俗說,就是建造平民化、實用性的房子。
是當代藝術成就了“798”,還是“798”成就了當代藝術?在藝術界至今莫衷一是。但廠區冰冷的紅磚與鋼筋混凝土建筑,及其銹漬斑斑的“鐵疙瘩”似的工業鑄件,表面看起來與藝術形成強烈反差,卻成就了富有叛逆性格,不修邊幅,個性十足的藝術家們理想王國,他們更愿在這樣的空間里尋找或建造屬于自己的藝術烏托邦。他們可以在這里玩俗的,無拘無束地一同聚餐、喝酒、罵娘,也可以秀高雅,聊藝術、探討人生,還可與廠里的工人哥們兒掰著胳膊摟著腰,胡打亂鬧,和諧相處。藝術家們也愿意在這樣輕松的環境氛圍之中快樂地創作。
在一般人的眼里,這里只是一個好玩的地方
隋建國的巨型雕塑《衣紋研究》、《大恐龍》等系列雕塑,岳敏君笑容燦爛的大頭系列人像繪畫,程昕東國際藝術空間里的《毛澤東與中國當代藝術家》主題展覽,王廣義的工農兵系列雕塑等都成為“798”的典型符號。而本土的長城空間、時態空間和百年印象畫廊,使藝術家們的作品脫離官方展覽展示體系,以民間會展方式向公眾自由彰顯個性十足的藝術成果。就連蜚聲世界藝術市場的東京藝術工程畫廊、比利時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紐約佩斯畫廊、德國空白空間、意大利常青畫廊及臺北帝門畫廊、香港美術館,都在這里安營扎寨,搭起了中國前衛藝術與世界藝術及收藏市場交流的橋梁。
而在一般人眼里,“798”就是一個與北京故宮、長城、天壇、胡同大不一樣的好玩的地方。耽于懷舊的中老年人,被曾經熟悉的環境與奇異的藝術氣息吸引過來,搜索、回味原屬于他們的過去,打量或品讀有些陌生和躁動的現實。而沒有過往經歷的80、90、00后們,則來這里輕松穿越時光隧道,獵奇、街拍、淘寶、品茶、飲酒、唱歌,將玩酷和樂購進行到底。菊香書屋、罐子書屋、伊力咖啡屋、鐵匠營以及露天擺攤的創意市集則成為年輕人的消費樂園。而那些被一輛輛大巴車運過來的“老外”們,通過這里的每一扇門,每一扇窗,以窺視光彩奪目的藝術背后這個古老而又嶄新的東方國度。 編輯 劉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