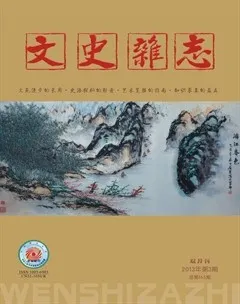曹操是歷史上最不講道德的人
編者按:
我國著名史學家、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今已91歲高齡的史式教授長期以來一直從事探討中華文化、重寫中華古史、批判皇帝制度、開展對臺交流的工作。最近三年來,海峽兩岸先后同步出版了他的三部歷史著作,尤其是第三部《皇權禍國》一書(有臺灣學者參與撰寫),大力批判荒唐的皇帝制度,特別引人注目,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曹操則是此書中著重批判的對象。本文較為詳細地闡述了作者的觀點,以期引起進一步討論。
為曹操翻案不合時宜
一千多年來,曹操一直是我國歷史上爭議最大的風云人物:一方面自唐宋以來,民間主要受說書與看戲的影響,長期把他看作一個白臉奸臣,罵聲不絕;另一方面,歷代又有一些好事者,為著不同的目的,采用不同的辦法,千方百計為曹操翻案。如果我們了解的歷史事實不多,聽了翻案者所說的翻案理由,似有幾分道理,即使不會貿然接受他們的看法,至少也會對曹操產生一定同情。對曹操的評價長期爭論不休,就是這么來的。就拿我這一生來說,七八十年中,遇到熱心為曹操翻案的人就有十來個,其中既有軍閥、政客、官員、學者、土匪、游民,也有文人、詩人、書迷、戲迷,什么樣的人都有。直到最近(2013年初)還有人公開揚言“立志”要為曹操翻案,一定要把“奸雄”曹操矯正為“英雄”。請閱《北京青年報》1月14日的文娛版,其中有一條消息:
本報訊(記者陸飛)由胡玫導演的電視劇《曹操》昨天在京舉行發布會,記者在其間獲悉,目前日、韓等國片商均欲高價購買該劇版權,其價格是最近兩年海外熱播中國劇的幾倍。
“奸雄”是人們對于曹操的慣性評價,但導演胡玫認為這種評價是不公正的,因而立志要將“奸雄”曹操矯正為“英雄”曹操。《曹操》的故事重心放在曹操青少年時期,講述一部由少年曹操、青年曹操到壯年曹操的心理和人格的成長故事。一個生于紛亂之世的輕率奸猾的游俠少年,最終磨煉成為一代銳意革新屢折不撓的政治家。為了更加接近史實,胡玫在開拍前曾找了一大批三國專家為劇本“挑刺”。眾多三國專家表示,此版《曹操》不但用細節重構了曹操14歲起勵志為國的故事,更通過一系列的歷史事件讓人們看到了一個勵志故事。
對于這一條消息,報紙的記者和編輯的處理是恰當的,不管在這次新聞發布會上,導演把自己這部片子說得多了不起,記者對此也只是作了有限與客觀的報道,許多溢美之詞都是導演說的,并非記者所說。編輯對于這條消息,也只是放在文娛版上,發了幾百字而已,并沒有任何“捧場”的做法。比較而言,卻是導演自己太不謙虛。她所說的一番話,只有一句是不錯的,那就是:曹操“是一個生于紛亂之世的輕率奸猾的游俠少年”,至于他最終能成為“一代銳意革新的政治家”,那只是她自己的說法,并非歷史事實。
對于曹操這樣一個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歷史人物,要想加以重新評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且那是史學家、歷史研究工作者的事,無須由一個導演來越俎代皰。要選什么樣的歷史人物青少年時期的成長經歷作為勵志教材,那是教育家、教育部官員的工作,也不是由一個電影導演能說了算的。而這位導演也太不客氣了,可以隨隨便便就找來“一大批三國專家”以助陣,這些人可否說幾個出來,讓大家聽聽看是否真的專家?須知為像曹操這樣的歷史人物翻案,不是兒戲,應該拿得出過硬的歷史事實來,說得出正當理由來。在目前舉國上下一致提倡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時候,倘要“立志”為不講道德、拋棄道德的奸雄翻案,未免有些不合時宜。難道沒有看到,邁入2013年以來,我們國家到處都是一片新氣象。那種讓帝王戲、宮廷戲充塞熒屏,讓又臭又長的電視連續劇想怎么說就怎么說的日子已成過去了么!
曹操成長的環境其實是重道德的
曹操,是一千多年來我國歷史上爭議最大的人物,有人對他大褒,有人對他大貶,總的說來,貶多于褒。褒之者主要著眼于他的“文治武功”,根據他的許多赫赫事功稱他為大政治家、大軍事家、曠代英雄;貶之者主要著眼于他的“道德品質”,根據他的許多違背人性的行為稱他為大野心家、大陰謀家、一代奸雄。有人為他的“英雄割據、文采風流”而無限傾倒,有人為他的陰險毒辣、虛偽狡詐而深惡痛絕。這樣各說各的,似乎都有根據,誰也說服不了誰。我們今天再來評論曹操的功罪,顯然不能重走那條雙方各執一端,各說各理展開馬拉松式討論的老路,而應該搬得出一個超乎一切小道理之上的大道理,得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曹操究竟是曠代英雄還是千古罪人?二者只能居其一,不可兼得。
歷史上的風云人物雖然林林總總,形形色色,但仍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栽樹者,另一類是“前人砍樹,后人遭殃”的砍樹者。有些人做事急功近利,只顧眼前,不顧后果,當時雖然把事情做成了,卻留下嚴重的后遺癥,后患無窮。從當時看,他似乎是栽樹者;從長遠看,他其實是個砍樹者。所以評價歷史人物,不能只看一時一事,而要超越時空,縱觀千年,橫觀萬里。不能只看小范圍內的“小歷史”,而是要看大范圍內的“大歷史”——宏觀的歷史。古人說“千秋功罪”,這個說法是不錯的,它包含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某些人物的功或罪可以影響到千百年后;另一層含義是某些人物的某些行為究竟是功是罪,一時難以判定,要等待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后才能看得準確,作出正確的結論。每一個人一生一世的所作所為,都要對別人產生影響。大人物的影響大,小人物的影響小,人死了,可是他產生的影響還在起作用。蓋棺就論定是不行的,常常是棺已蓋而論難定。如果草草做個結論,這個結論一定不可靠,早晚會被后人所推翻。
曹操名操,字孟德,沛國譙郡(今安徽亳州)人。操者,操守之意也。孟德,是指孟子所提倡的品德。曹操的名和字的含義都很不錯,有重視德行操守之意;只有小名阿瞞,足以暗示這是個很不老實的角色。有人說他是漢相國曹參之后,那是不可靠的。因為曹操本姓夏侯,其父曹嵩曾為宦官曹騰的養子,才冒姓曹,與歷史上的曹家全無關系。漢代選拔人才,一重門第,二重德行。曹操是宦官之后,門第自然不高,雖然頗有才氣,但很難得到選拔,只有通過自己奮斗、習武、從軍,才能向上攀升。因此,他對那時只重品行只談詩書不重實干不求實效的社會風氣極為反感,在言行中隨時表現出一種藐視道德、輕視詩書,急功近利、不畏人言的態度。在他小有成就之時,當時的名士許劭就評論過他:“君乃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耳!”他不但不以為忤,而且甚為得意。現在看來,他對那種只尚清談不務實際的風氣產生反感,自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后來矯枉過正,從反感標榜德行的社會風氣,發展到反對道德本身,直至仇視道德,那就不免大錯特錯。
東漢特別重視道德,民風淳樸,德高望重的長者一直受到社會的尊重,這是有根源的。東漢的開國之君劉秀是中國歷代帝王之中唯一出身于太學生的知識分子皇帝。他以儒家思想治國,三公之官,皆用宿儒,重道德,輕功利,寧肯發展得慢一點,也不用急功近利的野心家。他又崇尚節儉,愛惜民力,因此深受老百姓的愛戴。遇到災荒,發生動亂之時,老百姓恨的是貪宮酷吏,對朝廷還是十分尊重,還是“心存漢室”的。董卓之亂以后,雖然天下分崩,群雄并起,但是曹操還能“挾天子以令諸侯”;劉備雖然“東奔西走恨無家”,還能靠“帝室之胄”這塊招牌找到棲身之處,這都是因為大家對“帝室”還很尊崇,反映出這個社會重秩序,講道德,沒有亂套。如果一個社會亂了套,不守秩序,不重道德,則你雖挾天子也令不了諸侯,雖抬出“帝室之胄”的招牌也沒有人買你的賬,那就糟了。曹操自己走上了拋棄道德只求功利的邪路,通過他的“以身作則”,再大力提倡與宣傳,經過24年的時間,就把整個社會推上了拋棄道德、只求功利的危險可怕的邪路。
曹操的軍閥集團是靠陰謀起家的
曹操在成為一個軍閥之后,所重用的一是上戰場能夠拼命的猛將,二是擅搞陰謀詭計的謀臣。對于比較正直、有才干的知識分子例如孔融、楊修等人,早晚都會加上一個罪名加以鏟除。所以他那個曹氏集團迅速形成一個不講道德、不講政治理念,只爭現實利益的軍閥集團。
在政治上,他并不講求治國的真本領,通過良好的政績來贏得老百姓的擁護,而是采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手段縱橫捭闔、聯甲倒乙,消滅異己,擴充地盤。在軍事上,他并不是明恥教戰,認真培養出一批能夠衛國保民的子弟兵,而是盡量去收編一些剽悍善戰的現成隊伍,只圖他們能打勝仗,管他擾民不擾民。他所收編的隊伍,一是青州兵——即農民起義的黃巾軍中的精銳,二是烏桓兵——即東北游牧民族的驃悍騎兵。他就是靠這些職業兵幫他打下了江山。
曹氏集團是靠政治陰謀與軍事鎮壓兩手交替使用而發展起來的。比較而言,曹操對玩弄陰謀詭計更為內行。因此,他培訓出了一大批野心家兼陰謀家,包括自己的兒子曹丕和臣下司馬懿等人在內。
漢末天下大亂,群雄并起,長期紛爭下去,當然對老百姓不利。群雄之中若有一雄,能夠順應時勢,吊民伐罪,昭告天下,號召統一,那么老百姓一定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這當然是大好事。曹操當時身為漢相,已占天時,又有實力,如果自己沒有野心,無意奪取漢朝的江山,則以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號召力與軍事實力,恢復國家的統一并非難事,可以兵不血刃,傳檄而定。在赤壁鏖兵之前,曹操似乎就擁有這種優勢。他的兵力號稱八十萬,實有二十余萬,要想不戰而下江南,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為什么又吃了大敗仗?就是他自己的名聲太臭了。與其說他是政治家,倒不如說他是陰謀家。曹操用陰謀詭計,消滅異己,不斷擴充地盤;而且在戰勝之后,一再屠城。有了這種惡名在外,老百姓既恨他,又怕他,聽到他的兵來了,不是歡迎,而是逃避。他下江南的時候,老百姓紛紛逃跑,不愿意和他合作,卻愿意和反抗他的人合作。這就是他統一天下的計劃一再受到挫折的重要原因。他一開始就走上了以詐術取天下的邪路,處處培植曹家的勢力,打擊“漢室”的威信,使得天下皆知他“名為漢相,實為漢賊”。
為了急于求成,消滅異己,他甚至于公開提倡只求建功立業,不講倫理道德,造成整個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淪喪,秩序瓦解,人心渙散。從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開始,到匈奴騎兵打破東西兩京西晉覆亡為止,這一段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極為黑暗的時期。魏、晉兩朝,宮廷穢亂,骨肉相殘,官貪吏暴,民不聊生。西晉的八王之亂,同室操戈,混戰20年,幾乎耗盡了國力,終于召來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舉入侵,中原殘破,赤地千里。曹操的所作所為,直接導致了這一場滔天大禍,其間有極為清晰的脈絡可尋。舉例說吧,最先起兵南犯的匈奴五部騎兵,當年就是由曹操親自把他們安置在近畿(山西)而種下的禍根。
曹操怎樣教壞了自己的子孫
所謂“禍延子孫”,至少應該包括兩層含義,一層是指直接禍延自己的子孫;另一層是指禍延天下后世。一般人造福或者為禍,其影響只在包括自家子孫的小范圍之內,影響不了他人。凡能“禍延天下后世”者,必是個能量很大的風云人物。
歷史上有許多皇帝自己作惡多端,但總還想把子女培養成人。有些胡人皇帝不僅自己希望漢化,還希望子孫漢化,永遠留在中原過好日子,所以常常聘請漢人名師教育子女。曹操則不然,他在一心打天下的時候,不惜用自己的子女作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只要當時自己用得順手,完全不為子女的前途著想。他一共有多少女兒,史無明文,難以詳考,我們只知道他在公元213年秋,一次就把三個女兒送給漢獻帝做貴人,后來又逼漢獻帝立其中的曹節為皇后,自己當上了皇帝的老丈人。他謀殺皇子二人及其母伏皇后,曹節必然是參與了的。這樣把女兒當作禮物,一批一批地送人,而且讓她們參與陰謀,這不是坑害女兒又是什么!
曹操自己不講道德,只耍權術。和他比較接近的子女一定略有所知,想瞞也瞞不了。因此,他在這些子女面前也就難以裝得道貌岸然。試舉一例,即可看出他把太子曹丕培養成為一種什么樣的角色。有一次曹操領兵打破袁紹的根據地鄴城,曹丕也在軍中。 《后漢書·孔融列傳》說:“曹操攻屠鄴城,袁(袁紹)氏婦子,多見侵略(受到侵犯),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這個甄氏是袁紹的兒媳婦,是位出名的多才多藝的美人。曹氏父子久聞其名,早就對她垂涎。《世說新語》:“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即將(指曹丕)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指甄氏)。’”原來曹操父子兩人爭風吃醋,曹操對其子先下手為強的做法十分不滿。試看:軍無紀律,上梁不正下梁歪,父子兩人爭奪一個女人,這還有什么倫理道德可言?
曹丕初得甄氏,十分寵愛。他當皇帝后又立之為皇后,但不久即加虐殺。曹丕對人的殘忍、猜疑,不下于其父。曹操有子25人,除長子曹昂早死,能與曹丕爭位者,只有嫡出的曹彰、曹植二人。曹彰有戰功,曹植有文名,對曹丕都是很大的威脅。于是曹丕在棗蒂中下毒,毒死曹彰。從《三國演義》七步成詩一事來看,好像是曹丕寬宏大量,放過了曹植,事實并非如此。曹丕曾經多次陷害曹植,之所以沒有得逞,是其母卞太后舍命相爭。卞太后說:“汝既殺我任城(指任城王曹彰),不當復殺我東阿(指東阿侯曹植)!”曹丕怕事情鬧得太大,不好收拾,才不得不收手,但是此后曹植即被長期軟禁,失掉自由。曹操一死,曹丕立即全部接受曹操的姬妾,一個也不放過,被其母罵為“不如豬狗”。因為曹操傳授給子女的,都是權術、陰謀,而非友愛、團結;所以曹氏的兄弟姊妹之間照講權術,照耍陰謀,互相殘殺,毫不手軟。用不著等異姓來殘殺他們,他們的自相殘殺就一直沒有停息過。
東漢末年,曹氏父子欺壓漢獻帝,可以說是百般虐待,殺皇后、殺皇子,如宰牲口。曹魏末年,司馬氏父子欺壓小皇帝曹髦、曹奐,也是百般凌辱。公元 260年,20歲的曹髦不愿坐受廢辱,意率領殿中侍衛,仗劍升輦,要去討伐司馬昭,與昭的部下賈充相遇。賈充命人當眾刺死曹髦。司馬昭猖狂至此,他暗害許多曹氏子孫也就無須多說。公元220年,曹丕篡漢;265年,司馬炎篡魏,同樣都演出一場禪讓的鬧劇。前后相距45年,兩次鬧劇如出一轍。司馬懿是曹氏集團中的重要人物,是曹操一手培養出來的。他的陰險刻毒,善于偽裝,與曹操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司馬氏家族的陰險惡毒比曹氏家族更勝一籌。曹操自己培養了司馬一族來大殺曹氏子孫,這不是真正的禍延子孫又是什么?
曹操又是如何禍延天下后世的
曹操怎樣禍延天下后世?這又需要分為兩個方面來探討。一個方面是他對國家大局直接造成的負面影響。魏之篡漢,是他親手布置而由其子曹丕執行的。晉之篡魏,是他的嫡傳弟子司馬懿打下基礎而由其孫司馬炎執行的。魏、晉兩代統治集團實行的都是曹操倡導的“陰謀治國”術,直接造成了人心瓦解,國本動搖,招來北方游牧民族大舉入侵,國家覆亡。
另一方面是他公開號召壞人治國。從中華文明來說,自古都主張選賢舉能,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管理國家大事,一定要選有道德(賢者)有能力(能者)的人。好人不一定做得成好事;壞人肯定要做壞事。如果放手用壞人來管理國家大事,請問還會有好結果嗎?曹操在前后七年之間(從公元210年至217年)三下求賢令,即有名的“魏武三詔令”。在第三次求賢令中,他竟公開地說:“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這就是說,他敢于用不仁不孝的人來治國用兵。治國用兵是何等大事,就是很審慎地用人還難免會出一些問題,今竟公開承諾敢用不仁不孝之人,請問會把國治成什么樣子,把兵用成什么樣子?這種辦法,在理論上是矛盾的,站不住腳的;在實踐上是危險的,會出大毛病。在魏晉南北朝,整個中國北方一片糜爛,千百萬人頭落地,這就是曹操用不仁不孝之人治國用兵所付出的慘重代價。
曹操做人做事的方法也對后世起到很大的負面影響。由于他的名聲很大,一些后人跟樣學樣,每每理直氣壯地作惡多端。我們當然理解:不論曹操能量有多大,他所做的壞事究竟有限。可是由于一千多年來說書、演戲廣為傳布,大肆夸張,人間的許多壞事都便與曹操有了聯系。正所謂:“曹操!曹操!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陳壽的《三國志》是以魏為正統的。但是曹操的詭詐無良實在太出格了,陳壽也無法掩蓋,還是暴露出他的不少短處。至于日后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與毛宗崗修訂過的《三國演義》,對這位奸雄更是揭露得淋漓盡致。受到說書、演戲的長期影響,廣大民間對曹操的看法從來是深惡痛絕的。《東坡志林》中的一段話,可以作為民間看法的代表。這段話是:
王彭嘗云: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至于歷代官方,對曹操也不看好。《貞觀政要》中記載李世民對封德彝說:
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為人。
李世民自己就是個沽名釣譽的人,連他也都看不起曹操,恥與為伍,可見曹操是多么不得人心!
曹操襲殺呂伯奢的事是真是假
凡是讀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曹操狠心刺殺呂伯奢全家的故事。京劇中的《捉放曹》,就是根據這個故事編撰的。曹操殺呂伯奢一事,究竟是真是假?各種史料,說法不一。
陳壽《三國志·武帝紀》對此未有明載,只說:“董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私自逃跑)。”
為《三國志》作注的大史學家裴松之則在這一段話之后引用了三種史料以供讀者參考。
《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
《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各賓主孔。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凄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裴松之對這三條史料,未加任何評論。他只認真地提供給讀者,請讀者自己思考,自己判斷。但他在排列的次序上,多多少少做了一點暗示:那就是,排在前面的,官方色彩較濃的記載總會“為尊者諱”,掩蓋曹操的罪過;排在后面的,民間色彩較濃的記載就會透露出一些真相。所謂“正史”上的記載,往往如此。裴松之如此處理,是很有見識的。
曹操殺呂伯奢一事的有無,我們在一千多年之后再去查考,當然是困難的;但是從曹操故意制造許多冤案的史實看來,從他在求賢令中公開表示凡是“不仁不孝(不講品德)而有治國用兵之術(但有本領)者”,他都歡迎這樣的態度來看,他自己做出一些惡劣的缺德事,也就不足為奇了。
曹操是后世黑幫黑社會的老祖宗
曹操用自己的言行告訴后人,一個人要想成功,在處理問題的時候就要當機立斷,心狠手辣,寧肯我對不起天下人,也不讓天下人對不起我;寧肯錯殺一百,也不漏掉一個。被曹操冤殺的人確實太多了,有些突出的事例如夢中殺人,如對呂伯奢一家斬草除根,無不令人切齒。但是這些事不一定可靠,不一定是歷史事實。只有曹操殺周不疑一事,經過多種史料仔細核對,應是確有真事。現在暫選一種史料來作個簡要的介紹。《零陵先賢傳》云:
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曹操)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幼子倉舒(曹沖)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為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曹丕)諫以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能駕馭也。”乃遣刺客殺之。
另有《北堂書鈔》卷一百一十八載周不疑事云:
曹操攻柳城不下,圖畫形勢問計,周不疑進十計,攻城即下。
曹沖是曹操的小兒子,中國的阿基米德。是他利用浮力定律,發明了借船稱象的辦法。他幼年極為聰明,與周不疑不相上下,于是和周成為好友。
曹操殺周不疑的原因,不外以下幾條:
一是曹操想招他為婿,他有所畏懼,沒有接受,讓曹操失了面子,所以該死。
二是他與曹沖是好朋友,曹沖病死了,他也不能獨生,所以該死。
三是他是個了不起的人才,非曹丕等人所能駕馭;為了曹氏集團的安全,以殺之為宜。
曹操一再寫文章告訴后代的野心家,要想急功近利,早成大事,就要敢于用人,敢用亡命之徒。“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夫有行(有德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既要破格用之,又要從嚴控制,使其能為自己賣命。這種用人原則,非常接近現代的黑社會。而這樣網羅來的人才,能做出多少好事來?
曹操是歷史上最不講道德的人。他勸人們也別講道德。他說講道德,不過是“慕虛名”而已。這種說法,來自他所寫的一篇文章《讓縣自明本志令》。當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用朝廷的名義用兵,統一了北方。有人議論他,認為他會在羽毛豐滿之后,奪取漢朝天下。他寫此文進行表白,說自己絕無野心(這其實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他還自我吹噓說“設使國家無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就是說,如果少了我這個人,國家就會亂得一塌糊涂。(實際上有了他之后,國家還是年年打仗,一天也沒有太平過。)他說他本想辭職不干,以免被人誤會;但是轉念一想,自己如果交了權,特別是兵權,就很可能被人所害。自己被害,就會使“國家傾危”。自己不便辭職,不是自己戀棧,還是為了國家。因此,他絕不“慕虛名而處實禍”。說來說去,他是絕不交權。至于朝廷封給他的“食邑”一共有三萬戶,他愿交回兩萬,保留一萬戶,以此“自明本志”云云。其實曹操所說想要辭職是在裝腔作勢。歸根結底,大權是要抓的,實惠是要占的;至于名聲好不好,并不介意。
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是愛好和平,講究道德,重視誠信,對人寬容。曹操的所作所為正好與之唱對臺戲。要問曹操對后世產生的影響,說得具體一點,可以說曹操已經成為后世許多野心家的老祖宗。他的言行,成為后代野心家模仿的樣板;他的一些著作,成為后代野心家學習的經典。許多黑幫、黑社會的頭子每每通過《三國演義》虔誠學習這位奸雄的陰謀詭計,終生奉行。
對于這個違背中華民族精神,貽害天下后世的奸雄曹操,從古到今,從官方到民間,都是一片譴責之聲。雖有少數文人通過欣賞三曹的詩文,還會對曹操產生一些好感,但那是對文不對人,影響不了天下后世對他總的評價。
從古至今,從今而后,人類社會作為“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進行勞動的高等動物”所組成的群體而存在,總得建立秩序;為了維護秩序,總得有一種行為規范,也就是要講道德。雖然古往今來,道德標準因時代之不同會有一些變化,但是人類社會必須要講道德,不能拋棄道德,卻是一條死道理,硬道理,千古不易的大道理。如果拋棄道德,天下就會大亂,人類就會自我毀滅。敢于公開拋棄道德的人,總會被天下人所唾棄。誰想歌頌這種人,誰想為他翻案,就會使自己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想為曹操翻案實在是太困難了。只要曹操不講道德、拋棄道德的鐵案翻不了,他就永世不得翻身。在此文之末,筆者對這位“一世之雄而今安在”的曹孟德有詩嘆曰:
霸業狂圖轉頭空,民間千載笑奸雄。
貽禍后世成定局,翻案文章做不通!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成都)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