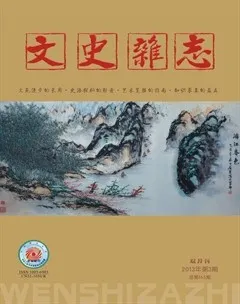糾正竹笛史研究中的一個訛傳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考古對“笛”這種樂器有許多發現:浙江河姆渡出土七千年前骨哨、骨笛;美國華僑報告收藏戰國時七個按音孔橫吹銅笛;湖北隨縣出土戰國初(公元前 433年)曾侯乙墓中的兩支橫吹竹笛;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公元前168年)出土兩支橫吹笛;廣西貴縣羅伯灣一號墓(漢初期)發現一支用二節竹制成的七個按音孔橫吹竹笛。許多音樂史研究者據此認為:“這些文物雖是鳳毛麟角,但都是中國竹笛鼻祖有力的見證,從而推翻了原史料中記載為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時把竹笛傳入中國的說法。”這樣的看法在關于竹笛史的著作、論文中比比皆是,例如,張勝芳先生的《中國竹笛發展沿革探源》、王力先生的《淺談中國竹笛技巧的南北融合》就是這樣闡述的。然而,仔細研讀古代典籍,卻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古籍中關于竹笛出自中國的記載不勝枚舉,但從來沒有過“張騫出使西域時把笛子傳入中國”的記載;既然本無此記載,那么“推翻”也就無從談起。實際上,關于“張騫出使西域時把竹笛傳入中國”的說法完全是訛傳,應該予以糾正。
一、竹笛出自中國的記載史不絕書
竹笛,民間稱笛子,是中國廣為流傳,最具特色的吹奏樂器之一。它用天然竹材制成,表現力非常豐富,既能演奏悠長、高亢的旋律,又能表現遼闊、寬廣的情調,也可以奏出歡快華麗的舞曲和婉轉華美的小調,還能表現大自然的各種聲音,比如模仿各種鳥叫等。
關于竹笛出自中國并且是中國古老樂器的記載,可以說是史不絕書。
竹笛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那時先輩們點燃篝火,圍繞捕獲的獵物邊進食邊歡騰歌舞,并且利用飛禽脛骨鉆孔吹之,也就誕生了中國最古老的樂器——骨笛。距今大約4000多年前,黃河流域至昆侖山一帶生長著大量竹子,先輩就開始選竹為材料制笛。戰國時期的《呂氏春秋·古樂》記載說:“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吹曰‘舍少’。”伶倫,據傳是黃帝時期的樂官,是發明律呂據以制樂的始祖。
竹笛在古代稱為“篴”。“篴”的本義是“竹”,竹笛因其廣泛使用和影響而取代了“篴”。《玉篇·竹部》說:“篴,同笛。”它由一根竹管做成,里面去節中空成內膛,外呈圓柱形,在管身上開有1個吹孔、1個膜孔、6個音孔、2個基音孔和2個助音孔。
同樣由竹管制成的簫也曾被稱為“篴”,但是更被稱為“豎篴”。宋元之際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樂考十一》說:“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竹膜焉。具黃鐘一均聲,或謂之尺八管,或謂之豎篴,或謂之中管。尺八,其長數也,后世宮縣用之;豎篴,其植如篴也;中管,盡長篴短篴之中也。今民間謂之簫管,非古之簫與管也。”簫和笛的主要區別在于竹笛橫吹有膜孔;簫豎吹且沒有膜孔,但有后音孔。現在也有短的豎笛,不貼膜,音色在笛簫之間,更接近笛子。
以竹為材料是笛制作的一大進步,一者竹比骨振動性好,發音清脆;二者竹便于加工。秦漢時已有七孔竹笛,并發明了兩頭笛,蔡邕、荀勖、梁武帝都曾制作十二律笛,即一笛一律。到了漢代,許慎《說文解字》有“笛,七孔,筒也,從竹,由聲”的記載。
東漢應劭《風俗通義·聲音》記載說:“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于雅正也。長一尺四寸,七孔。”這個特性,不僅使笛因為發音動人、婉回而具有強烈的民族特色;更因為古人謂它有“蕩滌之聲”,而使竹笛成為西周禮樂中用來“和天地”的一部分了。中國竹笛在日本至今還保留有“滌笛”之名。
1978年,從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戰國時期)出土了兩支竹篪。“篪”也是古代一種竹制管樂器,形狀像笛子。《洛陽伽藍記》就有“快馬健兒,不知老嫗吹篪”的記載。同年,從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墓(西漢時期)又出土了兩支竹笛,墓內的竹筒上還寫有“篪”的字樣。
1986年5月,在河南舞陽縣賈湖村東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發掘出16支豎吹骨笛(用鳥禽肢骨制成),根據測定距今已有8000余年歷史,豎吹,音孔由五孔至八孔不等,其中以七音孔笛居多,具有與現在大致相同的音階。骨笛音孔旁刻有等分符號,有些音孔旁還加打了小孔,試音發現與今天的音調完全一致。
上述資料,清楚地證明竹笛在漢代以前的古代中國就已大量存在,而它在漢代廣為流傳乃是不爭的事實:湖南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兩支竹笛,距今有2300多年的歷史;而張騫出使西域歸漢時為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距今2100多年。怎么能說竹笛是由張騫引進的呢?
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是唯一產生竹笛的國家。因為,盛產竹子的地域很多,竹笛的構造也不復雜,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不同地域的人們發明類似的包括樂器在內的生產、生活用品的事例很多。但是,中國古代就產生了竹笛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既然如此,“張騫出使西域時把竹笛傳入中國”的說法就是無本之木了。
二、張騫從西域傳回了“橫吹”
張騫出使西域這件事,在司馬遷的《史記·大宛列傳》、班固的《漢書·張騫傳》都有專章記載。應該說,這兩本分別寫于西漢武帝時期(與張騫同時代)和東漢明帝、章帝時期的史書,是最早撰寫張騫事跡的;同時,司馬遷和班固是非常嚴謹的史家,他們撰寫的“張騫傳”應該是可信的。但是,翻遍《史記》和《漢書》,卻找不到“張騫出使西域時把竹笛傳入中國”的記載。那么,這個說法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在晉代崔豹撰寫的《古今注》和唐人房玄齡、褚遂良等撰寫的《晉書》等文獻中,有關于張騫出使西域后傳入“橫吹”和西漢音樂家李延年據此創作改編“新聲二十八解”的記載。《晉書·樂志下》的記載是:
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后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
《古今注》的記載與《晉書·樂志下》大致相同。
以上兩段記載都涉及到“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的內容,而且都涉及到張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橫吹、胡樂”這四個字以及“傳其法于西京”這句話。
大概就是因為“橫吹、胡樂”這四個字,在竹笛的產生上就造成了誤解。有許多人因此而認為竹笛是由張騫從西域帶回的,這之中甚至包括明代著名的科學家、音樂家朱載堉,他就認為橫吹的笛子是張騫出使西域后傳入中原的。另外,日本的林木謙三在他那本很有影響的《東亞樂器考》一書中也堅持說:“中國笛子是從印度或西域傳入的。”
但是,前引資料明明記載張騫從西域帶回的是“橫吹”其法啊!
著名音樂史研究專家楊蔭瀏先生認為:“橫吹的笛,在鼓吹(橫吹)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是從公元前第2世紀末漢武帝的時候開始的。這可能和張騫由西域傳入吹笛的經驗和笛上的曲調有著關系。”楊蔭瀏先生客觀地指出橫吹笛在當時宮廷鼓吹中的地位以及笛與西域的關系。他認為西域傳來了“吹笛的經驗”和“曲調”,并非傳來笛樂器本身。楊蔭瀏先生的看法值得肯定,但是,他還沒有將“橫吹”說清楚。
三、“橫吹”不是竹笛而是軍樂隊
所謂“橫吹”,其實有三種含義:其一,樂器名,即橫笛,又名短簫。例如,唐王維《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軍司馬》詩:“橫吹雜繁笳,邊風卷塞沙。”宋王安石《和農具詩十五首·牧笛》:“芊綿杳靄間,落日一橫吹。”清陳維崧《菩薩蠻·江行》:“回首望臺城,依稀橫吹聲。”其二,樂府曲名,用于軍中。例如,《遼史·樂志》:“橫吹亦軍樂,與鼓吹分部而同用,皆屬鼓吹令。”其三,指演奏橫吹樂的樂隊。例如,《南史·垣護之傳》:“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乃啟求鼓吹橫吹。”
雖然“橫吹”確有指竹笛的含義,但在《晉書·樂志下》中卻并不是指竹笛這種樂器,因為這段史料的關鍵是“傳其法”,即“橫吹”的方法。該記載接著說的是“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很顯然,這里的“橫吹”應該指的是演奏橫吹樂的軍樂隊。
中國的竹笛,在漢代以前,多指豎吹笛,秦漢以后,“笛”才成為豎吹的簫和橫吹的笛的共同名稱,并延續了很長時間。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兩支竹笛,都屬橫吹類的笛樂器。在晉時已有豎笛,吹頭加一木頭,使氣從縫隙中通過,射向兩哨孔邊棱發音。北朝時,竹笛不僅極為普遍,而且有所發展,形制、長短、粗細變化較大。到了北周和隋代,開始有了“橫笛”之名。隋朝后期,出現了能演奏半音階的十孔笛。從唐代起,笛子還有大橫吹和小橫吹的區別。同時,豎吹的篪才被稱為簫,橫吹則稱之為笛。唐朝呂才,制“尺八”,豎吹,并傳入日本;在古都奈良的正倉院中,珍藏著中國盛唐時期制作的4支橫笛。其中有牙和石雕橫笛各一支,竹質的兩支,它們長短不同,但都開有7個橢圓形音孔。
西漢時出現了源于西域古樂的軍樂隊——“橫吹”。前引《晉書·樂志下》在“乘輿以為武樂”句后接著說:“后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 《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由此可知,李延年根據張騫從西域帶回的一支胡曲素材——《摩訶兜勒》,改編成了28首(段)樂曲,作為儀仗使用的軍樂,即“橫吹”。這些樂曲流傳甚久,直到數百年后的晉代尚能演奏其中的《黃鵠》《隴頭》《出關》《入關》等10首。這種將西域音調改編為新曲的創作實踐,也促進了民族音樂文化的交流。從這一角度講,張騫、李延年應該是我國歷史上根據外來音樂進行加工、改編、創作的最早者。
魏晉時期,橫吹樂不僅在北方盛行,在南方同樣盛行,而且除了騎馬的樂隊外,也有徒步的。河南鄧縣彩色畫像磚墓中東壁第二柱上就嵌有一方徒步橫吹者畫像磚,上有樂工四人,戴黑帽,著袴褶,縛袴。前二人吹角,長角上昂,口端系紅、綠二色的彩幡,隨風飄揚;后二人擊鼓,腰懸紅色板鼓,右手執桴敲擊。除了由角、鼓組成的橫吹樂外,這一時期又出現不用打擊樂器的橫吹樂,以角為主,增添了笛、簫、笳等吹奏樂器。到了隋代,在這種以吹奏樂器組成的樂隊中增加了篳篥和桃皮篳篥。《隋書·音樂志下》將其稱之為“小橫吹”,與有鼓的“大橫吹”一起列入皇室鹵簿中。于是橫吹這種軍樂隊也就成為宣揚威儀的工具了。
參考資料
1.張勝芳:《中國竹笛發展沿革探源》,《衡水學院學報》第7卷第4期,2005年12月。
2.王力:《淺談中國竹笛技巧的南北融合》,《魅力中國》2010年第32期。
3.[日本]林木謙三著,錢稻孫譯《東亞樂器考》,人民音樂出版社1962年版。
4.楊萌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人民音樂出版社2011年版。
5.袁靜芳編著《民族樂器》,人民音樂出版社2001年版。
6.李民雄:《民族器樂概論》,上海音樂出版社1997年版。
7.黎孟德:《中國藝術史》,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單位:四川音樂學院民樂系(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