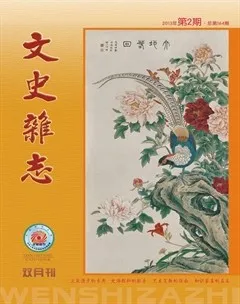晏殊為何不喜歡歐陽修
晏殊的身上閃耀著太多足以令歐陽修眼花繚亂的光環(huán)和艷羨不已的精彩。
晏殊早慧,7歲能文,曾被欽差大臣張知白目為“神童”。他14歲時,與全國千余考生一起參加了殿試, “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受到宋真宗的嘉賞,賜同進(jìn)士出身,授秘書省正字,成了少年進(jìn)士和年齡最小的領(lǐng)導(dǎo)干部。
他的詞家喻戶曉,如“昨夜西風(fēng)凋碧樹,獨(dú)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dú)徘徊”等等,都是讓人捧為圭臬的經(jīng)典名句,到處傳唱。
仕途上,他順風(fēng)順?biāo)簹v任太常寺丞、太子舍人、知制誥、翰林學(xué)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后來還被宋仁宗任命為集賢殿學(xué)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出任宰相,而且文武一肩挑。在士大夫和才子們眼里,晏殊的經(jīng)歷簡直就是一個傳奇。
歐陽修幸運(yùn),人生第一站就遇到了晏殊。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24歲的歐陽修參加了禮部舉行的考試,晏殊是主考官,出題《司空掌輿地之圖賦》。面對這過于僻澀的命題,眾考生不是偏題就是走題,唯歐陽修不光扣題精準(zhǔn),而且文采飛揚(yáng)。于是,晏殊慧眼識才俊,把歐陽修確定為“省元”,即第一名。從此,歐陽修對晏殊以門生自稱,執(zhí)弟子禮。
歐陽修中進(jìn)士后,出任西京(今河南洛陽市)留守推官。做官之余,他與錢惟演、尹洙、梅堯臣等文壇圣手們詩酒唱酬,佳作迭出,一時文名大振。當(dāng)時,晏殊的詞、梅堯臣的詩和歐陽修的文章,堪稱文壇三杰。
晏殊、歐陽修之間的緣分不可謂不深。作為有知遇之情的師生,作為一朝為官的同僚,作為共領(lǐng)時代風(fēng)騷的文壇世擘,他倆應(yīng)該是惺惺相惜而又相互提攜的,甚至可能產(chǎn)生許多文壇佳話,讓人津津樂道的。然而,這段師生情開始早,結(jié)束也早——雖然歐陽修對晏殊非常尊敬,但晏殊卻不喜歡歐陽修,甚至一度到了厭惡的境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遺憾。
據(jù)《東軒筆錄》載,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年),西夏犯邊,戰(zhàn)事吃緊。當(dāng)時,晏殊是樞密使,為軍機(jī)大臣。歐陽修擔(dān)心老師日理萬機(jī),過于辛苦,便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里,與詩人陸經(jīng)結(jié)伴去看望老師,希望帶給老師一絲安慰。誰知晏殊輕松得很,家里歡聲笑語,熱鬧非凡,毫無軍情緊迫之象,見他們來了,還在花園擺酒置茶,開懷暢飲起來。歐陽修深感意外,即席賦詩《晏太尉西園賀雪歌》,中有:“晚趨賓館賀太尉,坐覺滿路流歡聲。便開西園掃征步,正見玉樹花凋零。小軒卻坐對山石,拂拂酒面紅煙生。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余萬屯邊兵。”詩中飽含學(xué)生對老師的善意規(guī)勸,意思是國難當(dāng)頭,作為軍機(jī)大臣的晏殊,肩負(fù)重任,不應(yīng)該花天酒地,閑如散官。
晏殊讀后,差點(diǎn)兒沒背過氣去,憤然對人說:“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當(dāng)年韓愈擅長文章,赴裴度的聚會,也最多只說“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而他歐陽修在同樣情境下,卻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朋友尚且不開這種過火的玩笑,何況面對的是老師?果然,歐陽修善意的詩句,使晏殊背上了只顧享樂,不顧天下安危和社稷蒼生的惡名,成了他人生的污點(diǎn)。晏殊明確表示:“吾重修文章,不重他為人”。《邵氏聞見錄》也十分肯定地說:“晏公不喜歐陽公”。
對于晏殊的憤怒,歐陽修十分不解,頗感委屈和糾結(jié)。皇祐元年(1049年),歐陽修在潁州(治今安徽阜陽)知州任上給晏殊寫了一封信,說:“修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修以進(jìn)士而被選掄;及當(dāng)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跡不及于賓階,書問不通于執(zhí)事。豈非漂流之質(zhì)愈遠(yuǎn)而彌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信中雖有感激,但更多的是抱怨,抱怨老師對自己的冷遇,有一種追根究底的索問之意。然而,晏殊閱后,卻當(dāng)著賓客的面,敷衍幾句話,要文書代書作答。賓客說歐陽修也是當(dāng)今才子,文章名貫天下,如此回答,恐太草率。晏殊冷冷地說,對于一個科考門生,這幾句話已經(jīng)夠看得起他了。可見,晏殊的確不喜歡歐陽修。
然而,晏殊不喜歡歐陽修,難道僅僅是因?yàn)槟鞘滓?guī)勸詩嗎?這對于一個具有領(lǐng)頭雁風(fēng)范的文壇宿將和當(dāng)了多年宰相的人來說,未免小氣。從晏殊扶持后輩不遺余力的作風(fēng)來看,也不至于如此淺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qū)е玛淌鈱W陽修由喜到厭呢?
從性格上看,晏殊閑靜平和,崇尚道家,守成忌變,《宋史·晏殊列傳》說:“殊性剛簡,奉養(yǎng)清儉”,說明他是一個非常保守的人。他任相十余年,始終延續(xù)著呂蒙正、李沆、王旦等人的執(zhí)政風(fēng)格,尚寬簡,不苛細(xì),清凈無為,垂衣而治,遂有“太平宰相”之名。歐陽修卻耿介而切直,執(zhí)拗而剛烈,好論時弊,好爭長短,且以風(fēng)節(jié)自持。正如《宋史·歐陽修列傳》說:“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無論對象是誰,有批評就說,有意見就提,毫不忌諱。比如范仲淹因言被貶,高若訥作為司諫不僅不諫阻,反而推波助瀾;歐陽修便寫信痛罵高若訥“不復(fù)知人間有羞恥事”。晏殊任相期間,提拔歐陽修出任諫官。面對又一次有恩于自己的老師,歐陽修論事依然言辭激烈,常常讓晏殊下不了臺。這樣兩個性格迥異的人,要維持良好的師生關(guān)系是較難的。
從政見上說,尤其是在對 “慶歷新政”的態(tài)度上,兩人分歧嚴(yán)重。慶歷年間,北方的遼國和西北的夏國不斷侵略邊境,戰(zhàn)火不斷。在這兩個游牧民族的入侵過程中,宋朝始終處于劣勢,經(jīng)常吃敗仗。戰(zhàn)爭失敗除了帶來版圖縮小、貢輸增加、生靈涂炭的后果之外,也帶來對制度的拷問和反思,從而催生了北宋王朝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慶歷新政”。其核心內(nèi)容是改革吏制、壯大財力和增強(qiáng)武備,由參知政事范仲淹、樞密副使韓琦、富弼主導(dǎo)。時任翰林學(xué)士的歐陽修也緊隨其后,搖旗吶喊。
在改革不斷推進(jìn)的過程中,歐陽修也連連向宋仁宗上書,彈劾十余名反對改革的官員,愛憎分明,措辭激烈,朝野震驚。對于改革,作為宰相的晏殊雖然沒有高調(diào)反對,但卻是態(tài)度最為曖昧的高官之一。人家改革如火如荼,他卻仍然品酒填詞,舒舒服服地當(dāng)他的“太平宰相”。從“慶歷新政”的開始到失敗,幾乎看不到晏殊明確表態(tài)的歷史記載。而歐陽修追隨改革的態(tài)度和異常激進(jìn)的言論,自然會導(dǎo)致了他的反感。于是,晏殊干脆外放歐陽修為河北都轉(zhuǎn)運(yùn)使,眼不見為凈,但卻遭到諫官們的反對。他們上《乞留歐陽修札子》,說:“任修于河北而去朝廷,于修之才則失其所長,于朝廷之體則輕其所重”,強(qiáng)烈要求讓歐陽修留任。晏殊不為所動。諫官們也不干休,馬上聯(lián)名彈奏晏殊,致使晏殊罷相。他的罷相,起因是為了歐陽修,遂使他們之間的裂痕越來越深。
不過,盡管老師對自己成見日深,意見漸大,但歐陽修對自己的言行從來就沒有表露出一絲悔改,當(dāng)初怎么說,一生都怎么說。晏殊逝后,歐陽修為老師獻(xiàn)上了一首《挽辭》,一句“富貴優(yōu)游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表明了他對晏殊一輩子的態(tài)度。老師都入土為安了,他還直話直說,仍不肯掩飾自己過于苛刻的看法。晏殊當(dāng)初不喜歡他,看來的確不是誤傳。
作者單位:株洲縣政協(x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