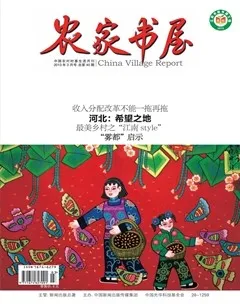心中的那片藍天
幾十度桃紅柳綠,一次次南北東西,吾這一生,的確到過不少地方,見過許多人。人們相見,一番噓寒問暖之后,若言語投機,便往往會問及“君是何方人士”,而且免不了伴著猜測、推度。眾人于吾,當然也不例外。但是,猜測吾是某某地之人的諸君,錯者十之八九。何也?蓋因吾之南腔北調使然。
吾出生在川南長江邊的一個小鎮上。小鎮地處川、滇、黔交界地區,從江邊往南走不多遠,便是無邊無際的大山。按說,吾乃一典型之南蠻,應一口南腔。然而,只要口一開,一陣東北味兒便順嘴流出來。為何鬢毛未衰鄉音已改?此中有一段淵源。
吾于“史無前例”的文革時期大學畢業。那時候的年輕人,胸涌一腔熱血,懷蕩無限激情,自然是一切交給黨安排。吾出身于貧寒的手藝人之家,算得根紅苗正;在校雖非拔尖人才,可也是個好學生。于是一紙命令,吾被分配到離家數千里之遙的反修前線——內蒙古。
在軍墾農場經歷了一番勞筋骨、餓體膚、苦心志的磨煉之后,“天”雖未降大任,但終于分配工作了,吾被分配到哲里木盟。早在書本上知道,那里是科爾沁草原,是孝莊皇后、嘎達梅林的故鄉,是一批作家詩人的搖籃。但是說實話,那時的通遼市,滿街土坯、泥頂房,一輛輛驢車在飛沙中穿行,即使在吾這樣一個山里孩子心中,也算不得一座像樣的城市。記得,當時聽到過一段描寫通遼的順口溜:一輛汽車跑兩頭,一個警察倆崗樓,一個公園兩個猴……可就是這樣一座城市,吾等這批“老九”也被禁止落腳。據說那時哲盟歸吉林省管轄,省里有指示,這批大學生不準分配到縣以上的地方和單位。于是,吾被分配到離城二十多公里的錢家店,當了一名鐵路養路工。
工區的師傅、大嫂、孩子們熱情地接待了吾等三個大學生。但是看得出,無論是大人還是孩子,眼神里都流露出幾分驚奇和疑惑。開始,吾以為他們只是出于對陌生人的好奇,后來才明白,其實不僅僅如此。鐵路是個小社會,工種門類繁多。各工種“優劣”如何?有一順口溜為證:指手畫腳車務段,擦脂抹粉列車段,煙熏火燎機務段,日曬雨淋工務段……在眾人眼里,養路工、裝卸工是鐵路上最苦、最累的工種。錢家店工區的師傅,大多來自農村,沒多少文化。幾個大學生來當養路工,眾人怎么會不疑惑呢!
時光在陰陰晴晴、風風雨雨中流逝,也漸漸磨去了吾等對這片土地的陌生,慢慢把吾等與這里的老老少少聯系起來。清晨,工友們推著軌道車上路了,腳下的鋼軌在遠方托出一輪朝陽。工地上,扒道岔、打道釘、墊路基……師傅們總是說:盡力就行了,別累著!一次吾打道釘,高高掄起的大錘沒打在道釘上,卻狠狠地砸在鋼軌上,迸起一簇火花。吾兩臂像被重重擊了一下,麻得半天抬不起來,兩眼直冒金星。一位師傅急忙過來,把吾扶到道邊坐下,一邊替吾揉著雙肩一邊說:“別著急,這活兒不是幾天的功夫!”吾啥也沒說,眼淚差點掉出來,不知是痛苦還是羞愧。干活時大家一條線拉開,師傅們總把我們三人安排在正中間,這是最安全的位置。師傅們手把手教我們干活,還教我們如何在野地里生火做飯……
收工回“家”,這位大嫂送來切好的酸菜,那位大嫂送來為我們洗好的被褥,漿得板板的,錘得平平的,疊得整整齊齊的。
節假日,或者自己買魚買雞改善生活,或者干脆到師傅家打秋風。吃完大嫂包的餃子,坐在炕上閑聊,從當年蘆葦叢生、野兔出沒的錢家店,到師傅們如何結婚成家。“我和你大哥結婚三天,還不知他長得啥模樣!天沒亮就走,深更半夜才回來。”大嫂的一席話,激得笑聲擠出屋子,飄到窗外。
孩子們改了口。年歲大的叫我們張哥、王哥,小的叫我們王叔、張叔。我們的屋子里少不了孩子們的身影,或是天南海北地講外頭的故事,或是解幾道疑難數學題。孩子們不只一次地說:“爹說了,你們是好人,只不過多念了幾年書,有啥罪過!”每當此時,我們無言以對。
冬天來了,這里的冬天是嚴酷的,對吾這樣的江南小子,更近乎一場災難。北風刀子似的刮在臉上,像要活生生扒下一層皮來;吹到手上,像在面團里揉進了蘇打,雙手漸漸“發”了起來。在工地上干活,頭戴狗皮帽子,腰上的草繩緊緊勒著厚厚的破棉襖。說得浪漫些,有些像小說中的保爾·柯察金;若講得刻薄點,真有幾分像勞改犯。一次工間休息,大家圍坐在火堆旁,師傅們談起要給我們介紹對象。吾笑笑曰:“連村姑也不愿嫁給我們這樣的人,還談什么對象!” 師傅們七嘴八舌地說:“別看不起自己!讀的書總有用著的一天。”“我看你們是好樣的,靠雙手也能養活自己,還愁沒媳婦兒!”“咱們不是文化多,而是文化太少了,你們還愁派不上用場?”……
凝視著一跳一閃的火焰,雙眼有些模糊。眼前沒有“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大草原,然而有飄著朵朵白云的一片藍天。這藍天從師傅們的胸中托出,高高地掛在我們的頭頂。
應了師傅們的話,讀的書總算派上了用場,后來吾被調到通遼鐵路中學當教員。不久,經同事介紹,有了女友。又一度冬去春來,愛情開花,小家庭組成了。說是成家,其實沒家,同為這個家像飄在水上的浮萍,沒有星點兒立根之地。吾在眾人的支持下,開始筑窩。吾與愛人的兩個弟弟,到野外推來一車車黃土,從荒灘上摟來一捆捆干草。沒有人招呼,鄰居的大人孩子都來幫忙,垛墻、上梁、蓋頂、搭炕,這個送來幾塊磚,那個送來兩根椽子。岳母告吾,幾十年的鄰居就像一家人,哪家有大事小情,大家都會伸手。待到過年,你準能嘗到十家八戶的過年萊。幾個月過去,一間“干打壘”小房,居然有模有樣地在岳父家的院子里,被我們像燕子似的,一口口銜泥壘了起來!房子蓋成的那天,看著一張張笑臉,吾情不自禁地感慨道:“這就是通遼人啦!”思緒流淌,吾心中又現出那一片藍藍的天……
青山擋不住,畢竟東流去。天空的陰霾終于消散,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神州迎來了春天,百業待興。吾等歡欣鼓舞,慶幸報國有日。在朋友們的鼓動下,吾產生了報考研究生的念頭。但細細一想,欲遠行千里的雙腳又重若萬斤。當初,岳父母一家,這個原籍山東、摻著滿族血統的家庭,接納了吾這個一貧如洗的異鄉游子,待吾如親人。吾未盡多少人子之責、兄長之職,卻要丟下兩個嗷嗷待哺的孩子獨自求學深造,那也太自私了。
不料,妻子知曉此事后,毅然表示愿獨自挑起家庭這副重擔,支持吾去念書。與吾有差不多經歷的妻子,深知這個機會對吾意味著什么。岳父母心里雖然不情愿吾離家遠行,但仍說:“青年人多念點書好。”在全家的支持下,吾做了一名胡子多頭發少的研究生。三載西窗秉燭,雖然不少牽腸掛肚,但更多的是激勵:吾必須盡力,起碼要對得起塞外苦撐苦熬的妻子。科爾沁那片藍天,讓吾總是看到希望。
研究生畢業,組織上留吾在北京工作,不久,妻兒也轉到北京。但是,無論走到哪里,不管做什么工作,吾總是喜歡唱內蒙古歌曲,留戀心中那片藍藍的天;說話總帶幾分通遼味兒,吾不否認自己也是通遼人,愿做藍藍的天上飄著的一朵白云。
時光像流水,磨去了河床里頑石的棱角,與流沙一起帶走了許多對往事的記憶。但是,在通遼的那些歲月,已溶入吾之血液。在通遼,吾目睹了國家命運的轉折;體味了嚴冬里人間真情的溫暖,從艱辛中走向春天;由孑然一身的游子成為人夫和兩個兒子的父親;無論暴雨滂沱還是狂風走石,心中總有一片藍天。
幾十年過去,如今通遼變了,坦坦蕩蕩的街道,櫛比鱗次的大樓,熙熙攘攘的人群,來來往往的車輛,綠樹成蔭,繁花似錦。吾也變了,昔日小伙子,今日白頭翁;昔日孑然一身,如今兒孫繞膝。永遠沒變的,是心中對通遼的那份情!
每當唱起“藍藍的天上白云飄……”吾就如癡如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