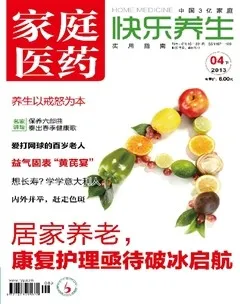與心對話
大概從而立之年開始,我交際的圈子漸漸固定下來。生子之后,交際的目的多半是為了工作,常常參與的圈子也大都和利益有關。細細品味起來,最純的友誼大概還是在學生時代。然而學生時代的好友們再見面時,有時也覺得無話可說。網絡的發達,隔斷了人情味,于是,我們越來越忙,忙到越來越孤獨。從骨髓深處發出來的孤獨,一直在講話,卻發不出“心聲”;一直在與人打交道,卻見不到“真心”。都市的荒漠中,我們如仙人掌孑然而立。
35歲那年,我在體檢的時候查出血壓偏高。高血壓向來是疾病中的“沉默殺手”——許多人對此并不警覺,也不因此節制自己,導致后來出現心臟疾病。為我診治的醫生是該領域的專家,在例行的醫學治療之外,他總是囑咐我要多一些“誠摯的對話”。他還向我推薦美國霍普金斯醫學院教授林奇的名著《我的哭聲無人聽見》。書中寫道:在位數驚人的早發型冠心病和過早死亡的案例里,人際交往失敗、愛的欠缺、社會支持的缺乏和寂寞問題,似乎都是身體出現問題的隱形因素。這位教授從大量醫學調查和統計數據出發,提出“對話是生命的靈藥,我們必須學習與心臟對話,與他人對話”。因為我家族中有不少親人死于心臟疾病,所以我不得不對此予以重視。
我撥出一些時間來去看已經疏遠的老朋友,我盡量創造一些比較安靜的場合,和他們聊聊心靈深處的話語。這一切對我來說難度非常大,因為我已經習慣了說“挺好的,我很好……”。我在自己的日程安排中特別排進了此類“心靈放松”的時間。比起從前看球賽或是打電游,走出去和朋友聊聊天實在是更有意義。
我和妻子報名參加了一個“夫妻溝通夏令營”,在專家的輔導下,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男人女人的不同,學習了解對方,并且更有效地進行溝通。之后,我們將一起看肥皂劇的時間變成了散步聊天的時間。我學會有事沒事就問她:“你感覺怎么樣?”當她絮絮叨叨講個沒完的時候,我不再像從前那樣厭煩,而是學習她豐富的表達詞匯。
另外,醫生讓我常常給心臟減負,雖然我沒有宗教信仰,也還是可以祈禱。當我覺得壓力很重的時候,我就試著把這些傾訴出來,向冥冥之中的蒼天之靈來訴說。卸下心靈的擔子,我的精力體力反而比從前更好了。
數學家畢達哥拉斯說,所有的一切都受到“和諧比例法則”的控制,都會以某種和諧的方式彼此相屬。我將這一點應用在處事上來:純粹的功利社交時間和單純的心靈溝通時間必須有和諧的比例;給職場的時間和給家人的時間也必須有和諧的比例;“帶上男子漢面具”的時間和“如小男孩般哭泣”的時間也必須有和諧的比例;社交圈子中合作伙伴和知心朋友也要有和諧的比例。
如今,我的血壓已經趨于正常。我發現這種和諧的生存方式帶給我的不僅是健康,還有人脈的廣厚,事業的成功。我不僅可以和“孤獨感”和平相處,而且還會將其升華為高尚的趣味。
“興逐時來,芳草地攜杖閑行,野鳥忘機時作伴;景與心會,落花下披襟兀坐,白云無語漫相留。”徜徉于山林泉石之間,不知不覺,我的凡塵之心就不見了。潛心在圖畫詩書之內,無聲無息,那種世俗之氣就消失了。“故君子雖不玩物喪志,亦常借境調心”,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