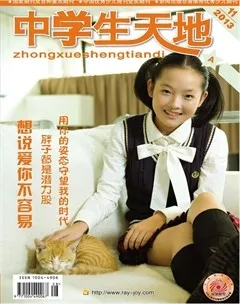用你的姿態守望我的時代
我的母親是位記者。
在她2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她做過一線記者、夜班編輯、部門主任以及期刊主編,無論崗位和職務怎樣變化,她的上班時間總是變幻莫測。而當她填寫履歷表的時候,在職業這一欄永遠都會寫上“記者”。
母親有過10年一線采訪的經歷,由此積累下了許多獨特的人生經歷——她在內蒙古和牧民一起策馬草原,在嵊泗海島和漁民一起出海追魚,也曾在中國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邊防哨卡用兩支鉛筆當筷子,和戍邊戰士一起吃拉條子……因為工作,母親結識了許多人,很多采訪對象都讓她深受感動,她說,這些普通人身上折射出的人性光輝比鉆石還要恒久。她曾跟我提過一位住在德清新市鎮的名叫陸松芳的83歲老人。這位靠送煤為生的老人生活清貧,他從58歲起就在德清租住一間面積5平方米的陋室,無論嚴寒酷暑,他堅持天天送煤,從不停歇。一車煤餅800多斤,老人一天要送兩三趟,每天能掙到30多元錢。汶川地震后,老人為災區捐出了1萬元——這些錢,他要送大約50萬斤煤餅才能掙到。社區干部勸他少捐點,可老人堅持到銀行排隊將萬元存折換成現金,送到工作人員手里。因常年勞累,老人的背已經佝僂了,兒子多次勸他回家享清+7SGyEakQ0xYqxFl+08URA==福,卻一再被他拒絕。在他租住的小屋里,電燈是唯一的電器,衣服和鞋大多是撿來的。熟悉老人的旁人告訴母親,他一天只花一元菜錢,存起來的錢都拿出來捐給需要的人。3個月前,母親去看望老人,臨走的時候想留下一些錢,也被老人拒絕了。看到母親堅持,老人很不好意思地說:“一定要給我什么的話,就給我點手套和毛巾,我送煤用得著。”母親說:“現實生活中有諸多令人不滿意的東西,可那位老人,就是一個精神標桿。生活千手萬手,他是觀音;道路千條萬條,他是羅馬。他讓我們找到了通往真善美的道路。”
看盡世間千景,嘗遍人生百味,母親將她的那些經歷一一寫成文字在報上發表。很多人對母親從事的記者職業神往不已,認為記者都是文藝而瀟灑的。但事實上每次她采訪歸來時,都是神情疲憊、面容憔悴,渾身臟兮兮的,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見到我和父親,總是弱弱地發出“嗯”的一聲算是問候,然后便一頭栽進臥室倒頭就睡。
因為有當記者的母親,我很早就知道記者這個職業遠沒有看上去那么光鮮奪目、浪漫瑰麗。在報社的大辦公室里,截稿時間就像是連接炸藥包的導火索,不可遏制地越來越短,所有的記者都要和它賽跑,敲擊鍵盤的聲音像雨點一樣打著耳膜。遇到突發事件,第一時間向最危險地方沖的往往是記者和警察。母親曾在抗洪一線的堤壩上和部隊官兵們共同奮戰了一個通宵,她說,那個時候更深刻地理解了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的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夠好,是因為你離得不夠近。”
可是,說這句話的卡帕正是因為站得太近,最后死在戰場上。記者總是在為他人的成功鼓掌喝彩,為他人的委屈秉筆直書,而他們自己永遠是默默的“隱形人”——有幾個記者可以名垂青史呢?相比而言,那些搗鼓資本抑或是笑傲政壇的人,他們一面揚名立萬一面得意洋洋地收集四方投射來的羨慕嫉妒恨,他們那樣生活似乎顯得更為“劃算”,他們也更像為人稱羨的“精英”。
“記者這一職業的意義和價值又在哪里呢?”我不禁問母親。
母親的回答是:“這個職業讓我看到了更豐富的世界,看到真善美最終能夠跨越時空獲得共鳴。只是它需要我們內心理想主義的支撐。”當時的我似懂非懂,遲疑地點頭。
恍恍惚惚地走過大半個青春期,我逐漸理解母親,并開始思考——關于名利紛擾糾結的去與留,關于人云亦云裹挾的得與失,以及幾年前的那個晚上母親所說的“理想主義”究竟是什么。我半是驚訝半是幸福地發現,母親對我的影響分分秒秒在滲透、日復一日在沉積。這不僅僅表現在我們用同一款新聞閱讀軟件,關注同樣的社會熱點話題,甚至走路的速度、仰頭的角度、調侃的腔調都如出一轍,更重要的是,母親已經成為我獨立思考的第一個效仿范本,體認生命意義的第一次參照。于是,在那個清新的夏日里,我認真地在大學第一志愿的空格里填上了“新聞傳播學”。
我知道,是那樣的母親成就了現在的我。每一代母女都因為不同成長背景而產生各種差異,譬如她迷戀梁朝偉、我喜歡林俊杰,她用手機打電話發短信、我用手機“切水果”“發微博”,她看我成日上躥下跳感嘆女兒不夠端莊、我見她每天行止沉穩只覺她太過呆板。但是每對母女也有著從血液里傳承下來的共同點,我想我和母親共同擁有的就是一份理想主義的激情,一種投身火熱生活的渴望,這些情緒與思想像是連接我與母親的紐帶,也像是兩代間的一種傳承。我們用不同的方式行走,卻總會為相似的風景駐足,我們身處不同時代,卻選擇了相同的姿態:追求真,守望善,相信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