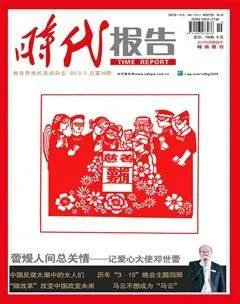反思與展望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消費品市場已經實現了從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到供大于求的買方市場的歷史性跨越,經濟模式也從原來的計劃經濟逐漸過渡為市場經濟,這一歷史性跨越標志著中國人民已經告別了短缺時代,標志著中國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然而,伴隨著物質文明的不斷進步,道德滑坡現象開始出現,假冒偽劣商品層出不窮,消費維權,逐漸成為中國消費者最不愿意面對而又常常不得不面對的事情。
從最初的被動維權到后來的主動維權,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消費者維權走過了30個年頭。但時至今日,維權的高成本,司法救濟、社會救濟的缺位及深層次的中國經濟環境因素影響,致使中國消費者的維權之路依然步履維艱。
維權意識在消費損害中萌生
20世紀80年代初期,改革開放如同魔杖一般激發了華夏大地的經濟活力,渴望物質文化生活豐富多彩的國人,掀起了一個又一個的消費熱潮:電風扇、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機、時裝……生活日漸富裕的人們綻開了笑臉。
江河奔流難免泥沙俱下。與此同時,一些見利忘義、不擇手段聚斂財富的不法之徒混進市場,利用消費者的購買欲,將黑手伸進了人們的腰包。剛剛開始過上舒心日子的人們又開始被另一種陰影攪得心神不寧——幾乎無處不在的假貨。
注水肉、化糞池腌大頭菜、罌粟殼火鍋、福爾馬林泡毛肚、假酒中毒、壓力鍋爆炸、售貨缺斤少兩……一樁樁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事件不斷發生。假風假雨讓剛剛過上好日子的中國消費者憂慮和傷心,如不認真解決這些問題,不僅會影響社會的安定和政府的形象,改革的聲譽也會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保護消費者權益為宗旨的消費者協會組織應運而生。1984年12月,中國消費者協會作為全國性消費者組織經國務院批準正式成立,它的成立標志著在全國范圍內有組織的保護消費者運動正式拉開了帷幕。中消協與國際消費者組織開始頻頻交流,并最終將“3·15”引入到中國內地。
1993年10月,備受消費者關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出臺,并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全票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施行,使消費者維權有了堅強的法律保障。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施行,掀起了中國消費者維權活動的一個小高潮。這一時期,以王海為代表的買假索賠式維權大行其道,將王海符號化的同時,也引發了對“知假買假”“買假索賠”謀利的爭議。
而伴隨著中國市場化、城市化的進程,政府對市場秩序的焦慮開始走向另一面:以1999年王海因知假買假索賠先后在南京、北京等地敗訴為標志,消費者“維權獲利”的模式基本遭到了否定——雖然也有勝訴的案例。以“道德”為題,輿論上開始因“王海模式”而生產兩極分化,中國消費者維權的第一個高潮也就此戛然而止。
事實上,“王海模式”的被否定,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在1990年代中后期,隨著分稅制和GDP主義的登場,特別是GDP納入政績考核體系,企業和政府之間有了利益上的共同語言。在這種經濟形勢下,消費者的維權活動和維權效率必然大打折扣。
但無論怎樣,消費者依法維權的時代已經來臨了。其后,從手機、電腦的“三包”規定到汽車“三包”規定,從《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的討論到《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出臺,從商品房是否屬于商品的討論到最高人民法院出臺司法解釋確立商品房同樣適用加倍賠償原則等,直至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正式公布實施,第一次明確規定了精神賠償的范圍、標準及可訴訟主體,消費者維權的法律保障越來越走向豐滿。
博弈的轉向:維權目標集中在知名企業
進入新世紀之后,中國消費者的維權形勢又發生了變化。在這一時期,消費者針對中小企業的維權逐漸不再引人關注,一些品牌知名大企業開始成為消費者維權的主要對象。
而這一轉向,還是從身在第一線、嗅覺最靈敏的職業打假人開始的。
打假名人王海曾說過,由于司法機關對“知假買假”行為所持的觀點不一,使打假人打官司索賠的不確定性加大,維權成本提高,他們開始轉向,從以前的打擊假冒偽劣商品,逐漸轉變為主攻知名企業的虛假宣傳等問題。
這種轉向當然還是有著深刻的經濟原因。畢竟,消費者維權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經濟活動,是消費者和生產者(企業)之間的反復博弈。無論對職業打假人還是對普通消費者來說,如果預期的收益等于或低于成本,這種賠本的維權只能迫使消費者放棄。
按照經濟學上的博弈論,如果說消費者和中小企業之間的博弈,更大程度上是零和博弈(一方輸,另一方贏;一方輸多少,另一方就贏多少,二者之和為零)的話,那么消費者和知名企業之間的博弈則是非零和博弈,其中的含義是:對局各方不再是完全對立的,一個局中人的所得并不一定意味著其他局中人要遭受同樣數量的損失。也就是說,博弈參與者之間不存在“你之得即我之失”這樣一種簡單的對應關系。其中隱含的一個意思是,參與者之間可能存在某種共同的利益,蘊含博弈參與才“雙贏”或者“多贏”這一博弈論中非常重要的理念。
這一時期,中國消費者的維權活動迎來另一個小高潮。為了避免丑聞,大多數知名企業愿意與打假人(維權者)私下和解。
當然,這種局面基本上限于2006年之前。之所以如此,深層次的原因在于,這一時期正處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抓大放小”的敏感期,“放小”勢必把被認為效率不高、成為包袱的中小國有企業逐出體制;“抓大”則成全了央企、壟斷國企的霸主地位。實際上,這一迅速推進的“改制”運動對民營企業也有同樣的壓力,如果不能在此期間做大做強而實現華麗轉身,必然就不得不承擔起中國經濟轉型的壓力,在生存線上掙扎。
因此,在這一時期,有見識、能力的企業都在拼命發展,“更大更強”的理念壓倒一切,消費者維權變得相對容易。
政府折中“懲罰性賠償” 企業強勢“反彈”
到2005年左右,中國新的經濟結構已經成型。一“元”是巨無霸式的央企和國企,它們擁有龐大的市場和體制資源,能夠攫取巨大的“市場收益”;另一“元”則是占企業總數99%的民企,它們一方面承擔繁重的稅負,另一方面在資金和政策優惠上被邊緣化,處在產業鏈的低端,更多的是一種“血汗經濟”。
當然,已華麗轉身的大型民營企業不在此列。
這種局面下,一起標志性的維權案件——2006年的“華碩電腦黃靜維權案”,宣告中國消費者維權進入到新的歷史階段。
黃靜案在公眾當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一方面包括專家學者對“懲罰性賠償”莫衷一是,吵得不亦樂乎,最終國家出臺了一個各方均能接受的結果——2009年,《食品安全法》中引入10倍賠償 ;另一方面,企業找到了對壘消費者維權的法寶——或者揮動“敲詐勒索”的大棒恫嚇,或者“建議通過法律途徑解決”。
有誰能想到,黃靜當初之所以提出高額懲罰性賠償,只是因為“覺得訴訟可能會得不償失”呢?
自此,中國消費者的維權環境又趨惡化。職業打假人和普通消費者在維權道路上也徹底分道揚鑣——聰明如王海等,參與到更高層次的維權活動“商業競爭”中去,愚鈍如劉江等,鋃鐺入獄;一干“屁民”的維權活動則在夾縫中進行。
新氣象:網絡維權同盟與中國消費者運動
進入新世紀的第10個年頭,伴隨著微博的興起,消費者維權事業似乎綻出一絲新氣象。
2012年1月28日,三亞宰客事件的爆發使公眾意識到了微博的力量。同年2月1日,由鄧飛等媒體人發起成立的“游客反殺豬聯盟”新浪微博認證成功,成為曝光網友“挨宰”經歷、協助網友維權的互助平臺。除了微博,這個聯盟還專門建立了網頁。在該聯盟接收的眾多投訴中,已有不少成功解決的例子。
微博維權聯盟的建立,預示著新時期社會力量在消費者維權方面的逐漸崛起。誠如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陳光金所說,“這是市場與社會關系調整的一個信號”,消費者對市場的監督比一般行政監督手段更有利于推動市場自身的規范化,社會監督比行政監督對市場的挑戰更大。
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正在創造出一個規模龐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據布魯金斯學會經濟學家哈拉斯分析,占總人口18.2%的2.47億中國人擁有被稱為中產階級的條件,也就是平均每天的家庭支出在10美元到100美元之間。如此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意味著巨大的消費市場,這是任何一個跨國公司都渴望進入的市場。
不過,中國的中等收入人群不僅有自己的市場需求,還有自己的消費價值觀,如果他們能夠自由表達,他們的喜歡會造就巨大的商機,而他們的厭惡則會成為某些公司的災難。隨著中國消費群體的實力增長,他們對自身權利的意識正在不可抑制地覺醒,正在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然而,中國市場上很多商品和服務的供應商似乎并未意識到這一點,仍在粗暴地榨取市場利潤,而忽視提供安全可靠的產品和服務。面對這種情況,消費者開始用腳投票,企業多行不義的結果就是被市場拋棄。在出現多起“毒奶事件”之后,蒙牛產品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形象已一落千丈。有人認為,蒙牛毒奶事件在中國消費者維權行動中具有標志性的意義,因為它很可能代表一個新的時代——中國的消費者運動時代正在來臨。
消費者運動發端于發達國家,它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者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自發或者有組織地以爭取社會公正、保護自己合法利益、改善其生活地位等為目的,同損害消費者利益行為進行斗爭的一種社會運動。消費者運動始于19世紀的英國,然后迅速波及西歐和北美。20世紀則是消費者運動蓬勃發展的世紀,美國在20世紀50、60年代,日本在70年代,消費者運動迅速發展成為改變市場、社會和政府的社會運動。1960年,國際消費者組織聯盟(IOCU)成立,1985年,第39屆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了《保護消費者準則》。
消費者運動一般要經歷啟蒙(自發)階段、有組織階段、行政和法律(政府依法)保護這三個階段。雖然中國在1984年底就成立了中國消費者協會,但在學者看來,中國的消費者運動此前處在啟蒙時期,一直未進入有組織階段。但從現在起,中國的消費者運動將進入自發組織階段,正在走向成熟。由于消費者運動直接關系到民生消費,因而最容易在中國社會產生共鳴。
因此,中國出現消費者運動的時機或已成熟,中國消費者將圍繞食品安全、藥品安全等領域的事件性問題,形成廣泛的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社會運動,它會誕生出一些民間組織,會引發出一些有代表性的訴訟事件,形成持續性較強的輿論氛圍,推動政府和立法機構出臺相關政策以及立法。
中國的消費者已經覺醒,“小政府,大社會”,或許這是未來中國消費者維權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