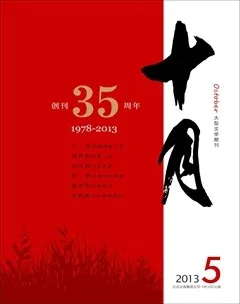木黃,木黃,木色蒼黃
一
站在那棵遺世獨立的大柏樹下,我抬起頭往上看:兩根碩大的樹干并駕齊驅,直直地插向空中,到達十幾米處,它們像突然意識到了什么,彼此親熱地向對方靠上來,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如同兩個失散已久的兄弟。再往上看,是茂密的蓬蓬勃勃的枝葉,根本分不清樹枝和樹葉是從哪根枝干上長出來的,一群群鳥兒在枝葉間飛進飛出,發出嘰嘰喳喳歡快的叫聲。在墨綠的樹冠上面,天空高邈,湛藍,一望無際,飄浮著一朵朵輕盈而素凈的白云,仿若盛開在天空的一簇簇白玉蘭。接下來,往云朵里看,我便看見了那支不倦的在天上行走的隊伍,他們衣著破爛,腳蹬草鞋,身影若隱若現,幾乎聽得見他們甩動手臂的聲音,槍托叮叮當當地敲擊水壺的聲音,彈袋里可數的幾顆子彈在嘩啦嘩啦晃動中被磨得金光閃閃的聲音。
眼睛一陣灼燙,我知道我在流淚。那是我總也止不住的淚。
到1975年9月13日的此時此刻,我已經走了很長的一段路,我從江漢平原、四川盆地往云貴高原走。不是一個人,而是三個人。我們從夏天啟程,沿著紅軍長征的道路順走一段,逆走一程。先去了湖北洪湖,然后翻過二郎山,從雅安進入阿壩;再從青草長得比人還高的大草地踅轉身子,順岷江而下,跨過大渡河、金沙江和烏江,沿階梯般步步登高的山脈進入云遮霧罩的烏蒙山。走到貴州的時候,已是秋風浩蕩。眼看就要萬木霜天了,進了貴州省城貴陽,幾個人累得東倒西歪,人困馬乏,都想躺下來美美地睡一覺。
我是三人中唯一的女性,當然更累,兩條腿沉得像深陷在沼澤里。可我不想停下來,還想繼續走,往黔東的印江、沿河和四川的酉陽走。我對我的兩個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同事萬鋼和何春芳說,你們在貴陽歇幾天吧,剩下的幾個地方我一個人去。我沒有說出的另一句話是,黔東那片偏僻而蠻荒的土地,于公于私,都是我不敢遺忘的地方。我發誓此生必須親自去尋訪,就像有什么東西丟在了那里。
離開同事,我直奔省府找李葆華。他是革命先驅李大釗的兒子,在貴州當省委書記,說起來,我們是心照不宣的老熟人和老朋友了,到了貴州沒有理由不見他,何況我還有事要求他。但那一年,跟著小平同志出來“促生產”的這批老干部,被那批熱衷于“抓革命”的人揪住不放,日子很不好過。聽說北京來人要見他,正在開會的李葆華一臉疑惑地走出來。我像在黑暗中找到了黨,開門見山,提出請他從省博物館派個同志陪我去黔東。他說這事他還能辦到。當時正是午餐時間,會開得差不多了,他回去簡單做了交代,然后對我說:“捷生,你來得真不是時候,我沒法招待你,跟我去吃食堂吧。”
省博物館派來陪我的譚用忠同志,是個黨史專家,學問很深,對黔東革命史了如指掌。他建議我先去印江,因為印江的木黃非去不可,那地方太重要了。這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我說我最想去的就是木黃。
那時我雖然還年輕,但也經不起折騰,當我們沿著驚濤拍岸的烏江舟車勞頓地走到木黃這棵千年古柏下時,我已是臉色枯黃,頭發蓬亂,身上的衣服皺皺巴巴的。從附近挑著擔子走過的土家族人和苗人,都用驚奇的目光望著我,不知道一個外鄉人為什么會對著一棵樹流淚。
肯定是李葆華的特別叮囑,印江派出一個副縣長接待并陪同我尋訪,不過那時叫“草委會副主任”。副縣長和我一樣,也是個女同志,叫張朝仙,是很樸素也很潑辣的一個人。許多年后,她以縣政協文史委員的名義在縣里局域網上撰文回憶,她在印江縣招待所第一眼看見我,都不敢相信我是賀龍的女兒,“像一個女知青。”她說。
二
木黃是因為那棵千年古柏而聞名,還是那棵千年古柏因為見證過那段轟轟烈烈的歷史而聞名,沒有人能說得出來。反正當我尋遍那幾條簡陋的街道,最后站在那棵古柏下時,我發現木黃唯一能作為那段歷史和我面對面的,也就剩下這棵樹了。
這讓我無語而泣,悲從中來。
當著漫山遍野又要飄落的落葉,我們怎么能忘記木黃呢?
黨史和軍史都應該記載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六軍團木黃會師,迄今都過去41年了,新中國也建立26年了。我想,我們可以不知道歷史的每個細節,但應該知道在紅軍的三大主力中,有一個紅二方面軍。而紅二方面軍的源頭,就是1934年10月,從湘西發展壯大的紅二軍團與從湘贛邊界跋涉而來的紅六軍團,在貴州印江的這個叫木黃的小鎮上勝利會合。兩支勁旅從此合二為一,生死與共,開始了讓世人稱奇的全新征程。
紅二、六軍團的會師地點,就在木黃的這棵大柏樹下。
許多紅二方面軍的老同志回憶,41年前,就是在這樣一個木色蒼黃的秋日,父親賀龍親自帶著紅三軍主力,站在木黃的這棵樹下焦急地等待任弼時、蕭克和王震,等待他們帶領的那支遠道而來的篳路藍縷的隊伍。
這是1934年10月24日,層林盡染,彎彎曲曲的山路上白霜鋪地,在黔東逶迤起伏的山嶺里吹蕩的風,已經像藏著刀片那般凌厲了。
9天前的10月15日,父親在酉陽南腰界獲悉由任弼時、蕭克和王震帶領的紅六軍團號稱“湘西遠殖隊”,從江西永新出發,試圖深入湘西,與我父親的隊伍會合。經過一路惡戰,此時已進入黔東印江和沿河一帶尋找我父親率領的紅三軍,這讓我父親喜出望外,因為到這時,他在湘西拉起的這支隊伍已經有整整兩年與中央紅軍失去了聯系。在這兩年里,由于“圍剿”的敵軍蜂擁而至,夏曦又在紅軍內部大搞“肅反”運動,把許多忠心耿耿的指揮員和地方干部殘忍地殺害了,鬧得人心惶惶,軍心渙散,把父親在湘鄂西好不容易建立的根據地給弄丟了。父親慘淡經營,站出來收拾殘局,他把我懷孕在身的母親丟在湘西的山野中苦苦掙扎,自己帶著由紅四軍改為紅三軍的部隊退到黔東的印江、沿河和酉陽等地,建立新的根據地。黔東一帶雖屬貴州軍閥王家烈和川軍的地盤,但因地處湘黔川三省邊界,山高林密,河流縱橫,敵人鞭長莫及;還有一個原因,是當地的民眾也和湘西一樣,多為土家族和苗族,與父親這支在湘西土家族和苗族地區拉起的隊伍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因而逐漸被當地號稱“神兵”的民族武裝接納,使這支傷痕累累的部隊勉強站穩了腳跟。
那天,部隊報告說抓到了一個探子,但幾番審問,最終弄清是個普通郵差。父親說,既然是個郵差,就把他放了吧,把信件和匯款單還給他,讓他繼續去送信,但必須把報紙留下來。如果沒有路費,再發給他路費。就是從郵差留下的那摞報紙里,父親看到了任弼時、蕭克和王震率領的紅六軍團經湘南向黔東“流竄”的消息。
紅六軍團同樣是一支苦旅。1933年10月,蔣介石調動幾十萬精銳部隊步步為營,對江西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因王明推行的“左”傾路線占據上風,中央紅軍屢戰失利。為實行戰略轉移,中央命令在湘贛邊界作戰的紅六軍團開始西征,挺進湘西與賀龍領導的紅三軍會合,策應中央紅軍突圍。這支由任弼時任軍政委員會主席、蕭克任軍團長、王震任政委的部隊,1934年9月從湘黔邊界進入貴州,立刻遭到王家烈聯合三方會剿。部隊原想沖破敵人的防線,西渡烏江,進軍黔北,中央軍委卻命令他們奔向江口。10月7日拂曉,第六軍團在輾轉中到達石阡甘溪,準備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色越過石阡、鎮遠進入江口。誰知敵人在甘溪設下埋伏,一場讓紅六軍團在須臾之間損失3000指戰員的慘烈戰斗在此打響,軍團十八師師部及五十二團指戰員大部壯烈犧牲,團長田海青陣亡,師長龍云被俘后遭殺害。軍團參謀長李達引領前衛四十九團、五十一團各一部突圍后,意外得知賀龍的部隊在印江、沿河一帶活動,毅然率部奔赴沿河地區。
在獲悉紅六軍團主力行蹤的同一天,前方傳來消息,李達在突圍中帶出來的部隊與紅三軍七師十六團在沿河水田壩會合。父親興奮不已,在第二天,也就是10月16日,率領紅三軍主力從酉陽進入松桃,在梵凈山區縱橫交錯的峽谷里尋找中央紅軍。
在山里整整轉了7天,22日,當紅三軍主力到達印江苗王坡時,紅六軍團主力已先他們一步經苗王坡向纏溪進發。看見紅六軍團踩過的青草還沒有直起腰來,父親一揮馬鞭說,快!抄近路追趕,不能讓中央紅軍再吃苦受累了。
22日深夜,隨紅六軍參謀長李達突圍、先期與紅三軍會合的郭鵬團長,率偵察連穿插到印江苗王坡,忽然聽到后面發來一陣“嘀嘀嗒嗒”的軍號聲。仔細一聽,是他極為熟悉的紅六軍團四十九團的號譜!郭團長欣喜若狂,命令司號員吹應答號。霎時一問一答的軍號聲此起彼伏,就像兩股泉水在空中歡快地碰撞和交纏。號音未落,兩隊人馬已在溪谷的一塊坪地上淚光閃爍地抱成一團。
23日,紅六軍團從印江纏溪出發,經大坳、楓香坪、官寨、慕龍,宿于印江落坳一帶。紅三軍從印江苗王坡出發,經龍門坳、團龍、坪所,宿于芙蓉壩、鍋廠、金廠。從地圖上我們就能看清楚,兩支部隊其實是向一個中心靠攏,這個中心就是木黃。
24日中午,按照事先約定,任弼時、蕭克、王震率紅六軍團主力經落坳、三甲抵達木黃。父親賀龍、關向應和先期到達的紅六軍團參謀長李達帶領紅三軍,提前在木黃的大柏樹下列隊迎接。
雖是滿身戰塵,衣衫破舊,還拖著300多名傷病員,但在槍林彈雨中跋涉而來的紅六軍團,精神百倍,指戰員們該刮胡子的刮了,背包里還有換洗衣服的都換上了。隊伍走近大柏樹的時候,正生病躺在擔架上的任弼時,一見父親的身影,立刻從擔架上跳下來,堅持要自己走;父親連忙迎上去,想讓他繼續躺在擔架上。任弼時激動萬分,緊緊握住父親伸來的手,說這下好了,我們兩軍終于會師了!
父親也非常激動,連連說好!好!好!我們終于會師了!
站在各自首長身后的隊伍,頓時歡呼雀躍,掌聲如雷。在兩軍領導人歷史性握手之際,雙方擁上來熱烈擁抱,相互通報姓名,又相互捶打著對方的肩膀。后面的人擠不進去,急得朝天放槍。
木黃的這棵千年古柏,就這樣見證了兩軍會師的偉大時刻,見證了紅軍中幾個湘籍領袖久久地把手握在一起。
兩軍會師后,雙方領導人在鎮上的水府宮召開緊急會議,商量下一步行動。會議根據中央的部署和黔東的敵情,作出了迅速向湘西發展的決定,而且事不宜遲,第二天便拔寨啟程,實施戰略轉移。
10月25日,兩軍到達酉陽紅三軍大本營南腰界。這里雞鳴三省,群眾基礎穩固,暫無敵人追擊之虞。部隊駐下后,用紅六軍團的電臺及時向中央軍委報告了會師情況。26日,在南腰界一塊坪地上隆重召開兩軍會師大會。在會上,作為中央代表,任弼時首先宣讀了黨中央為兩軍會師發來的賀電,接著宣布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兩軍整編后正式稱為紅二、六軍團,設軍團總指揮部,總指揮賀龍、政治委員任弼時,副總指揮蕭克、副政治委員關向應,參謀長李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其中紅二軍團下轄四、六兩師4個團共4300余人,賀龍任軍團長、關向應任政委。紅六軍團的軍團長仍為蕭克,政委仍為王震,下轄3個團共3300余人。
父親尊重中央紅軍,信賴中央紅軍。他雖然擔任兩軍會師后的紅二、六軍團總指揮,但他在大會上說了一句話,讓后人交口稱贊。父親說:“會師,會師,會見老師,中央紅軍就是我們的老師!”
28日,紅二、六軍團從南腰界出發,向湘西挺進,拉開了創建湘鄂川黔新蘇區的序幕,有力地策應中央紅軍長征。
熟悉中國紅軍史的人都知道,紅二、六軍團木黃會師,意義重大,它使不同戰略區域的兩支紅軍匯成了一股強大的革命力量。
1936年7月,在緊追中央紅軍的長征途中,中央軍委發來電文:“中央決定,從7月1日起,紅二、六軍團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
三
是的,我尋訪木黃的時候,正值如今我們已不堪回首的年代,那時“十年動亂”還沒有結束,在人們的期待中艱難復出的小平同志又面臨著被打倒的危局,中國大地正處在火山爆發的前夜。
自然,那時人們對父親賀龍的名字還諱莫如深。都知道他作為共和國開國元帥,在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盡管中央在1974年已作出為他平反昭雪的決定,召開了有周總理參加的追悼會,但有關方面規定不準見報,不準宣傳。正因為如此,在那個騷動不安的秋天,我是懷揣著1974年9月29日中央發出的《關于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上路的。在這片寫滿父親的光榮,每個人都說得出他名字的土地上,我每到一地,每遇到一個當地領導,都要拿出那份紅頭文件給他們看,讓他們眼見為實。我對他們說,毛主席都說話了,賀龍是個好人,對中國革命有過巨大貢獻。在中央為父親舉行的追悼會上,帶病出席追悼會的周總理連鞠了7個躬。我還說,我是按照周總理的指示,以中國革命博物館文物征集組副組長的名義,沿著賀龍等老一輩革命家創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足跡,來尋訪和收集革命文物的,請多多包涵。
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是那樣的謙卑,那樣的怯懦,就像魯迅筆下那個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其實大可不必,當我第一站到達印江,縣里的領導就傾巢出動,甚至在我住著的縣招待所安排了崗哨。這讓我大感意外,又大為感動。我想,天下自有公道,原來老區人民并沒有忘記我父親,沒有忘記他們這一代革命老前輩。還有什么比這片土地上的人,在那樣一個錯亂的年代,在心里深深地銘記著他們的功德,更讓人感到激動和欣慰呢?
路途遙遠又崎嶇,第二天一早,縣草會主任和副主任、木黃所在的天堂區草委會主任,還有縣公安局負責安全保衛的同志,近十人前呼后擁,一起陪著我去天堂區蘭克公社的毛壩尋訪。那兒有紅三軍一個師部的舊址,并有經常隨該師行動的我父親的舊居。戶主是個叫陳明章的老人,當年給我父親做過飯,放過哨,至今還能說出他的音容笑貌。
走進那棟年久失修的房子,樓下的一間廂房洞開,我心里一驚,仿佛聞見從里面飄出來一股熟悉的煙草味。陳明章老人說,我父親當年就住在這間廂房里,在夜間,他聲震屋瓦,常聽見他累得像打雷那樣打鼾。聽見這句話,我一頭往廂房里鉆。屋子里逼仄、幽暗、潮濕,微弱的光線從一扇不大的開得很高的窗口射進來;兩條長凳架著一塊薄薄的床板,想必就是父親睡過的床了,靠近頭部的位置明顯有松明火熏過的痕跡。那時還沒有開放參觀一說,更不敢提賀龍曾在這里住過,我一眼認定都是原物,而且幾十年都沒有人動過。我趴在留有父親汗漬的床前,想起他睡下后又撐起身子來夠墻壁上的松明火點煙斗的情景,止不住失聲痛哭。父親苦啊!但當年他苦,是他心甘情愿的選擇,苦中有樂,有他能遠遠看到的光明和希望。可后來呢?后來革命勝利了,他當了人民贊頌的元帥,卻在那場黑白顛倒的運動中,死在了一間同樣陰暗潮濕的屋子里,而且那是一間鋼筋水泥屋子,墻壁比這還堅硬,還冰涼;而且父親去世的時候,重病纏身,連一口水都沒有喝上……
全程陪著我的縣草委副主任張朝仙,后來在她自己整理的回憶文章中這樣記述:“賀捷生撫摸著父親曾經睡過的床,睹物思人,想到父親為黨和人民的事業革命一輩子,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都度過來了,卻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殘酷迫害含冤而死,不禁悲從心起,泣不成聲。看到她的哀傷,不知道該怎樣安慰她,我想還是讓她痛哭一場宣泄一下為好。從陳明章家出來到公路有三里左右路程,賀捷生邊走邊哭,一直到上車才止住哭泣。這次慟哭,是我陪她在整個尋訪過程中哭得時間最長的一次。”
接著我們去了青坨紅花園。
我記得清清楚楚,在一個叫何瑞開的老鄉家,進門便看到板壁上保留一條巨大的紅軍標語:“反對川軍拉夫送糧,保護神兵家屬。紅三軍九師政治部宣”。字跡古樸,醒目,散發出一股在那個年代紅軍和民眾心心相印的感召力。從紅二、六軍團幾個幸存的老同志嘴里,我聽說當年負責往墻上刷大標語的,是后來長期主政新疆的王恩茂。我不敢斷定這條標語就是他寫的,但我說,這是一件難得的珍貴文物,征詢主人何瑞開愿不愿意讓中國革命博物館征用。怎么不愿意?何瑞開拍著胸脯說,只要給我一個屋頂避雨,需要這棟房子都可以征去。又說,賀同志,你父親當年為我們打江山,生生死死,圖個什么?還不是圖我們老百姓能過上太平日子!現在真太平了,沒有人欺壓我們老百姓了,我怎么舍不得這壁木板?還說,我懂,不是這壁木板有多么金貴,是紅軍寫在上面的字,字字千金。
這天,我們還去看了鉛廠黔東蘇維埃工農兵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址,楓香溪湘鄂西分局會議會址。兩個地方都是窮鄉僻壤,需要翻山過坳,累得人筋疲力盡。令人痛心的是,因為父親蒙受冤屈,這些理應受到保護的革命舊址,已無人問津,顯得破敗不堪,岌岌可危,有幾處墻壁開始坍塌。
從楓香溪會址出來,已過傍晚7時,黑下來的天突然下起了瓢潑大雨,滿世界回響著雨打山林的聲音。下一站去耳當溪,還要走6里山路才能坐上車,只能冒雨前行。走在雜草過膝的山路上,衣服很快便濕透了。天又冷,渾身起著雞皮疙瘩。走到耳當溪,水漫進了吉普車里。車往前開,看不見一盞燈光。走著,走著,耳邊傳來轟轟隆隆的流水聲。
張朝仙說,賀處長,這地方叫沙坨,前面就是烏江,就是紅軍突破烏江的烏江。今晚我們也得突破烏江,到對岸的沿河縣投宿,但江上沒有橋,必須擺渡過去。又說,賀處長,沿河是印江的鄰縣,條件可能還沒有印江好,要有思想準備哦。在路上,張朝仙自作主張,總是叫我“賀處長”,我多次糾正她說,我不是處長,是文物征集組副組長。她固執地說,國務院“文革”領導小組的領導也叫組長,那是多大的官啊!你們中央來的人,組長都比我們縣長大,叫你處長還不應該?聽她一路對我表達歉意,說貴州窮,貴州的老區更窮,讓我受委屈了,我又忍不住說,你們能這樣接待我,已經讓我感激不盡了,還講什么條件?你以為我有多么嬌氣啊,其實我也為人妻,為人母,吃的苦和受的罪,不比別人少。她沒話說了,驚愕地看著我。
在江邊等船的時候,夜色漆黑一團,深夜的雨打在肌膚上冰涼刺骨。登上渡船后,湍急的浪濤噼噼啪啪地撞在渡船上,明顯感到船身在震顫。站在甲板上,比我高大的張朝仙用雙臂護著我,好像怕我被浪濤卷走似的。我在想,當年父親他們反反復復過烏江,有多難啊!
到達沿河縣招待所,已是下半夜了。服務員在半醒半夢中從窗口扔出來一把鑰匙,讓我們自己去客房。打開門一看,這哪里是縣招待所?分明是北方的大車店:房間里擺著八九張硬板床,沒有被子、褥子和床單,也沒有蚊帳,簡陋的床板上鋪著滿是破洞的粗席子。雖是初秋,但山區的雨夜很冷,加上在山里跑了一整天,又淋了雨,睡過去肯定要著涼。我對張朝仙說,就這樣湊合一夜吧,反正天快亮了。張朝仙說不行,丟咱老區人的臉,轉身去找服務員。只聽見她對服務員說,這是北京來的領導,你們得給她換一床干凈的被子和床單,把領導招呼好,我們無所謂。沒多久,她抱回來兩套破舊的被褥,給我鋪好后,說賀處長,您好好休息,今天太累了,早點睡,有什么事叫我。說著往隔壁走。我知道隔壁的條件比這還差,一把拉住了她。我說朝仙同志,你就住這里,我們在一起說說話。
這個晚上窗外雨水滴答,空中蚊蟲飛舞,我和張朝仙在各自的床上靠墻而坐,扯著被子蓋住雙腿,聊了很久。我把我父母怎么結的婚,母親是個什么人,姓什么,叫什么;我父親帶領紅三軍到黔東后,母親怎樣懷著姐姐紅紅在湘西的山里打游擊,姐姐紅紅又是怎么死在她手里的;還有我姨騫先佛怎么嫁給紅六軍團軍團長蕭克,怎么在長征途中生的孩子;我的童年怎么寄養在湘西,大學沒畢業又怎么去青海支邊等等,都給她說了。聽得她淚光閃閃,連連說想不到,真是想不到。我還對她說了我父親當年在黔東的一個生活細節:那時候戰斗頻繁,居無定所,父親為了養精蓄銳,養成了在扁擔上睡覺的習慣。他在兩條凳子上放一根扁擔,又在手指上綁一根點燃的香,躺下就能睡過去。當那根香燒疼他的手指,馬上就能醒來。因此,他每次睡覺的時間,掌握得就像鐘那么準確。我講完這個細節,張朝仙已在黑暗中抽泣。她說,當年打江山有多苦啊!我弄不明白,現在為什么要整那些老干部,這不是過河拆橋嘛。
從這個晚上開始,我和張朝仙成了朋友,以后常有來往。
四
我再次站在木黃那棵千年古柏下的時候,是10月2日。這時我在黔東的崇山峻嶺中前后跋涉了近10天。中途張朝仙送我在烏江上船,回貴陽參加了一個文物會議。正想著下一步往故鄉桑植走,北京打來電話,說中央準備開展紀念紅軍長征40周年活動,要我在當地請一個攝影師,重回印江木黃和酉陽南腰界去拍組照片。我重新出現在印江縣招待所時,張朝仙大感意外,以為我把魂丟在了印江。
我說我的魂真丟了,但沒有丟在這里,丟在了木黃。
還是張朝仙陪我下去。到了小鎮上,攝影師只顧得取景拍照,我獨自在大柏樹下盤桓,心里有個莫名的念頭在不住地翻涌和纏繞,卻捉不住它,說不清它。之后,我撥開樹叢,攀上了父親曾經戰斗過的一面山坡。這里居高臨下,能一覽無余地看到木黃的全貌——
遠處的梵凈山主峰,虎踞龍盤,在奔涌的云霧中巋然不動。腳下的木黃鎮,夾在一道深深的峽谷中,兩岸的青山雄偉,俊秀,一派蒼茫。在秋日陽光的照耀下,正在變色的樹葉泛出一片片金黃,如同漫山遍野散落的金箔。與鎮子同名的河流穿峽而過,像一條玉色飄帶逶迤而來,又逶迤而去。三三兩兩散落在田野里或山路上的農人,小得像一只只各自在為生活奔忙的螞蟻,好像日子天長地久,誰都是匆匆的過客,即使哪年哪月發生過什么事情,也不過如此,漸漸地就會被遺忘。
想到我兩次來木黃,無論在兩軍會師的古柏下,還是在兩軍會師后召開會議決定下一步行動的水府宮,都沒有一塊像樣的標牌,更別說作為歷史見證開辟出來供人瞻仰了,心里不禁有些苦澀。
10月3日,我們經松桃、秀山去酉陽的南腰界,過縣過省的旅途峰回路轉,險象環生。不僅是近日下了幾場大雨,把多處的路橋沖斷了,車開著開著就得下來步行,而且還有不明身份的人出來搗亂。
那是我們從酉陽去南腰界的路上,途經金家壩休息,忽然有人對前來陪同我們的酉陽縣委孫副書記說:“孫書記,你要小心,有人要殺你。”當時正值“文革”后期,威脅恐嚇領導干部是常有的事,因此孫書記并未理會。但稍過片刻,還是在金家壩,忽然又有人貼上來問:“孫書記,你們晚上還回來嗎?”孫副書記還沒在意,說當然回來。我們在南腰界拍完照片回酉陽,天色已晚,開著大燈的兩輛車在夜幕中緩緩行進。可是,當我們的車駛進一片密林,公路上突然橫著一根巨大的木料,路中央堆著一大堆石頭,無法通過。此時黑夜沉沉,兩邊的山林靜悄悄的,偶爾傳來幾聲夜鳥的驚叫。張朝仙說:“壞了,看來真有人破壞!”然后對孫副書記說:“孫書記,不能再往前走了,不如折到李溪先住下。”孫副書記想起在金家壩的遭遇,也覺得事情蹊蹺,同意改道往李溪走。
后來證實,那天晚上真有人要鬧事,并且是沖著我來的。原來,1934年,紅軍在南腰界貓貓山開過一個大會,當場殺了幾個惡霸。那幾個惡霸的后代聽說賀龍的女兒來了,躍躍欲試,暗中組織了幾十個人攔路,企圖趁亂報殺父之仇。
第二天,孫副書記調來一輛救護車開路,料想那些人不敢在大白天膽大妄為。車開到頭天晚上斷路的地方,那根橫著的木料和路中央堆著的石頭依然還在,公路上散落一地燃燒過的柏木皮火把,到處是新鮮的屎尿;兩塊石頭上分別寫著:“到此開會,彭?菖?菖”和“我們到了”等字樣。我們下車把木料和石頭搬開,用了半個多小時才把路打通。
雖是虛驚一場,但回到印江,我的心里仍然五味雜陳。倒不是感到后怕,我是想,都什么年代了,怎么還會出現當年被懲治的惡霸后代尋釁報仇?而且公然把目標對著賀龍的女兒?這說明歷史被淡忘到了何等地步!也說明紅軍和賀龍的威名,被時間,尤其是被“文革”的倒行逆施,漸漸地磨滅了。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啊!
就在這時,那個幾天前在木黃莫名纏繞我的念頭,忽然變得清晰起來,明確起來。我想我知道該做什么了。
離開印江那天,我鼓足勇氣,含蓄地對張朝仙,其實是對她擔任的縣草委副主任的職務說,紅二、六軍團1934年9月在木黃會師的歷史地位有多重要,無須我多言。但我去過洪湖,也去過遵義,前些天又和你一起去了南腰界,這些地方都有歷史紀念碑,你們想過木黃也應該有嗎?
張朝仙沉默許久,認真地說:“賀處長,我明白你的意思,但這是一件大事,偏偏我們又是貧困的少數民族地區,容我慎重報告縣委。”
五
1977年,我收到張朝仙寫來的一封信,告訴我說木黃兩軍會師紀念碑已經破土動工,碑址就選在我攀登過的那座山下面。現在這座山取名為將軍山,那棵大柏樹,取名為會師柏。張朝仙還說,紀念碑的碑文,他們請1975年陪同我去木黃尋訪的省博物館黨史專家譚用忠同志撰寫,但碑名至關重要,必須請一個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留下字跡,問我能不能找到當年率部會師的紅六軍團政委、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震題寫。
我心里一高興,馬上回答說,這個任務包在我身上了。
事后印江的朋友告訴我,我離開木黃后,張朝仙立刻向縣委書記瞿大國匯報了在木黃建碑的想法。“我知道縣里窮,但可以先拿出萬把塊錢來建個簡單的紀念塔。”她說:“有總比沒有好啊,不能被后人戳我們的脊梁骨。”瞿大國完全同意張朝仙的提議,并在縣常委會上討論通過。有意思的是,在考慮主管紀念碑建設的人選時,大家都想到了張朝仙。
少數民族地區的同志感情淳樸,認準的事情按照自己的習慣干了再說。張朝仙不負眾望,卷起鋪蓋一頭扎進木黃,動員群眾土法上馬,興致勃勃地開始了建碑。設計圖紙還沒有出來,他們就開始平地基,修公路。木黃區更是積極響應,從各公社抽調一個民兵排上陣;又從全區選調了一批石匠,進山提前采集石料。縣里經費緊張,常委會決定下撥的一萬元遲遲沒有到賬,木黃區的同志們說,給紅軍蓋碑,是我們多年的愿望,我們不要縣里的錢,給大伙記工分。工地上生活艱苦,沒有水,便發動機關干部職工和學校師生前來挑水,讓各部門負責拉沙。他們提出的唯一條件,是山里的石料用手掰不開,縣里得提供雷管和炸藥。
木黃雖是老區,又是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交通閉塞,但紅軍烈屬和親屬多,群眾覺悟高,有許多見過兩軍會師的人還健在;甚至還有跟隨過紅軍戰斗,因傷或因其他原因沒有跟著走的老游擊隊員,聽說要建紅軍會師紀念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紛紛擁來助陣。
將軍山下,大柏樹旁,一時人聲鼎沸。
我后來聽到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天,張朝仙站在張家溝采石場向大家宣講建碑的意義,人群中突然有個老漢高聲回應說:“這個同志講得好,為紅軍建碑是我們木黃的責任。”張朝仙尋聲望去,只見那人滿臉皺紋,背像弓那樣駝著,頭發稀稀疏疏地全白了,手里拄著一根拐杖。張朝仙走過去問他:“老伯,你是誰?在辦哪樣?”老漢說:“我叫張羽鵬,天堂區陡溪公社茶坨村人,賀老總在印江鬧革命的時候我當過游擊隊長。聽到要為紅軍修紀念碑,我特意趕來出力,連口糧都帶來了,不信你來看嘛。”張朝仙朝他身后背著的背篼一看,果然有一包米,一包飯,一些蔬菜。張朝仙當眾表揚老漢說,你這個認識很好,很有代表性,大家要向你學習。因為縣城與天堂公社同路,那天回縣城時,張朝仙特地請張羽鵬坐她的車走,老漢說:“我不跟你走,我是來修碑的,又不是來看熱鬧的。碑還沒建好,我走哪樣?”最后,張老漢硬是堅持到紀念碑完工,才背著背篼回家。
這個叫張羽鵬的老漢我還見過,在北京接待過他。那是多年后,張朝仙給我打來電話,說那個背著背篼去木黃修碑的老游擊隊員,你還記得嗎?現在他的眼睛不行了,看不見了,想來北京治病,能不能幫幫他?我說,怎么不記得?你讓他來吧,我來管他。那時我的老伴李振軍還在世,張老漢到了北京,我們一起去看他,一起把他送進醫院。老漢的住院費和治療費,全部免除。當然,這是后話。
印江在木黃土法上馬建會師紀念碑的消息,很快傳到省里,省文化廳、省設計院和省博物館迅速派人來查看。他們既為群眾自發紀念紅軍的精神感動,又覺得按此辦法建碑太簡陋,與兩軍會師的重要地位不相稱,必須重新設計并把碑挪到半山腰,那兒視野開闊,也更莊重,更氣派。省里的同志說,給紅軍立碑,那是千秋萬代的事情,不能壘幾塊石料豎一面碑了事,像蓋一個土地廟。印江的領導聽得頻頻點頭,從心里感到省里的人就是比自己站得高,看得遠。可他們接著說,那么錢呢?那得要多少錢?我們拿不出來啊!省里的同志說,這樣吧,我們給你們設計圖紙,再撥給你們四萬元,只有那么多了,你們得精打細算。縣委和縣草委的人笑了,說四萬元不少了,我們勒緊褲帶,再自籌兩萬。
我就是在這個時候收到張朝仙的來信,讓我想辦法請國務院副總理王震題寫碑名。我知道王震叔叔很忙,但再忙他也不會推辭的。因為木黃會師不僅是紅軍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我父親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包括蕭克和他在內——他們個人革命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何況他是我父親的老部下,對父親和那段歷史感情深厚。所以,當我向他報告木黃正在建造紅軍會師紀念碑時,他馬上說:“好啊,需要我做什么?”
這已是1978年,聽說我拿到了王震的墨寶,張朝仙在電話那邊激動得哭了,馬上讓正在北京參加全國婦聯代表大會的縣婦聯主任上我家來取。婦聯主任開完會立即趕回印江,到了縣里得知張朝仙在銅仁開會,又馬不停蹄趕到銅仁,當面把墨寶交給張朝仙。
1979年夏天,由王震題寫碑名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二第六軍團木黃會師紀念碑”就要落成了,縣里挑選7月1日建黨58周年這個特殊的日子舉行揭幕儀式,并來電來信鄭重邀請我參加。不巧的是,我剛做完一個手術,行走不便,未能成行。但是,我字斟句酌地給印江縣委寫了一封賀信,表達我難以平復的喜悅:
印江縣委負責同志:
你們好!收到你們的來電和來信,心情非常激動,木黃會師紀念碑終于落成了,這是一件政治上的大喜事,我萬分高興。記得1975年,我兩次走訪印江,那時正是烏云壓頂,“四人幫”橫行之時。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給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講話消息尚不能公開見報,印江縣委的領導瞿大國、張朝仙等同志就提出要修建木黃會師紀念碑,對我的鼓舞和教育至今仍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印江不僅山清水秀,風景優美,還是個有著光榮傳統的革命根據地,在艱苦的戰爭年代,為革命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后,繼續發揚革命光榮傳統,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貢獻,這些都是值得我學習的。總之,1975年的兩次印江之行,感受很深,受益甚大。也非常感激縣委對我的熱情接待。這次我非常想去參加木黃會師紀念碑的落成典禮,但因我患甲狀腺功能亢進,剛動過手術不能參加,甚感遺憾,請你們原諒。不過,我一定要爭取第三次去印江看望老根據地的人民……
責任編輯 谷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