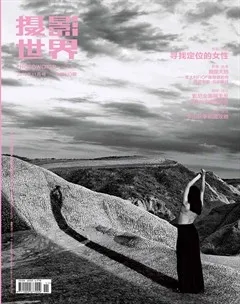楊文潔:她自己的一間房










“女人想要寫小說,必須有錢,再加一間自己的房間。”
在《一間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1929年)中,化身瑪麗的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國女作家,批判家,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人物,《一間自己的房間》為其代表性散文作品—編者注)因為女性身份而被禁止單獨進入圖書館,她不得不在柔軟而適于思考的草坪上疾步走過,躲避著守衛,退回到“屬于她們的粗硬的礫子路”上。思考的小火苗被無情掐滅,瑪麗覺得“所有一切都像銹菌一樣,吃掉了春天的花朵,從心里把樹木毀掉”。面對她的窘境,伍爾夫在小說中慷慨“贈予”她每年500英磅的遺產。
500英鎊和一間房,獨立的經濟能力和完全屬于個人的私密空間,這對當時的女性來說恐怕是天方夜譚。此后的80多年中,在廚房和客廳圍著父親、丈夫和兒子打轉的女人們披荊斬棘,為被掐斷的天分、思考和彌足珍貴的自我爭取權益。
女攝影師楊文潔的《她自己的一間房》系列正脫胎于此。在女性經濟獨立不再是妄想的今天,對個人空間的傾軋、擠占卻還在不斷發生。獨居的女性往往承受著更多壓力,卻也意味著擁有更為獨立的思考空間和更豐富的自我世界。
楊文潔拍攝了單身女性們在自己寓所的肖像,展現這些女性在屬于她們自己的空間中最自然的生活狀態。她說:“這個專題意在表現一位獨立女性所擁有的復雜生活,她生命中的那些時刻:沉思、快樂、悲傷、滿足、憤怒,以及在自己空間內的自由自在。擁有自己的房間,就如同是擁有了自己的天地,在那里一切各就各位,有條不紊。這個專題就是想探索這種生活方式的深度,并去探求個體身份的意義。”
女性和她們的房間
楊文潔第一次讀到伍爾夫《一間自己的房間》時還在讀大學,對此一片懵懂。在上海長大的她一直三代人同居一間陋室,直到23歲才擁有自己的房間。
拍攝專題第一組照片時,她重讀了這部作品,契合感才真正油然而生。照片中,她的朋友陶立夏蹲在床邊,右手舉著蘋果,眼神中滿是安穩和放松。這組照片只是她使用中畫幅拍攝肖像的嘗試之作,卻意外打動了自己。在ICP(國際攝影中心,位于美國紐約)進修時,她放棄了導師力薦的紀實類項目,將這一專題進行下去。
楊文潔的拍攝對象來自世界不同的國家,從事著各類職業,有商人、畫廊代理、藝術家、攝影師、自由職業者,甚至包括一名專業女巫。她們大多單身,過著獨居生活。在紐約的每個周末,楊文潔的行程都很滿,她造訪每個街區,和陌生人成為朋友,聊天,聽故事,最后來到她們獨居的寓所,拍攝她們的生活。
自然光線、近距離,房屋里的細節維持著本來的模樣。被攝者們居家時的日常穿著,或寂寞或滿足的神情,楊文潔希望展現的不是被攝者經過修飾的完美狀態,而是捕捉女性在她們的私密空間中才有的微妙感受。
“我最喜歡的一張照片,是一位60歲的老太太。”在浴室的毛玻璃后,Connie舒展開身體,和玻璃上的魚一樣愜意。“她自然而然地把浴袍拿了下來,我根本沒有要求她做這件事,就是這樣一個非常放肆的狀態,她很享受她自己。”沒有人能猜到她已經是3個孩子的祖母。Connie在40歲時突然愛上了同性,毅然結束了自己的婚姻,和一位比她小十幾歲的愛人維持了十多年情感關系。
房間里充滿撿來物品的神經學家穿著朋友的舊紅裙坐在箱子上,這箱子也是男友從街上撿來送她的禮物;和貓咪生活在一起,睡著沙發床,衣物上粘滿貓毛的女子眼神中流露出孤獨感;愛慕者從未間斷的舞者躺在大床上,床收起后是一面鏡子,她可以隨時穿上舞鞋對鏡舞蹈;住在頂層的獅子座女人站在陽臺澆花,整個曼哈頓都收攏在她腳下;愛跳弗拉明戈的樂器代理商窩在沙發里,裸露的身體只披著紅色披肩,鮮亮的紅和房間的暗凸顯了她眼神中不經意的驕傲。
每個被攝者身上的閃光點都讓楊文潔興奮不已,她觀察一切細節,用這些微妙的部分判斷和展示被攝者的個性。“只有在紐約,才會有那么多不同膚色、不同年齡的獨居女性,愿意和我分享她們的人生。”回到上海后的楊文潔發現這一專題很難繼續。聽說“房間”系列而聯系拍攝的人并不少,可大部分人在意的是自己在照片中的形象“美不美”,在意自己的身材是否過于豐腴,是否有某個角度會突顯面部的小瑕疵。
這與專題理念背道而馳。“她們本身不滿足于她自己的狀態, 我覺得她們不真實。”楊文潔拒絕了這些請求,在她看來,拍肖像的關鍵在于接受拍攝的那個人, “房間”系列中的女性,無一例外都熱愛生活,保持自足而享受的狀態,“我沒有碰到一個人跟我抱怨。生活給予她們什么,她們就enjoy(享受)什么 。”
建造于內心的房間
楊文潔并不想為“房間”系列貼上女性主義標簽。“很多人都說這是一個非常女性的話題,但我覺得對現代人來說,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匱乏的:個體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個體在盲從社會告訴他們的那些需要。”只是這一現象在女性身上體現得更為明顯。許多人每做一件事都會考慮他人的看法,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見,喪失了自己做決定的能力,家庭主婦和職業女性中這類情況都不鮮見。
“每個女性對自我空間的需求是不一樣的,但我覺得有自己空間的女性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楊文潔曾表示,拍攝的初衷是源自童年時對自己房間的向往。然而盡管度過了沒有個人空間和隱私可言的23年,她卻始終在內心為自己搭建了一座房間,隱遁其間和自己相處,任憑情緒和思考肆意流淌。
在拍攝之初,楊文潔仍有一些憂慮,但這些拍攝對象展現出的獨立性和對生活的熱愛讓她堅定了“房間”系列的創作,這里展現的生活正是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現在的楊文潔仍然獨居上海,男友遠在美國,也常常會收到父母和朋友們對“人生大事”的關心。她希望向困于“剩女”之名的女孩乃至整個社會展現一種不一樣的生存方式,讓人們看到一個更具包容性、容許個體差異性存在的社會,一些更為自足,自我認知和自我認同都得到高度發展的女性是怎樣生活的。
在楊文潔看來,有沒有一個真實的房間并不重要,私密而獨立的空間可以是任何形式的。人以個體的形式存在于世,需要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而非作為他人和社會陳習的附庸。坐擁豪宅卻內心怨懟的人數不勝數,而那些內心自由柔軟的女性,即使沒有自己的空間,她的世界始終溫暖向上。
自己的房間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楊文潔:可以更加獨立思考自我的世界。我在做這個專題的時候一個人在上海住了很長時間,跟一些同齡的朋友們相比,我們的生活完全是兩個世界。戀愛、結婚、生子,她們會被更多的瑣事所纏繞,每做一件事都會有相應的回應。我覺得我那個時候可以比較自由地決定自己的生活,可以不用顧忌空間里的另外一個人。可能對于其他人來說,她們從公司回到家會感覺到家里的溫暖、樂趣。而我需要在家中處理一些工作事務,我會感受到在外面忙了一天,回到家中還要思考我接下來的工作。
人們都適度地需要這樣一個空間。至于它以什么樣的形式出現,是房間、還是以度假的形式都不重要。因為每個人在世界里都是一個個體,我們中國人就是群體化的東西太多了,所以每做一件事情都在考慮別人會怎么看,征求別人的意見或者征求家人朋友的意見,我碰到過很多這樣子的女孩子。可能這些女孩子很早結婚生孩子,反倒沒有自己做決定的能力了,每件事情都在看,因為她不希望出錯,她希望會有人幫她做權衡。女人應該明白自己要什么而不是整天作為一個附屬品。
“房間”系列的拍攝,你是否提前有一個預設?
楊文潔:我之前做過7年的電影,我會去看一些細節,通過房間里一些細節去判斷這個人的個性。每個人房間里的東西都不一樣,就像有一個上海女生打開冰箱的一張,穿著豹紋內衣的那張。我就說,那個冰箱代表了一切,我要說的東西都在里面了。為什么我要選這個點?還有一些衣服堆在一起,或者說別的也能代表,但可能在我眼里,這個冰箱就是她的生活,忙亂的,冰箱一打開可能只有兩袋酸奶,或者一些其他的東西,與你去別的人家看到的就不一樣。
如何讓拍攝對象保持自己在家中的放松狀態?
楊文潔:有些人可能并不放松,有些人面對鏡頭會緊張,我會先和她聊聊天。有些人5分鐘,有些人可能要1個小時才能進入狀態。
影像語言如何傳達女性經驗?
楊文潔:我沒有試圖通過照片去告訴別人什么,我是試圖用照片來告訴我自己,我感受到的那一刻的東西,至于別人是否能感受到,我覺得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完全全感受到(和我一樣的)。我欣賞的照片,帶有很強的情感。以前我也是個視覺動物,因為是拍電影、拍廣告出身,喜歡那些紀實性,大廣角,沖擊力很強的照片,也和現在很多年輕人一樣,看到大光圈的照片覺得美呆了。但現在我不會這樣去拍照片了。哪怕我現在去喜馬拉雅山,去最美的地方,我都不帶相機。因為我覺得,如果去拍那些大家都看得到的東西,我沒有必要去做攝影師,我要拍大家看不到的東西。(什么樣的東西是大家看不到的?)情感,情感不是大家看得到的,但它是每個個體不一樣的感受。
談一談你在從業過程中和性別相關的困惑。
楊文潔:我經常被拒絕,因為是女性。我以前剛畢業的時候做副導演,在現場,整個劇組就兩三個女性,其他都在化妝服裝這些部門。而且我剛從紐約回來的時候,應聘一些媒體、雜志,他們看到我這樣的年齡就怕你要生孩子等一系列問題。從美國回來后我發現,很多女性都很努力想證明自己不比男人差,其實根本沒必要證明,我本來就跟你們不一樣,沒必要去跟他們拼。
尤其在我做完這個專題之后,也可能是年紀大了,有很多事我都可以放得下了。我覺得這個社會沒有任何不公平,你可以把不公平變成公平。因為很多事情你看到不公平,就發揮不了你的長處,那這個事情就是不公平的。他們說的沒錯,女人就是要生孩子,就是要做母親,是會把很大精力放在孩子上面。你非要拿你的弱勢去和男人比,那就是要去玩這個不公平的游戲。但是你要想,我們看到的東西和男人是不一樣的,我們天生和人溝通的能力是男人沒有的。有多少男人想去拍女人的房間,但他們拍不過我。
優勢和弱勢是相對而言的,沒有一件事你占得了絕對的優勢,也沒有一件事你永遠處在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