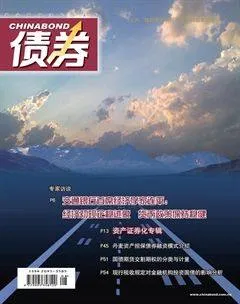流動性:從漣漪到波濤的演繹






▲國內經濟潛在增長率中樞的臺階式下移不可逆轉,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形勢緊迫。
▲經濟體只有完成去杠桿過程,資金面才能慢慢走向平穩,才能有效降低企業單體的融資成本,進而更好地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隨著去杠桿累積幅度的逐漸增大,流動性的緊張程度也會慢慢變小,從物理學的角度看,是一個“阻尼振蕩”的過程,而且利率中樞將呈現下移的趨勢。
今年6月份,銀行間市場經歷了年內資金面最緊張的階段,這一驚險的過程值得反思。7月末資金面的漸行漸緊也說明流動性的緊平衡格局并沒有退潮,而階段性、突發性、反復性仍是資金面緊張的主要特點。
外匯占款急速下跌 銀行間流動性波動劇烈
6月外匯占款下降412億元,結束了長達數月的連續增長,原因有二:一是國內廉價勞動成本優勢弱化,出口順差呈下降趨勢,在政府擠出進出口水分后,出口競爭力下滑趨勢更加明顯;二是美國經濟強勢復蘇,國際投機資本大幅逃離,特別是美聯儲QE政策退出預期愈來愈強,市場風險偏好不斷升溫,國際投機資本有回歸歐美的訴求。其中,后者對外匯占款的影響更加明顯、更加長遠,而且這種跡象在5月份就已經初現端倪。同時,國際投機資本的流動往往具有不可控性、突發性。如1-5月份,外匯占款新增約1.5萬億元,而6月份卻由正轉負,年內增量與下跌均超預期,而央行加強對結售匯的調控也不可預期,由此,造成了銀行間流動性波動劇烈(見圖1)。
鑒于美國制造業的復蘇以及市場風險重新偏好美國(美國股市連連創下歷史新高),國內外匯占款的回落可能在相當的時間內將成為常態。考慮到國內貨幣供給模式,預計流動性整體緊張的格局不會變化,再經過突發性因素與不可控性因素的交織,流動性短時間就呈現出從“漣漪”到“波濤”的態勢。
另外,與市場主流觀點不同,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并未完全對沖由外匯占款下降而產生的影響(見圖2),即使從2012年6月份利率市場化改革深化以來,央行公開市場操作也未完全對沖銀行間流動性的缺口,至少存在非常明顯的滯后性,而金融機構與企業單體存在資產杠桿期限錯配風險,一旦風險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流動性危機”。結合近兩年的數據來看,2季度由于外匯占款與央行凈投放產生的基礎貨幣增量較低,而且正好趕上不能有效滿足國內經濟增長速度和市場的資金需求,換句話說,外匯占款回落產生了巨大的資金缺口,而市場也缺乏自我修復的能力,再經過市場的稍微炒作以及財政繳款等不確定性變量的擾動,很容易造成資金面“缺血”現象,由此,市場利率也難逃“波濤洶涌”的行情走勢。
財政繳款周期性效應增強 資金面階段性緊張加劇
如果說外匯占款是銀行間流動性最核心的影響因素,那么財政存款可以說是最敏感的驅動因素。近兩年來,隨著利率市場化的不斷深入,財政繳款、投放周期與銀行間流動性的運行態勢基本吻合,而且財政繳款這種周期性效應影響越來越明顯,而外匯占款等核心驅動因素影響效果呈下降趨勢,尤其是今年春節遲于往年,致使財政繳款與投放周期明顯晚于往年。如二季度繳款日期明顯較晚,財政繳款力度明顯大于往年均值(見圖3),對銀行間資金面的緊張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這種階段性的緊張狀況在之后發生的概率較大。不妨設想一下,4、5月份財政繳款超預期,6月份財政投放又小于往年,那么作為財政繳款的大月份,7月財政繳款規模超預期的概率也較大,這也印證了7月末資金面的偏緊態勢。
外匯占款新增規模下降與財政繳款周期性因素增強,致使基礎貨幣大幅減少,是銀行間流動性整體緊張的主要原因。雖然央行數據顯示,貨幣供給仍呈高速增長態勢,但影響銀行間流動性的核心指標是超儲率。比如6月份商業銀行的超儲率可能低于1.5%,甚至在6月下旬資金超緊張情況下,商業銀行的超儲率可能低于1%,而且在商業銀行大幅擴張資產負債表,放大貨幣乘數的推動下,銀行的可用流動性可能更低,同時企業單體層面,面臨社會總需求的疲軟,仍需要業績層面的高位增長來充實自身的資產負債表,那么就對流動性的需求更多、更強,所以流動性需求層面也存在同比增量的概念,從而形成了銀行間流動性與貨幣整體供給相背離的局面。
高收益理財如雨后春筍 結構性緊張矛盾突出
在外匯占款缺失、財政繳款推動的背景下,商業銀行僅能依靠強大的營銷渠道來博得現有市場存量的青睞,增強攬儲能力,以此來滿足自身流動性的需求。6月份大行以及股份制銀行的高收益理財如雨后春筍般頻頻出現,如保本理財收益高達6%、8%,甚至出現兩位數的高位,而中小銀行以及農商行、券商、基金等機構顯然缺乏優勢,造成流動性結構失衡,更加劇了資金面的緊張,為6月下旬超緊的資金面下,市場利率沖至30%的歷史新高也貢獻出了不可忽視的一份力量。
同時,銀監8號文、央行8號文,均加強對銀行理財業務的監管,要求銀行對表外資產進行有效清理,然而不到不得已的時刻,商業銀行只能靠不斷壓縮業務利潤空間來維持自身資產的存續,而途徑就是犧牲銀行間流動性,甚至自身流動性來保證資產的自然到期。所以,目前銀行資產去杠桿基本也以時間換空間的模式漸漸往前推進,雖然不會對整體流動性造成損失,但資金面的結構性失衡會加劇,這也對資金面的緊張產生了不可回避的沖擊。而且這種結構性的失衡發展到一定階段,一旦市場出現信用違約等事件,流動性風險將升級為系統性風險,被推向幕前,那么資金較為充裕的大行、股份制銀行支行,難免會出現流動性“惜借”的心理,即使承擔著高收益理財的成本。
在利率市場化進程不斷加速的前提下,央行對流動性的市場自我修復能力會進行一輪又一輪的壓力測試,6月下旬的情況或許是一個開始,后續流動性的結構性失衡局面仍會出現,而7月末資金面的緊張,背后也存在著結構性失衡的因素。
貨幣政策穩中有緊 不會偏離“去杠桿”主題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流動性的緊張局面既有整體規模不足的因素,還有結構性失衡的影響,但前提都是央行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沒有通過政策層面去放松流動性、緩解市場需求的壓力。筆者并不否認,央行有增強市場自我修復能力的意圖,還有政策面確實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效應,但更深入地看,由于我國面臨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任務,上半年,央行不斷加速利率市場化進程,從而為產業升級營造較佳的貨幣環境,低利率、寬信貸(見圖4)、高社會融資(見圖5)。1-6月,社會融資總規模高達10萬多億元,但國內經濟增長維持下滑態勢(見圖6),社會總需求也未見企穩,如果說這是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產生的規律性現象,那么房地產價格的迅速攀升,資產價格泡沫風險持續加大,要從哪一個方面來進行合理解釋呢?
直觀地看,高位的貨幣增長、信貸支持在經過市場化的疏導后,又跑到了產能過剩、有資產泡沫的高利潤行業,成為經濟升級的間接絆腳石。深入地看,國內實體經濟結構的杠桿效應已經見頂,無論怎么進行貨幣刺激,似乎都不能帶動經濟的有效增長,那么經濟結構轉型已經步入不可逾越的改革階段,而貨幣政策的功效首先要滿足的就是企業去杠桿、金融機構的去杠桿,讓國內經濟體先“喘口氣”,然后再輕裝上陣,尋求更健康、更長遠、更完善的產業升級路線。
由此,貨幣政策保持穩健的主題不會改變,常態中出現穩中偏緊的概率較大,而央行放開信貸下限等政策也表明利率市場化進程依然會加速,降準、降息等政策出臺的概率持續降低,而且對影子銀行的監管愈來愈強,金融機構以及實體經濟的經營路線不會偏離去杠桿的主題。隨著杠桿效應的漸漸減弱,銀行間市場的流動性將重新步入寬松的通道,市場利率中樞也將呈現逐漸下移的態勢,這樣才能有效降低企業單體的融資成本,進而更好地支持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這是可預見的未來的貨幣市場運行的基本思路。需要注意的是,去杠桿是一個反復、曲折的過程,需要資金面的緊張來矯正市場的預期,可以理解為,緊一段,去一段,松一段,然后,再重復同一樣的過程。值得欣慰的是,隨著去杠桿累積幅度的逐漸增大,流動性的緊張程度也會慢慢變小,從物理學的角度來看,是一個“阻尼振蕩”的過程,而且利率中樞將呈現下移的趨勢。
作者單位:中信銀行
責任編輯: 印穎 夏宇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