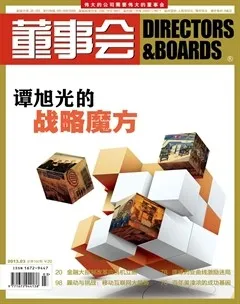中國制造業升級的動力何在?
近年來,產業升級成為中國最熱門的話題之一。中央政府在“十二五”規劃中,更是把產業升級作為中國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推動力。然而,政府和企業的高度重視,并沒有改變中國制造業仍然徘徊在低附加值生產活動的現狀。到目前為止,各級政府提出的產業升級的宏偉藍圖大多都是停留在紙上的規劃和目標,空洞無力;學術界提出的產業升級理論,也由于缺乏對我國基本國情和制度環境的考慮,難以實踐。許多人擔心,中國的產業升級最后可能會變成一句口號。
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國擺脫了資本短缺的窘境,外匯儲備總量高居世界首位;大量本土企業迅速成長,有些企業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成為了全球性經營的跨國企業(盡管離行業的領先企業還有很大差距),例如華為、TCL、海爾、聯想等公司。此外,中國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教育投資逐年增加,人均教育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種種跡象似乎在表明,中國企業具備了產業升級的條件,只要輔以適宜的產業政策,定然可以在不遠的將來趕超世界強國。這種樂觀的預測基于一個重要的理論假設,即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會導致產業升級。但這個理論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一個國家的產業進行全面、持續的升級,升級行為的主體是誰?誰是最終的投資者和最大的受益者?
實際上,中國不是缺乏產業升級的能力,而是缺乏產業升級的動力。產業WPmZ3LaCc6NLCCr/1z0OJQ==升級是通過自主創新實現產品或服務的附加值提升。只要是創新,尤其是原創性的創新,必然涉及大量持續的高風險投資。在最有能力(資金雄厚、人才濟濟)進行產業升級的企業當中,主要是大型國有企業(包括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和家族企業。但是,這兩種企業都缺乏產業升級的動力。國有企業的管理層傾向于將企業規模做大,強調業績穩定,一般會回避高風險的投資,因此國有企業的創新大多是模仿創新和局部創新;一些頗有實力的家族企業,雖有可能成為產業升級的領軍企業,但這些企業的問題是家族觀念很重,子承父業的模式限制了職業經理人的發展,而最能力和動力進行冒險活動的是職業經理人。若家族企業不能克服這種傳統理念的局限,就很難在產業升級中有大的作為。
我們一直把日本和韓國的制造業升級作為比照對象。可是,不要忘了,日本的松下、索尼,韓國的三星、LG公司,都是股權高度分散的跨國公司,資本結構的不同造成了行為激勵的差異。借鑒日本和韓國這兩個國家的經驗,不應該只看到自主創新和產業政策的作用,還要看到公司治理結構對創新投資的激勵,以及政治制度對企業制度的影響。
也許中國目前的體制和政策適合于某些領域的升級,例如能源、高鐵、大飛機制造等壟斷性行業。但在競爭性領域,中國企業想要升級,想要在國際上有競爭力,還必須得解決好最基本的升級動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