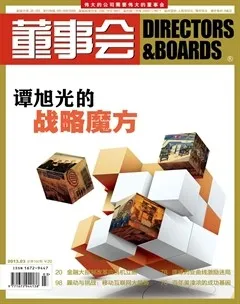證交所紀律處分措施存在斷層
根據《證券法》,以及兩大證券交易所的交易規則、上市規則、會員管理規則及紀律處分細則等相關規定,交易所的紀律處分措施主要包括通報批評、公開譴責、暫停或者限制交易、取消資格、認定不適合擔任相關職務、建議法院更換管理人或管理人成員等。
通報批評和公開譴責最常用,是一種名譽處分。這么多年來,兩大交易所年年通報批評與公開譴責一批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監事、高管,但在目前這樣一個誠信普遍缺失的社會環境下,不僅被批評和被譴責者對此無動于衷,投資者也早已對此類信息感覺麻木了。人們發現,遭遇通報批評的上市公司股價極少因此受到影響,有時甚至出現股價不降反升的怪現象,致使上市公司對被通報批評和公開譴責沒有后顧之憂。這也是為什么曾被通報批評和公開譴責過的上市公司中,有相當一部分會二次、三次違規,而未被處分過的企業會前赴后繼違規的原因。違規的成本如此之低,如果再乘以被查處的概率,上市公司違規行為的成本比起其可能的收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截至2012年底,兩市境內上市公司兩千余家,2012年被查處的為44家,被查處的違規公司占上市公司總數的2%不到。在造假違規盛行的市場氛圍之下,要說這一查處范圍已經涵蓋主要違規主體,實難令人信服。
在處分措施上,44家公司除個別高管被認定為不適合擔任相關職務外,幾乎全都是名譽處分。而且名譽處分中較重的公開譴責也只有9家,其余80%的公司是被課以毫無違規349fc2116f472b6a22567c34befdc94af1fd8a25e10a85dd43236f2e32625f51成本的通報批評。仔細看交易所的處分決定,會發現很多公司涉及好幾項違規行為,但也僅被處以一個最低程度的通報批評。比如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日常關聯交易違規、關聯投資違規、關聯擔保違規、關聯財務資助違規等四項違規行為,但深交所僅給予公司及公司董事長一個通報批評的處分。再如粵水電,在2010年和2011年期間,也分別涉及三個不同項目的關聯交易,均未及時履行相關審批程序和信息披露義務,深交所也僅對粵水電及其監事會主席和副總經理兼總工程師給予通報批評的處分。交易所對違規上市公司手軟到何種程度,由此可見一斑。無怪乎有學者指出,“自律組織以追求成員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不應被期望像慈善團體、或者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那樣服務于公共利益”。
在處分時間上,交易所公布的處分決定,很多被處分事項發生在2011年、2010年、2009年甚至2008年。交易所的自律監管之所以被認為是一國證券監管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被公認為是市場的第一道防線,是因為交易所的自律監管能夠對市場做出迅速反應,從而彌補行政監管的滯后性。違規行為發生后的較長時間內未被發現或者被發現了也遲遲不處罰,顯然會大大降低處罰的威懾力。
根據法律經濟學“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在交易所如此微小的懲罰力度和查處概率面前,違規者或者其他市場主體會做何選擇,當是不言而喻的了。當然,對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而言,公開譴責已與其上市地位掛鉤。如深交所《中小企業板股票暫停上市、終止上市特別規定》第三條規:“公司受到本所公開譴責后,在二十四個月內再次受到本所公開譴責,對其股票交易實行退市風險警示”。第十一條規定:因這一情形“股票交易被實行退市風險警示的,公司在其后十二個月內再次受到本所公開譴責的,暫停其股票上市”。第十七條規定:“因這一情形“被暫停上市的,其后十二個月內再次受到本所公開譴責的,終止其股票上市”。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但現實中要滿足在特定期限內再次或者第三次受到同種處分當也是小概率的事件,再笨的公司也會盡力規避。
當然,除了前述無關痛癢之通報批評和公開譴責外,交易所還有暫停或者終止上市等嚴厲的處分措施。特別是終止上市,對上市公司是致命的打擊,但問題是交易所在對上市公司實施這種致命打擊的同時,覆巢之下無有完卵,購買該公司股票的投資者的利益也將遭受巨大損失。所以現實中,交易所難免投鼠忌器,不敢輕易使用這一手段。
可見,目前交易所的紀律處分措施存在斷層,即要么是無關痛癢的批評與譴責,要么是剝奪資格的致命打擊,中間少了介于兩者之間的金錢處分。從目前世界各國交易所的自律監管措施來看,大多采用了罰款(或違約金)這種處罰措施,而且在實際的案例中,罰款(或違約金)是最常見的處分措施。違規者之所以違規,其終極目的不外乎是利益,因此對其處以與其違規行為相適應的金錢處罰應是最有針對性也最有實際效果的懲罰措施,而且這一懲罰措施可以與通報批評和公開譴責并用。
好的制度必須讓違規者付出足夠的代價,證券市場發展20多年來,我們有了很多的法規、制度,但顯然還不夠好。就算有好的法規和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和制度的生命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