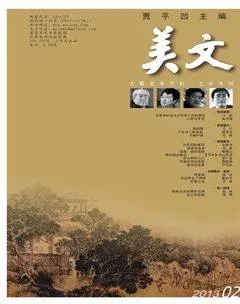擁有歷史圖景的視界

初聞范老,與自己閱讀沈從文的體驗(yàn)有關(guān)。當(dāng)時(shí)隱約知道他是國(guó)畫(huà)大師,不過(guò)對(duì)他的生平事跡未做進(jìn)一步的考究。如今,范老古稀之年仍熱情地出現(xiàn)在公眾面前,或以國(guó)畫(huà)、書(shū)法與詩(shī)詞之美好,或以藝術(shù)、人生與愛(ài)國(guó)之覺(jué)悟,或以古典、自然與儒學(xué)之對(duì)話(huà),諄諄告誡于我們。更難能可貴的是,范老還通過(guò)畫(huà)展、文化演講以及畫(huà)作等途徑,擔(dān)任起了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使者。為此,范老不但先后得到法國(guó)領(lǐng)導(dǎo)人薩科齊、奧朗德等的高度贊賞,還和戴高樂(lè)將軍的愛(ài)子菲利普·戴高樂(lè)有過(guò)書(shū)信往來(lái)。早在2011年12月7日的《新華副刊》上,我就看到了范曾先生所作戴高樂(lè)將軍像那張珍貴的畫(huà)。我清楚地記得,范老在《準(zhǔn)將的肩章》文末特別附錄了書(shū)信全文。
《準(zhǔn)將的肩章》把我們引入了1940年代硝煙彌漫的歐洲戰(zhàn)場(chǎng)——那片看似熟悉的歷史場(chǎng)景中,把我們的目光定格在那位“心中只有‘法蘭西’三字,而置自己生死于度外的偉大人物”,“絲毫不在乎自己的準(zhǔn)將軍銜”的戴高樂(lè)身上。“戰(zhàn)爭(zhēng)是離不開(kāi)火焰的,烈火中可以飛出鳳凰,也會(huì)燒焦了烏鴉”,我們從五個(gè)場(chǎng)景中不僅看到了戴高樂(lè)將軍對(duì)自由法蘭西民族尊嚴(yán)的維護(hù),還體味了他“澹泊寡欲、不務(wù)浮名”所彰顯的人性的光潔。特別是戴高樂(lè)故去十八年前的那封信函的內(nèi)容,讓我想起了茨威格在《世間最美麗的墳?zāi)埂?928年的一次俄國(guó)旅行》一文中描述過(guò)自己瞻仰托爾斯泰墓時(shí)的感受:“保護(hù)列夫·托爾斯泰得以安息的沒(méi)有任何別的東西,唯有人們的敬意”,“逼人的樸素禁錮住任何一種觀(guān)賞的閑情,并且不容許你大聲說(shuō)話(huà)。”托爾斯泰墓如此,范老眼中的戴高樂(lè)墓地亦如此。
這些天,由馮小剛導(dǎo)演、劉震云編劇的《一九四二》正在熱映。我覺(jué)得,影片也好,劉震云小說(shuō)《溫故一九四二》也罷,在講到“人與世界的和解”這一主題的背后,有著自覺(jué)的世界歷史圖景的視界。當(dāng)時(shí)間定格在1942年,不僅僅有河南省的大饑荒,也有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fǎng)美和丘吉爾感冒等事件,盡管其間少不了劉震云一貫的調(diào)侃或者揶揄。而我感觸很深的是,我們的歷史課堂教育改革迫在眉睫。哈耶克說(shuō),“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將把我們引向何處,并不是某一黨派的問(wèn)題,而是我們每一個(gè)人的問(wèn)題,是一個(gè)有著最重大意義的問(wèn)題”。在認(rèn)知自然的同時(shí),我們要擁有歷史圖景的視界。雖然我們的歷史傳統(tǒng)還音調(diào)未定,但對(duì)歷史的細(xì)部、尤其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lái)遭遇的恥辱要有個(gè)清醒的認(rèn)識(shí):如何理解近代中國(guó)歷史在思想層面的轉(zhuǎn)折——從匍匐的奴隸到“起來(lái),不愿做奴隸的人們”的中國(guó)人。這也是澳洲學(xué)者費(fèi)約翰《喚醒中國(guó)》那本思辨性著作給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只有這樣,知恥后勇的我們才會(huì)更明白維護(hù)民族尊嚴(yán)的可貴。
末尾,借用范老二十一年前贈(zèng)送給蕭瀚的一首七絕作結(jié):“畫(huà)到煙霞迷惘處,人間碧落兩勾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