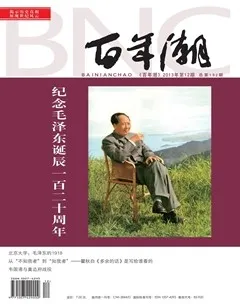北京大學:毛澤東的1918
1918年8月15日,青年毛澤東為新民學會赴法勤工儉學的事,由長沙乘火車赴北京,這是他第一次走出湖南的長途之旅。他沒有去法國,而選擇留在北京。10月,經恩師楊昌濟的介紹,他被安排到北京大學圖書館當新聞紙閱覽室書記。在北大不到半年的時光,毛澤東讀了很多書刊,接觸了很多的人和事,這個過程和影響,一直深植于他的記憶之中。
優秀的師范生
1913年春,毛澤東被湖南第四師范錄取,師范學校為五年制。次年春,第四師范合并入第一師范。第四師范是春季開學,而第一師范是秋季開學,毛澤東重讀了半年預科,到1918年暑期畢業,他實際成為讀了五年半的師范生。在這所學校里,對他影響至深的教員有楊昌濟、徐特立、袁仲謙、黎錦熙、王季范、方維夏等,其中尤以楊昌濟的影響最大。楊先生教授教育學、倫理學等。楊先生對這位農家子弟尤感興趣,他曾在日記中寫道:“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才,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楊先生期望不可謂不高,希望毛澤東像曾國藩、梁啟超一樣出類拔萃、大才槃槃。僅比毛澤東年長三歲的黎錦熙和毛澤東來往密切,相交于師友之間,在讀過毛澤東的日記后,他寫道:“在潤之處觀其日記,甚切實,文理優于章甫(陳章甫,毛的同學故友),篤行兩人略同,皆可大造。”
劇烈動蕩的社會呼喚“大造”之才,而毛澤東也正以極大的責任心,關注著變幻的政治風云。袁世凱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消息傳來,一師學生編印《明恥篇》小冊子,毛澤東在封面寫下:“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他還在挽學友的詩中寫道:“我懷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蓓,愿言試長劍;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蕩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那種對民族危難的沉重憂患,那種以雪恥救亡為己任的情懷抱負,已是溢于字里行間,躍然紙上。更令人稱奇的是,他在給蕭子升的信中就警告:中日之間“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而國人尤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后來的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果然應驗了這一石破天驚、防患未然的預言。
正是由于楊先生的介紹和推薦,《新青年》給毛澤東開啟了另一扇認識中國與世界的窗口。他對陳獨秀所說的“倫理的覺悟是吾人最后之覺悟”感觸極深,循著新文化運動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為此閱讀了許多哲學和倫理學的著作,而興趣最大的是倫理學,他認為,“倫理學是規定人生目的及達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學”。之所以如此認識,是因為他覺得“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而要改變這種狀態,就必須“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
“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一生酷愛游泳的毛澤東,不僅能在江河湖海中“勝似閑庭信步”,而且對改造中國與世界,充滿著“舍我其誰”的自信和“拿得定,見得透,事無不成”的意志。他一生之所以能最后成功,一師所奠定的自信心和意志力,是最為根本的基礎。他常對人說,好男兒要為天下奇,讀奇書,交奇友,做奇事,做個奇男子。同學們用諧音給他起名為“毛奇”,以歷史上普魯士的一名很有學問的將領毛奇相比喻。在一師的人物互選活動中,毛澤東在34名當選者中,得票最高,而在德、智、體三方面都有得票者,唯有毛澤東一人。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學會在蔡和森家正式成立,到會的有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何叔衡、蕭三、張昆弟、陳書農、鄒鼎丞、羅章龍等。這是五四時期最早的新型社團之一,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蕭子升為總干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干事。學會成立不久,蕭子升去了法國,會務便由毛澤東主持。1920年冬,由毛澤東撰寫的《新民學會會務報告》中提到:“會章系鼎丞、潤之起草,條文頗詳;子升不贊成將現在不見諸行事的條文加入,頗加刪削。”蕭子升“頗加刪削”的條文,恰是毛澤東所提激烈的政治主張。一激烈一溫和,這是兩位好友最終分道揚鑣的主要原因。
其實,毛澤東此時的思想信仰仍未確定,就是他所說“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但是我是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學會召開會議,認為留法勤工儉學很有必要,應該盡力進行,推舉蔡和森等“專負進行之責”。蔡和森到了北京后,給毛澤東來了一封信,十分同意毛澤東的新民學會的方針意見,信中說:“兄對于會務,本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實極表同情,且尤不諱忌嫌疑于政黨社會黨及諸清流所不敢為者之間。以為清流既無望,心地不純潔者又不可,吾輩不努力為之,尚讓何人去做?此區區之意,相與共照也。”“三年之內,必使我輩團體,成為中國之重心點。”他們真的做到了這一點,新民學會會員大多成了中共早期黨員,擔當起中國革命的重任。
楊昌濟此前已在北大哲學系任教,赴法勤工儉學的信息就是他傳遞回家鄉的,并讓一師的學生們積極準備赴法留學。這時的湖南政局混亂,政權更迭頻繁,教育已經摧殘殆盡,學生已至無學可求的境地。勤工儉學便是一條新的出路。蔡和森在北京忙碌之際,常去楊先生處。6月30日,蔡和森在致毛澤東的信中說:“兄事已與楊師詳切言之,師頗希望兄入北京大學。”北大校長蔡元培“正謀網羅海內人才”。“吾三人有進大學之必要,進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兄事”當指毛澤東正在長沙籌劃赴法勤工儉學的事,“吾三人”是指毛澤東、蔡和森與蕭子升。他們都是楊昌濟最看重的學生。楊昌濟希望毛澤東先“入北京大學”,以造學業和事業的“可大可久之基”。
在全國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中,湖南是報名最多的省份,毛澤東擔心大量人才外流,造成基礎教育薄弱,所以,他在致同學羅學瓚的信中說,同人已沒有幾個從事小學教育,“后路空虛,非計之得”。認為羅學瓚從事教育工作最適宜,不如留下從事教育。在安排給患病母親開一藥方后,毛澤東于8月15日離開長沙前往北京,途中因鐵路被大水沖斷,延至19日到達北京。“我正在尋找出路”
到了北京后,毛澤東忙碌著奔波著,幾經聯系,才落實好勤工儉學的事宜。大多青年因出國補習法語,陸陸續續進了預備班,沒有進預備班的也考入北大預科。楊先生希望毛澤東最好能在北大繼續讀書,可他卻沒有報考預科,其間不乏經濟的原因,亦不排除與他一向推崇自學的主張相關。這里還有一個客觀存在的原因,那就是當時教育部規定,中等師范生畢業后,必須先工作幾年后,才能報考大學。現今這一愿望已然落空,他便作另外的努力,據蕭子升回憶,由于“蔡(元培)校長幫忙的緣故”,圖書館長“李大釗安排毛澤東干打掃圖書館、整理圖書等輕便工作”。他說:“毛澤東對蔡孑民校長一直非常感激。寫給他的每封信都以‘蔡夫子大人’開頭。他認為自己是蔡校長的學生,永遠對蔡校長表示尊敬。1938
原北京大學校址——沙灘紅樓年,蔡孑民先生隱居九龍,在他逝世前12月左右,我常到他家促膝而談。有幾次我們談起毛澤東。以蔡先生的高齡,自然他不能記住一切。蔡先生還能記得毛澤東給他寫信,但想不起毛澤東的音容笑貌了。”
毛澤東最初住在楊昌濟家,其他會員分住在湖南會館。由于分散居住,聯系起來十分不便。不久,毛澤東與蔡和森、蕭子升、羅章龍等八人搬到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八個人擠住在一間小屋里,白天還好,一到晚上,大家擠在一個炕上,擠得幾乎都透不過氣。如果實在熬不住要翻身,必須要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否則根本翻不過來。毛澤東是帶著抱負和求知欲來到北京的,在他的眼中,這點兒困難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說:“在公園里和故宮廣場上,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當北海仍然結著冰的時候,我看到白梅花開。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雪后披上冬裝的樹木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嘆和贊美。”
來京的新民學會會員中,毛澤東當屬最窘困者之一。蕭子升說:“毛澤東幾乎一無所有,雖然路費(往法國)已減少到一百大洋,但這對他仍是無法解決的大數目,而且他自己知道,無人能借這筆錢給他。”毛澤東自己也說:“北京的生活費用對我來說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的錢來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馬上找工作不行。”有了這份工作,“我每月可以領到一大筆錢——八塊大洋。”這固定的經濟收入,對他來說顯得尤為重要,因為由此奠定了他在北京的生活,故而分外珍惜,怎會像有的文章所說的那樣,不切實際地與“那時北大的名教授的工資高者300元”相比,而“感到屈辱”呢?
毛澤東的頂頭上司李大釗對他的影響最為直接。可有文章說:“1918年,張申府曾是北大圖書館的代理館長(關于張是否是代理館長一事,還有另外的說法),正是臨時工毛澤東的頂頭上司。”又說:毛澤東“用那種龍飛鳳舞、潦草的,并沒有多少根基的草體字書寫圖書卡片,顯然是很不合適的。”因此,受到代理館長張申府的訓斥,毛澤東“恨聲不絕”,“自尊心受到了嚴重的傷害”。1957年,張申府之所以被打成右派,“當然都與當年給毛‘受氣’有關”。
張申府是否曾任北大圖書館代理館長,就是這位作者也以為“還有另外的說法”。毛澤東在延安接受斯諾采訪時,已經說得十分明白,他說:“我從前在師范學校的倫理學教師當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的主任。這個人就是李大釗,他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蕭子升對這件事的敘述,就更為詳盡。他說,他們原打算讓毛澤東去做教室清潔員,因為,那樣可以在工作之余,免費旁聽。后來,是蔡元培改變了毛澤東的工作,蕭子升說:“蔡校長是位可敬的人,立即了解了我們的困難。他有個更好的主意:與其做個教室清潔員,不如安排毛澤東在圖書館工作。因此他寫了張條子給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先生:‘毛澤東為實行勤工儉學計劃想在校內工作,請將他安排在圖書館中……’蔡校長沒有指出毛澤東是由長沙來的,是‘青年領袖’。李大釗安排毛澤東干打掃圖書館、整理圖書等輕便工作。”又說,1924年至1926年間,蕭子升與李大釗曾在一次會面中舊事重提,“我們談到過毛澤東,有一次李大釗說:‘我叫毛澤東做清潔工作,完全是遵守蔡校長的指示。我并不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希望你能原諒我。’”當事人毛澤東和蕭子升的回憶,都已經表明毛澤東的頂頭上司是李大釗,而并非張申府。
說到毛澤東用草書填寫圖書卡片,那更是站不住腳,稍有書法知識的人都知道,草書寫起來是筆畫連綿,飛鳥驚蛇,小小的圖書卡片怎么也不能以草書填寫,這是常識。十分珍惜這一工作的毛澤東,怎么可能冒著丟“飯碗”的風險,而任意在上面用草書填寫,況且也無法書寫。毛澤東的草書是中老年后才人佳境,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寫得一手工整雋秀的楷書,他在一師時所作的讀書眉批,他給表兄文詠昌的還書便條,便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明。
毛澤東的工作問題落實了,他再也不用為生活發愁了,除專心于工作之外,對學業和人生的思索仍在追尋之中。他和新民學會在京會員,曾邀請蔡元培、陶孟和、胡適分別在北大文科大樓談話,所談多是學術和人生問題,對他們很有啟迪。
五四運動前后,西方的各種主義如潮涌來,毛澤東在圖書館工作,當然最先感知,他憑著一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熾熱的心,苦苦尋覓著救國之路。他說:“當時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用我們的話說,我正在尋找出路。我讀了一些關于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來看我的、名叫朱謙之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當時,我贊同無政府主義的很多主張。”
和邵飄萍、梁漱溟、周作人的交往
毛澤東在北大時,和邵飄萍、梁漱溟、周作人都有過一段交往。聽過邵飄萍、梁漱溟的課,交往的時間頗長。因討教新村主義而拜訪過周作人,可謂一面之緣。然而,無論交往的長短,毛澤東都沒有忘記他們。在談起北大往事時,他曾深情地說:“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的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18年,邵飄萍在北京創辦《京報》和新聞編譯社,并在北大講授新聞學。當時,北大成立了新聞學研究會,毛澤東是會員之一,邵飄萍常到學會講課,傳授辦報的業務知識。毛澤東除了在課堂聽邵先生講課外,還常去邵先生家討教,據邵飄萍夫人回憶:“那時,毛主席是北大職員,平易近人,到我家里來,很有禮貌,叫飄萍為先生,叫俺邵師娘。”
后來,毛澤東回長沙創辦《湘江評論》,邵飄萍所傳授的知識,給了他不少的幫助。毛澤東對邵飄萍的半年授課之恩,一直懷念在心。1926年4月26日,邵飄萍被軍閥殺害。毛澤東知道后,十分惋惜。1949年4月,毛澤東親自批文追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他對這段短暫的師生關系,極為珍惜,就是到了晚年,他仍稱“我是邵飄萍的學生”。
毛澤東雖然沒有上北大,但他是新聞學會和哲學會會員,由此而旁聽了邵飄萍和梁漱溟的課。他和梁漱溟是同齡人,只是在月份上,梁漱溟長毛澤東兩個多月。梁漱溟與楊昌濟同在哲學系任教,經常來楊家,多次為梁漱溟開門的都是毛澤東,他們開始有交往而熟悉起來。1938年,梁漱溟為積極奔走全民抗戰,來到延安。他單獨與毛澤東進行八次談話,其中兩次徹夜長談,使梁漱溟對共產黨,對毛澤東本人有了深刻的印象。
毛澤東來北大之前,作為湖南一師的學生,曾信奉過新村主義。到北大后,他理應去拜訪中國新村主義最積極的倡導者周作人,可卻不見這方面的記載,想必周作人教務繁忙,而毛澤東又因圖書館的本職工作,兼之為新民學會會員勤工儉學,事務性的工作太多,而沒有時間去拜訪周作人。他們之間的直接接觸發生在1920年4月7日,周作人的當天日記:“毛澤東君來訪。”此前,周作人已經辦起所謂新村支部,并在《新青年》發布啟事:“凡有關于新村的各種事務,均請直接通信接洽。”
早在1918年春,毛澤東就邀了幾個朋友,在岳麓山設工讀同志會,從事半耕半讀,雖然收效不大,可他仍很向往。1919年12月,毛澤東率湖南驅逐張敬堯請愿團來到北京。他的日程安排得滿滿的,不是起草驅張的文稿,就是往駐京的各大報館送驅張的文電,再不就是往各大衙門請愿。往八道灣拜訪周作人的事,一直拖到次年4月7日。他和周作人會面具體談了什么,看來已成為永遠的謎,但有一點是應該肯定的,那就是他們都會談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新村主義。
抗戰期間,日軍占領北平,周作人淪為文化漢奸。但在此期間,他曾盡力保護過好友李大釗的兒女們。在護送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兒子李光華離開北平前往延安時,周作人特意告訴李星華:“延安我不認識什么人,只認識一個毛潤之,請你給他帶好。”
抗戰勝利后,周作人以漢奸罪被捕并服刑。1949年1月,他被保釋出獄后一直住在上海。新中國成立后,他日夜思念回到北京,便給毛澤東、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發出后便在深深地期待著。他對朋友說:“南北通車了,我已經發出一書信給毛潤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當圖書館館員時見過面。有一次,他來八道灣看魯迅,魯迅不在家,同我談了一會兒。我去信問他能不能讓我回北京,還不知道給不給回音。”
周恩來接信后,立即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看罷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后出版。”不久,周作人得到可以回北京的消息,他高興地告訴友人:“回音果然來了,是毛先生請周恩來寫給我的,允許我回家。”回京后,周作人重新入住八道灣,在周揚、馮雪峰的安排下,人民文學出版社買下他的全部譯稿,每月支付200元,這在當時應是一筆不菲的收入,待書稿全部出版后,稿費再重新結算。周作人自然清楚這一切得益于毛澤東,原想給毛澤東去一信,可“因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驚動”,遲遲地就一直沒有去信。
“劉項原來不讀書”
毛澤東零距離地接觸陳獨秀,當然是在北大。他說:“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北京。當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大。”又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我在這方面發生興趣,陳獨秀也有幫助。”
1920年6月,毛澤東第二次來到上海,他特意拜訪陳獨秀,他說:“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盡管他們后來道不同,但是毛澤東就個人情感上,一直沒有忘記陳獨秀。全面抗戰爆發后,陳獨秀獲釋出獄,并重提與中共中央合作抗戰的事情。中共中央立即以張聞天、毛澤東的名義作出“我們對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則”,其精神實質是要陳獨秀等承認托派的錯誤,即可重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恰在此時,王明回到延安,極力阻止這一工作的進行。王明直至晚年對此還沾沾自喜地說:“由于我已回到延安,陳獨秀恢復黨籍的計劃才未實現。”
毛澤東沒有忘記自己的引路人,1942年3月30日,也就是陳獨秀逝世前兩個月,他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三年后,毛澤東再論陳獨秀,他說:陳獨秀雖然“有些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關于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在1959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再提陳獨秀,他說:“他后來去世,那個責任在我,我沒有把他接來。”顯而易見,毛澤東為此仍在深深自責之中。
毛澤東作為新民學會赴法勤工儉學的組織者之一,自己卻沒有出國,這其中的理由當然如他跟斯諾說:“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了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據毛澤東致周世釗信說,他曾為此討教胡適、黎錦熙,“他們都以為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并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毛澤東虛心好學,奉胡適為“楷模”,胡適又待人熱情,好為人師,而且他們又年齡相仿,他們之間定有一段亦師亦友的交往。
毛澤東回到長沙創辦了《湘江評論》,這引起了胡適的注意,而毛澤東所寫《民眾的大聯合》,更讓胡適拍手叫好,他在《每周評論》發表文章,稱贊《民眾的大聯合》,“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稱贊《湘江評論》道,“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出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1919年12月,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曾和幾個新民學會會員拜訪胡適,并留下一封信。回到長沙后,毛澤東還給胡適寄份明信片說:“將來湖南有多點借重先生之處。”在此之前,毛澤東經過上海時,曾給胡適去信一封。1921年9月,毛澤東創辦湖南自修大學。1951年5月17日,胡適在閱讀胡華所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中關于湖南自修大學的內容后,于當日日記中寫道:
毛澤東依據了我在一九二零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
在胡適的眼中,毛澤東就是他的學生。抗戰勝利后,他致書毛澤東,希望“中共領袖諸公……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胡適太天真了,中國共產黨前赴后繼英勇犧牲所創立的軍隊,所開辟的根據地,怎么能拱手讓于他人,而蔣介石“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獨裁體制,又怎么能容忍中共作為“第二大政黨”存在呢?如此不合時宜的話語,真所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毛澤東很期望與大學生多有交往,可事與愿違。毛澤東對斯諾說:“由于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愿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這件事當然使毛澤東刻骨銘心,他所說“不把我當人看待”,當有言過其實之處,不過有一點卻是事實,作為全國最高學府——北大學生,“他們大多數”也免不了輕視勞動者的毛病,這些“天之驕子”怎能俯身與圖書館助理員,一個月只有八塊大洋的下等人,“交談政治和文化”呢,況且,所講又是難以聽懂的“南方土話”。這之后,天各一方,急景流年,北大學生們怎么也沒有想到,當年那個講“南方土話”的圖書館工作人員,20多年后,竟會成就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
1945年7月1日,抗戰勝利在即,傅斯年作為六名國民參政員之一乘飛機訪問延安。毛澤東單獨安排時間,與傅斯年徹夜長談。同當年北大相比,時間和場景都有了轉換,可毛澤東依然不失他鄉遇故知的情懷和禮賢學人的雅量。談話中,自然談到北大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談到傅斯年等五四運動風云人物。聽到談及自己,傅斯年謙遜地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第二天也就是7月5日,毛澤東給傅斯年寫了封信,上寫道:“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這便是章碣的《焚書坑》,毛澤東以條幅書寫,以贈傅斯年。詩云: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毛澤東為什么給傅斯年書寫《焚書坑》,時下有著很多解。筆者以為毛澤東之所以書寫這首唐詩,是針對傅斯年所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而抒發,毛澤東以“劉項原來不讀書”回應,其間含有自謙自況之意,即與傅相比,不是讀書太多的知識分子,抑或有別的什么寓意,已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編輯姚建萍)
(作者是安徽省地方志部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