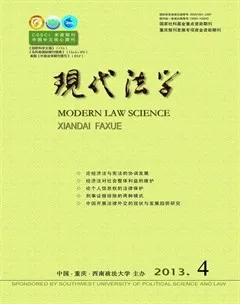論國際投資條約中的金融審慎例外安排
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生的多次金融危機,包括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使人們日益意識到有必要在投資條約中明確東道國的金融規制權。在這方面,美國、加拿大的雙邊投資協定(BIT)范本對金融審慎例外的安排具有代表性,已經被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投資條約所借鑒。然而,無論從締約實踐還是爭端解決的角度,既有的金融審慎例外條款都還只是初步的,有必要進一步加以完善。中國應當在借鑒域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本國具體情況設計恰當、合理的金融審慎例外安排。
關鍵詞:投資條約;金融審慎例外;爭端解決
中圖分類號:DF964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3.04.14
金融審慎措施的基本含義是指基于審慎原因所采取或維持的合理措施,包括:(1)保護存款人、金融市場參與者和投資者、投保人、索賠人或金融機構對其負有信托責任的人的措施;(2)維護金融機構的安全、穩健、完整或其財務責任的措施;(3)確保締約方金融體系完整性和穩定性的措施。這種措施始于國際貿易體制對于金融服務的規制,典型的實踐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第14章(金融服務)和《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的金融服務附件。從投資條約的角度看,美國2004年BIT范本和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率先在雙邊投資協定中引入專門的金融審慎例外安排,這一作法逐步影響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締約實踐,構成國際投資法的一個最新發展。
一、在投資條約中納入金融審慎例外安排的基本背景(一)金融審慎例外安排產生的一般背景
應該承認,金融審慎例外對于美國而言并不陌生,長期以來,美國政府一直尋求將服務業納入多邊條約框架,以適應其在國際貿易中比較優勢的轉換趨勢,即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業的比較優勢日益轉向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的優勢則轉移到新興工業國家,而發達國家仍然具有重要比較優勢的知識型或高科技型產業和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卻被長期排除在多邊框架外。作為一項自由化程度極高的區域性貿易協定,NAFTA把傳統上被認為涉及國家主權最敏感領域之一的金融服務貿易納入規制范圍,部分實現了美國的政策目標,推動了金融市場的開放[1]。其中,NAFTA第14章規定了金融服務的相關規則,不僅包含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基本原則,甚至涉及金融機構的設立、行業協會、金融機構監管等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致力于金融領域的自由化,NAFTA第14章還是規定了金融審慎例外,這一作法同時影響到《服務貿易總協定》金融服務附件第2.1條的規定。
由于NAFTA第14章關于提供金融服務的方式之一為“商業存在”,因此,該章實際上已經包含了投資規則。然而,NAFTA專門規制投資問題的第11章卻未出現金融審慎例外安排,并且外國投資者在金融領域設立“商業存在”的行為及其經營也非適用第11章的規定,從這個意義上說,NAFTA投資體制對金融審慎例外的規定并不充分,而事實上這也是美國、加拿大在投資自由化驅動下的必然選擇。但是,此后不斷發生的金融危機以及阿根廷政府被外國投資者頻頻訴諸國際仲裁的慘痛經歷,促使一些國家意識到,有必要將金融審慎例外安排引入國際投資條約,以便在投資(包括金融服務投資)自由化進程中維護東道國正當的規制權。在此情況下,極力鼓吹投資自由化但同時極為注重維護本國主權的美國,以及在NAFTA體制內頻頻被美國投資者訴諸國際仲裁的加拿大及時地“改弦易張”截至2011年12月,美國被訴14次,成為全球第十大被訴國,而加拿大被訴17次,是全球第六大被訴國。(參見:UNCTAD. Latest Development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J].IIA Moniter,2012,(1):17.) ,在投資條約中率先規定金融審慎例外。
(二)金融審慎例外安排產生的特殊背景
傳統的國際投資條約并未包含專門的金融審慎例外安排。在晚近國際投資仲裁實踐尤其是阿根廷應對2001年經濟危機誘發的大規模投資仲裁案件中,被訴東道國通常援引根本安全例外條款作為金融管制措施的抗辯。例如,Continent公司案的仲裁申請人認為,阿根廷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限制匯出、重新安排現金存款、美元存款比索化等,損害了其在阿根廷的投資權益。針對這一指控,阿根廷提出的基本抗辯依據是1991年美國—阿根廷BIT第11條,即根本安全例外條款。該條規定:“本條約不排除任何一方為維持公共秩序采取的措施,為履行與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有關的義務,或保護自身根本安全利益所采取的措施。”阿根廷據此認為,根據該條規定,應完全或部分免除針對所指控的違反條約義務行為承擔的賠償責任。ICSID仲裁庭最終接受了阿根廷的抗辯,其基本的裁判邏輯是:對根本安全利益應采取廣泛界定的作法,它不僅涉及地理、戰略以及國防的利益,還包括締約方在面對社會、政治、嚴重經濟危機時所采取的確保國家安全的措施。參見:Continental Casualty Company (Claimant) v. Argentine Republic(Respondent),ICSID Case No. ARB/03/9(2008),paras. 162-165.然而,東道國援引根本安全例外條款經常受到制約,主要原因有二:
現代法學陳欣:論國際投資條約中的金融審慎例外安排第一,總體而言,投資仲裁庭對于根本安全例外條款采取嚴格解釋的方法,從而導致在類似案件中出現截然不同的裁決結果[2]。例如,在涉及阿根廷的一系列投資仲裁案中,雖然仲裁庭普遍同意根本安全例外包含經濟緊急情況,但緊急情況要達到何種程度才可以使東道國免責,不同仲裁庭的裁決意見并不一致。一些仲裁庭甚至將根本安全例外等同于習慣國際法中的危急情況,從而進一步限制了根本安全例外條款的適用范圍[3]。例如,CMS公司案、Enron公司案和Sempra公司案等案的仲裁庭即認為,雖然阿根廷面臨著嚴重危機,但危機尚未導致阿根廷經濟與社會崩潰,尚未危及到國家的存在,因而不能援引美國—阿根廷BIT第11條的規定。參見:CMS Gas Transmission Co. v. The Republic of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 /01 /8 ( 2005) ; Enron Corp. Ponderosa Assets v. The Republic of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 /01 /3 ( 2007) ; Sempra Energy International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 /02 /16(2007). 這3起案件后來都進入撤銷程序,CMS公司案的撤銷委員會認為,仲裁庭將根本安全例外條款的必要條件與習慣國際法中危急情況的必要條件相等同是錯誤的,但最終認定該裁決沒有明顯越權而未予撤銷。Enron公司案和Sempra公司案的撤銷委員會都作出撤銷裁決的裁定,理由是仲裁庭未適用根本安全例外,由于沒有正確適用法律,已構成明顯越權。
第二,根本安全例外主要針對特定的、極其嚴重的國家安全事件或情勢,這一點是國際投資仲裁庭共同承認的。換言之,根本安全例外條款適用十分嚴格的標準。然而,這與東道國在投資自由化進程不斷深化,尤其是在金融服務成為日益重要投資形態的背景下維護金融公共利益(如維護金融市場穩定)的客觀需要并不符合。有效地維護金融公共利益不僅要求東道國在出現嚴重金融事件或情勢時采取有力措施,也許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管理中通過審慎措施預防嚴重金融事件或情勢的發生。在這種情況下,適用根本安全例外顯然十分困難[4]。與此不同,NAFTA以及GATS的實踐表明構成金融審慎例外的條件要比根本安全例外寬松。在金融審慎例外中,通常采取的措辭是“為保護…”,而非根本安全例外中的“必需”、“必要”等。對于后者,只要存在一種可行的替代性措施比現有措施更有助于實現目標,現有措施就會被認為不符合必需要件;對于前者,即使存在更優的替代性措施,但只要現有措施滿足最低標準,仍有可能符合金融審慎例外的要件。,相關措施只需滿足最低標準,仍有可能被認定為構成金融審慎例外。
二、投資條約中金融審慎例外安排的實體內容(一)主要內容
與1994年BIT范本未針對金融領域的投資制定專門的規則不同,美國2004年BIT范本增加了金融審慎例外安排,并在2012年BIT范本中延續了這一作法。美國2004年和2012年BIT范本采用的共同模式,是把審慎例外安排規定在金融服務條款中,進而規定特殊的爭端解決方式、嚴格的透明度要求等。然而,該模式導致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當東道國所采取的金融審慎措施影響到非金融領域投資時,東道國政府能否援引金融審慎例外作為抗辯。這種將審慎例外安排納入或局限于金融服務的作法,反映了美國政府對于賦予東道國寬泛的金融規制權的顧慮,以及擁有強大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跨國公司、商業組織在BIT范本修改過程中表達出來的反對態度,因此其安排未必是充分合理的。美國國際經濟政策委員會投資分會在美國2004年BIT范本頒布前的評論中表明了這一點,該機構指出,它的一些成員認為:“金融領域應承擔與其他領域相同的BIT項下的義務,審慎例外安排會成為締約方政府違反條約義務的保護傘,從而導致美國投資者承擔巨大的風險。”[5]與美國的作法不同,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將金融審慎例外規定于一般例外中參見: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第10.2條。,允許締約方基于審慎原因采取或維持合理措施,據此,金融審慎例外被延伸到非金融領域。其結果是,在相關金融審慎措施(如適用于宏觀經濟的金融調控措施)影響到非金融市場投資者利益的情況下,只要它們滿足金融審慎例外的構成要件,就不會被視為成員方違背依協定本應承擔的義務或責任。
加拿大BIT范本的另一個重要特色,是將金融審慎例外適用到資本匯兌與轉移條款。從傳統來看,投資條約中的資本匯兌與轉移條款旨在平衡兩個目標:一是賦予投資者與投資相關的資金可以自由輸出入的權利;二是賦予東道國一定的靈活性,推行其貨幣和財政政策。就目前而言,絕大多數投資條約中的資本匯兌與轉移條款只強調“締約方應當允許所有與合格投資有關的資金自由、迅速地匯入或匯出其境內”,“允許以按照市場最高價換算出的自由使用貨幣形式進行轉移”參見:美國2004年BIT范本、2012年BIT范本第7條。,但沒有包含用于處理嚴重國際收支失衡及其他情況的例外條款。其原因可能在于,締約方并不認為限制轉移是處理國際儲備短缺的最佳選擇,相反,在發生危機時,對國際轉移進行限制反而會加重投資者的焦慮情緒,從而想方設法去規避這些限制。美國2004年和2012年BIT范本甚至強調,金融服務(顯然包含金融審慎例外)不影響締約方在“資本轉移”和“實績要求”項下的義務。參見:美國2004年BTI范本、2012年BIT范本第20.2條。
但是,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使情況發生了變化,一些學者和政府官員曾經建議,投資條約應當對資本自由匯兌與轉移施加限制。例如,Anderson指出,美國BIT范本中的相關規定已經過時,嚴重制約了政府推行維護國家金融體系穩定的政策或導致這些政策的實施不夠充分……事實證明,控制資本流動是避免投機資本泡沫和恐慌性資本外流的極少數有效工具之一[6]。作為效力于美國政府的政策研究中心全球經濟項目主任,Anderson的建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又如,美國國務院咨詢委員會的報告援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員的觀點認為,資本項目流動的暫時限制對于防范和緩和金融危機是必要的,而短期資本輸出入的規制尤其如此[7]。遺憾的是,可能受到著力推動并維護投資自由化的商業界的影響,這些建議在美國2012年BIT范本中并未獲得采納。與美國躑躅不前的情形不同,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已經對金融機構的資本匯兌與轉移作出明確的規制。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第14.6條規定,為了保護金融機構的安全、穩定、完整及其支付能力,締約方可以禁止或限制某一金融機構將資金轉移給其分支機構或者與該機構相關的人,但該措施的適用必須是公平的、非歧視的以及善意的。
(二)晚近采取金融審慎措施可能誘發的投資爭端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后,傳統上奉投資自由化為圭臬的發達國家頻頻以保護公共利益為由采取一些非常態的管制措施,這種情況在金融領域尤為突出。布雷頓項目組織(Bretton Woods Project)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可能導致國際投資仲裁中申請人和被申請人的結構出現轉向,即來自于南方國家的投資者更有可能對發達國家政府提出仲裁指控[8]。Aaken和Kurtz也認為,由于政府在救助危機時采取的策略和措施,與其他國際經濟法領域相比,短期內國際投資法領域更容易產生法律訴訟。其原因主要在于,國際投資法中涉及金融審慎例外的內容顯然比國際貿易法如WTO規則更為寬泛。同時,與WTO的爭端解決在政府與政府之間進行,容易引起針對對方同類型措施的報復性訴訟或貿易報復不同,國際投資領域允許私人投資者發起投資者—國家間的仲裁程序,從而弱化了政府間爭端解決的政治考量。(參見:Anne van Aaken,Jürgen Kurtz.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G]// Simon Evenett,Bernard Hoekman.Trade Implications of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risis.Washington:World Bank Publication,2009:9-10.)它們主要包括政府在發生危機時的政策介入,比如對流動性的支持、購買銀行資產、對銀行間同業借款的支持以及給予零售銀行的存款擔保等。由于這些救助措施一般只適用于國內金融機構,而外國投資者不能享受到同等的非歧視待遇,因此大多存在隱性投資保護主義的傾向[9]。例如,美國《2008年緊急經濟穩定法案》授權財政部通過“問題資產解救方案”(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收購問題住房抵押貸款和其他資產,其救助的對象限定為在美國有“重要經營”(significant operations)的金融機構。雖然該方案并未排除外國銀行受惠于美國救市計劃的可能,但實際上美國的國內銀行占據了絕大多數。
誠然,由于美國政府采取的救助措施多采用“補貼或津貼包括政府支持的貸款、擔保和保險”的方式,它們屬于美國2004年或2012年BIT范本第14.5條規定的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豁免范圍,因而外國投資者難以根據國民待遇或最惠國待遇條款獲得補償。并且,由于政府針對金融市場的救市政策通常因勢而動,不斷調整,要界定這些措施的性質并非易事。但是,第14.5條并未提及公平和公正待遇,因此,投資者仍然有可能以未獲得與美國銀行相同的救助計劃為由,根據公平和公正待遇條款提出指控。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已經出現過類似措施引發的投資仲裁案件。比如,Saluka案仲裁庭認為,捷克政府在處理銀行業的壞賬問題時,不能提供合理的理由證明為什么對日本銀行在荷蘭的子公司給予差別待遇。捷克本國的四家大型銀行在面對壞賬問題時處于類似的情況,投資者存在合理的預期,認為救助計劃也會涵蓋Saluka公司,但捷克政府的作法顯然讓投資者的合理預期落空。參見:Saluka Investments BV v. The Czech Republic,UNCITRAL,Award (Mar. 17,2006).
三、金融審慎例外爭端解決的特殊程序安排 在WTO體制下,涉及金融服務的爭端只能通過WTO成員方之間的爭端解決機制加以解決。與此不同,20世紀90年代后締結的國際投資條約普遍規定了投資者—國家間仲裁機制,據此,投資者往往可以不受國家(東道國和母國)限制直接訴諸該機制。對于傳統上僅適用于當地救濟的金融服務來說,這是一個重大發展,但同時也給主權國家尤其是東道國帶來嚴峻的挑戰。對此,無論是NAFTA還是此后的美國、加拿大BIT范本,一方面規定了投資條約中通常采用的投資者—國家間仲裁和國家間仲裁程序,另一方面則借鑒了在維護東道國主權時同樣敏感的稅收措施的處理模式,即將締約方之間主管部門的協商作為爭端解決的主要方式之一。例如,以強調獨立裁判和承認投資者訴權著稱的NAFTA,對金融審慎例外設置了特殊的由金融服務主管部門磋商的規則,并承認它們的共同決定對仲裁庭具有約束力。更早一些的《美國—加拿大自由貿易協定》甚至排除適用仲裁的方式,規定涉及金融服務的爭議只能由加拿大財政部和美國財政部通過協商加以解決。NAFTA第1415.2條,《美國—加拿大自由貿易協定》第1704條。(參見:Anna V. Morne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A Comparative Snapshot[J].Law & Business Review of the Americas,2001,(Fall):67-68).此后,無論是加拿大還是美國的BIT范本,涉及金融審慎例外的仲裁機制都既不同于一般的國際商事仲裁或公法意義上國家間的國際仲裁,也有別于ICSID體制下的投資者—國家仲裁機制。
例如,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第17條規定:當投資者向國際仲裁庭提出訴請而被訴方東道國以金融審慎措施和合理的阻止或限制資本轉移措施為由進行抗辯時,應先由締約雙方的金融主管部門進行磋商,在達成協議的基礎上,或通過另設國家間仲裁小組的方式,準備一份書面報告,該報告對仲裁庭具有約束力。仲裁庭在收到該份報告前,不得就前述條款能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對投資者的訴請構成有效抗辯作出審理。反之,如果仲裁庭在收到投資者訴請的70天內,既未收到兩國另設仲裁小組的請求也未收到來自兩國金融主管部門達成共識的書面報告,仲裁庭即可直接對前述問題進行審理和作出裁定。其中,承認主管部門間書面報告約束力的意義在于可以更好地反映締約方的真實意圖,避免由仲裁庭自行任意解釋條約而影響到締約方金融安全的情形發生,而時間上的限制則可避免僅由締約雙方協商出具報告時締約雙方的久拖不決。簡言之,仲裁庭對于投資者單方提出的東道國金融措施“不合法”侵權的訴請,享有較為直接的管轄權、審理權和裁決權,而不僅僅是主管部門協商程序的延伸[10]。
在投資者—國家間仲裁解決爭端方面,較之加拿大較為保守的作法,美國的締約實踐則顯得較為激進。事實上,美國2004年BIT范本頒布前的草案曾經規定,當雙方金融主管部門未能就金融審慎例外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作為有效辯護決定的情況下,被申請方可以請求設立國家間仲裁庭對金融主管部門的未決問題作出決定。但是,這一程序的設置遭到代表投資者利益的國內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他們抱怨認為,在仲裁庭作出裁決之前,首先是兩國主管部門的聯合決定,如果被訴國要求,還將進入沒有時間限制的國家間仲裁,這種冗長、重復的程序設置降低了仲裁效率[11]。由此導致的結果是,美國2004年和2012年BIT范本都規定,如果雙方金融主管部門在收到請求后120天內未能作出正式決定,仲裁庭應當認定該問題未能由締約雙方適格的金融主管部門解決,并適用投資者—國家仲裁的程序。同時,美國2012年BIT范本還設置了更嚴格的時間限制,該范本第20.3(e)條規定,如果兩國金融主管部門沒有作出聯合決定,仲裁庭應在30天內就主管部門的未決事項形成報告,以解決被申請方(東道國政府)是否能夠援引金融審慎例外的問題。由此可見,雖然美國BIT范本還保留著國家間仲裁程序,但它與投資者—國家仲裁是徹底分離的。這種模式維護了投資者在金融服務爭端解決中實質性的地位,從而降低了國家間仲裁對投資者保護的弱化,強調了投資者通過投資者—國家仲裁途徑尋求救濟的權利。
四、中國投資條約中的金融審慎例外安排及其完善目前,在投資條約中包含金融審慎例外安排已經成為國際投資法發展的重要趨勢,但對中國而言,這一安排顯然具有“雙刃劍”的作用。一方面,中國是傳統的投資輸入國,另一方面,中國正在向對外投資大國轉變。2011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160.11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到746.5億美元,其中金融類投資為60.7億美元。(參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 三部門發布《201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EB/OL].[2012-12-07].http://www.gov.cn/gzdt/2012-08/30/content_2213920.htm.)這種轉變同時意味著投資風險的增加,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頻頻發生的背景下,更是如此。例如,中國平安集團訴比利時政府案表明,中國的投資實踐實際上已經涉及金融審慎例外問題。作為首起中國內地企業訴諸ICSID解決投資爭端的案件,該案備受關注。2007年11月,平安保險集團斥資238.74億元購買富通銀行4.18%的股權,成為其第一大股東。但富通銀行因金融危機的影響而陷入困境,比利時政府通過對該公司進行國有化及變賣資產的方式提供援助,嚴重損害了股東的利益。作為第一大股東的平安保險集團最終累計計提損失達227.9億元,2012年9月,平安保險集團訴諸ICSID申請國際仲裁[12]。對此,比利時政府抗辯認為,在2008年富通集團面臨整體性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政府有責任及時采取措施保障該實體繼續經營,其購買富通銀行股權并將75%的股權轉售給巴黎銀行,是為了保障存款人和客戶的利益以及富通集團在比利時境內雇員的就業[13]。由于中國—比利時BIT(1984)中并無根本安全例外或金融審慎例外的規定2005年6月簽訂的中國—比利時BIT在發生國有化時還未生效,即便如此,2009年12月生效的中國—比利時BIT也未包含根本安全例外或一般例外條款。,比利時政府的法律依據主要是該行為屬于非補償性的管制措施而非間接征收。國際法上雖然承認非補償性政府管理措施的存在,但未對兩者的區分予以明確闡述,且仲裁庭在實踐中更傾向于關注這些措施對財產所有人產生的影響而忽視規制措施的目的[14]。
單就本案而言,中國—比利時BIT中沒有包含根本安全例外或金融審慎例外條款對中國企業可能是“因禍得福”,比利時政府無法以該措施的目的是維護國內金融市場、金融機構的穩定為由成功抗辯。盡管如此,從中國兼具重要資本輸入國與資本輸出國的雙重身份看來,我們沒有必要為此“歡呼雀躍”。例如,WTO爭端解決的統計數據表明,截至目前,涉及GATS金融服務附件的案件共有4例這4起案件分別是中國-影響金融信息服務和外國金融信息提供者的措施案(DS372,DS373,DS378),中國-影響電子支付措施案(DS413)。(參見:Disputes by Agreement[EB/OL].[2013-01-14].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agreements_index_e.htm?id=A8#selected_agreement.),全部指向中國,這也凸顯了中國將金融審慎例外安排作為金融領域(包括金融服務)開放安全閥的重要性。因此,在我國締結的國際投資條約中設計恰當、合理的金融審慎例外安排,將有利于維護我國的金融規制權,同時又避免過度限制或損害對外投資者的利益。
(一)實體性條款
就我國的締約實踐而言,除中國—哥倫比亞BIT(2008年12月簽訂)、中國—加拿大BIT(2012年9月簽訂)外,金融審慎例外安排還出現在《中國政府與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政府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之投資協議》(以下簡稱《中國—東盟國家投資協議》)、《中國政府、日本國政府及大韓民國政府關于促進、便利和保護投資的協定》(以下簡稱《中日韓投資協定》)、《海峽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等投資條約或協議中。
1.金融審慎例外
在設置金融審慎例外安排方面,我國簽署的投資條約并沒有遵循統一的模式,甚至對于是否將金融服務納入投資協議還存在著一定的顧慮,體現為相關條約或協議簽署時的語焉不詳。例如,《中國—東盟國家投資協議》第3.5條規定,投資待遇(公平和公正待遇)、征收、轉移和利潤匯回、損失的補償、代位和締約方與投資者間爭端解決,經必要修改后應適用通過商業存在提供的服務貿易。同時,該協議第16.2條針對金融服務,允許GATS金融服務附件第2款(國內規制)經必要調整后并入。但對于何為“必要調整”,至今都沒有明確界定。《海峽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既無專門的章節涉及金融服務,也未對金融服務的內容作出專門規定,卻在第2條(適用范圍和例外)第6款規定,一方可以基于審慎理由采取或維持與金融服務相關的措施。
此外,即使是明確地將金融審慎例外納入調整范圍的近期投資條約,其規定也不盡相同。中國—哥倫比亞BIT在第13條中明確指明“金融部門的審慎措施”,《中日韓投資條約》第20條的標題為“審慎措施”,但在具體內容上將其界定為“涉及金融服務的措施”,而中國—加拿大BIT則把金融審慎例外規定在一般例外中。本文認為,雖然將金融服務單列的方式有利于強調對金融服務納入投資條約保護范圍的重視,但較之中國—加拿大BIT而言,在具體適用時缺乏周延性,因為后者更有利于東道國政府利用金融審慎例外安排維護金融主管部門在非金融領域的規制權。
當然,美國、加拿大的BIT范本對于金融審慎例外的實體性規定也頗為籠統,其主要原因在于,國際法中“審慎”一詞和“例外”存在密切關系,與此不同,國內法中的“審慎”往往被視為金融監管的原則之一。審慎例外的敏感性使得各方在此問題的談判過程中分歧不小,因此持較為謹慎的態度。與之相類似,在規定金融審慎例外的判斷標準時,GATS金融服務附件第2條同樣存在著模糊性問題。對此,歐盟曾建議適用國際標準制定機構如巴塞爾委員會、國際證券業監管者組織和國際保險業監管者組織制定的國際標準對“審慎”一詞進行補充解釋,但因為WTO成員方對上述國際標準制定機構的代表性有所質疑,該建議并未獲得廣泛支持。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Special Session,Report of the Meeting Held on 3-6 December 2001,S/CSS/M/13,Feb. 26,2002.實際上,就各國規制金融業的法規和政策來看,其中多數都具有直接或間接的審慎考量,如果不進一步區分,審慎措施將等同于各國的金融法規和政策,從而導致推行金融服務領域的投資自由化努力淪為一紙空文。
由此可見,審慎原因的界定以及審慎措施的標準和范圍缺乏明確性,會導致其在適用中的困難。如果提交投資者—國家仲裁,很可能是承認了仲裁庭對這些模糊問題的解釋權。對此,美國國務院關于修改2004年BIT范本的一份報告曾經提出,針對第20.1條的金融審慎例外,應當加入類似于根本安全例外中采取的“自裁決”(self-judging)的措辭。例如,《美國—哥倫比亞自由貿易協定》第22.2條的腳注2就特別提出,當一成員方按照第10章“投資”或第21章“爭端解決”提出根本安全例外的仲裁程序時,仲裁庭或專家聽證程序應適用該項例外(即屬于“自裁決”的內容)。因為基于歷次金融危機的嚴重性,其是否危及國家生存只有當事國最為清楚,當事國應最有權根據自己的判斷采取其認為必要的措施,無論是發生金融危機或者為防范金融危機所采取的審慎措施都是如此,而置身事外的第三方的事后判斷無法取代當事國在當時的決策。自裁決條款一般取決于條款本身的措辭,締約方可以通過明確的條約措辭來體現某一條款具有自裁決性質,反映其真實的意圖,以影響仲裁庭的評判標準。(參見:韓秀麗. 雙邊投資協定中的自裁決條款研究——由森普拉能源公司撤銷案引發的思考[J].法商研究,2011(2):17-24.)
本文認為,雖然投資條約尚未將金融審慎例外設置為“自裁決條款”,但從美國金融危機后對投資條約的反思以及對國內金融市場利益加強保護的實踐來看,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因此,在我國簽訂國際投資條約時,如果能把金融審慎例外規定為“自裁決條款”,將有利于為自身保留更靈活的政策空間。當然,為了避免金融審慎例外的模糊性賦予仲裁庭過于寬泛的裁決權,有必要針對爭端解決作出特殊規定,從而確保締約國金融主管部門可以有效參與甚至主導此類爭端的解決。
2.資本匯兌與轉移例外
1996年12月,我國宣布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并開始了資本項目的開放。特別是在2001年加入WTO后,我國加快了資本項目改革的步伐,直接投資領域實現了基本開放,而證券投資領域則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重要時期[15]。此后,我國外匯管理局不斷推出取消和調整資本項目外匯業務審核權限及管理措施的通知,在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防范跨境資金異常流動風險的同時,穩妥有序地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轉移。由此可見,從長遠來看,中國將實現資本項目的自由匯兌與轉移,因此,有必要在投資條約中規定相應的資本匯兌與轉移例外條款。
另一方面,從我國的國際投資條約實踐來看,早期資本匯兌與轉移條款一般僅規定“在滿足其法律要求的條件下,各締約方應允許另一締約方的投資者以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實現款項的匯出,并且不應不合理地遲延”,2003年中國—德國BIT議定書第5條甚至前瞻性地提出,如果相關手續根據中國法律的規定不再被要求,BIT中“投資和收益的匯回條款”可以不受限制地適用。2004年5月,中國—烏干達BIT第7.4條首次規定了資本匯兌與轉移中的金融審慎例外,允許一旦發生嚴重的收支失衡或外部融資困難或存在這樣的威脅,締約任何一方可以暫時限制資本轉移,前提是該限制應被立即通知締約另一方,與IMF協定的條款相一致,限制在商定的期限內,并根據公平、非歧視和誠實信用原則而實施,此后,中國在部分BIT中陸續加入了類似規則。
但與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不同,我國投資條約中針對資本匯兌與轉移事項規定的金融審慎例外安排主要適用于嚴重國際收支失衡的情況。 例如,中國—加拿大BIT第12條、中國—西班牙 BIT議定書第6條等。對此,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予以完善:首先,中國—韓國BIT第6.4條增加了“在例外情況下,資本轉移引起特別是金融和匯率政策方面的宏觀經濟管理的嚴重困難或有上述困難之虞”,其范圍較之加拿大2004年BIT范本仍較為狹窄。因此,特別是在資本項目完全放開的初期,我國應將資本匯兌與轉移例外放寬到“為保護金融體系的安全、穩定、完整”,擴大其適用范圍。其次,在極少數BIT如中國—法國BIT第6條中,資本轉移限制措施實施的時間被限制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長于6個月”,這樣的約束雖然有利于保證投資者在金融危機發生時也能盡快轉移其資本,但對于東道國的政策制訂顯然十分不利。因此,我國未來簽訂的國際投資條約應盡量采用中國—韓國BIT的措辭,即“臨時的并在條件許可時被取消”。
(二)爭端解決
在爭端解決方式的選擇上,最有利于維護國家主權的方式當屬協商。在協商解決爭議的過程中,爭議雙方地位平等,方法靈活多樣。正因為如此,對于涉及國家主權核心的領域,爭議國家往往不愿采用法律的方式,而更傾向于協商。然而,相互協商程序只能要求相關國家的主管部門設法就爭議的解決達成協議,并不是必須達成,其結果容易因主管部門無法達成共識而使爭端得不到有效解決。因此,在目前的國際投資領域,通過仲裁解決爭端已經成為發展趨勢。雖然將涉及金融審慎例外的投資爭議置于國際仲裁之下,可能會導致外國投資者濫用訴權以挑戰東道國政府對金融市場的監管權,東道國政府基于審慎監管追求特定公共政策目標的能力有可能受到抑制,但在金融市場全球化、WTO明確了對金融服務進行規制的背景下,投資條約將金融審慎例外徹底擯除于仲裁解決之外,并不可行。
因此,中國—加拿大BIT針對金融審慎措施合法性的認定,采取了特殊的處理方式,即投資者與國家間的仲裁庭不享有裁決金融審慎措施合法性的管轄權:首先,仲裁庭應向締約雙方尋求關于此問題的書面報告。投資者—國家仲裁庭只有在收到此報告后方可繼續仲裁程序,或在設立國家間仲裁庭的情況下,只有在收到此國家間仲裁庭裁定后方可繼續仲裁程序。其次,如果爭端各方的金融服務主管部門未能在規定的期限(60天)內聯合作出共同決定,則任一締約方可在30天內將爭端提交給締約國間的仲裁庭解決。
由此可見,該程序的設計是調和傳統的金融服務爭議由東道國國內管轄與投資者尋求國際仲裁之間矛盾的產物,其試圖在解決金融審慎例外問題上實現尊重sXCJoTDyfXUKvbNU0t5R1Q==東道國對國內金融市場進行監管與維護跨國投資者權益之間適當平衡的目標,但仍然屬于相互協商程序的延伸。應該說,由于有后續國家間仲裁程序的壓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使締約國雙方主管部門積極主動地盡最大努力通過此前的相互協商程序達成解決問題的協議,以避免啟動后續的仲裁程序,從而提高雙方主管部門間相互協商程序的效率。即使雙方主管部門不能在前置性的相互協商程序階段經過談判解決爭議問題,通過后續的具有第三方爭端解決性質的國家間仲裁程序,也能夠使妨礙主管部門間達成協議的未決問題獲得仲裁裁決。
結論
國際投資條約歷來被認為是強有力的保護投資者的法律工具,然而,例外條款的存在表明,對投資者的保護不適用處于極端風險中的危機情況或其他特定情形。例外條款為締約方設置了一種免責機制,締約方可以在例外情況發生時采取必要措施來維護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而不承擔違反條約義務的責任,從而合理平衡投資者與東道國間的權益保護關系。由于晚近投資仲裁實踐暴露出的根本安全例外條款在抗辯外國投資者訴求方面的不足,金融審慎例外的出現具有其必然性和現實性,有利于通過肯定東道國的規制權來應對投資自由化帶來的風險。對于我國而言,金融審慎例外安排還有其特殊性:作為資本輸出國,我國需要關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一些國家以金融審慎為由實施的市場干預措施和救助措施,這些措施存在的投資保護主義傾向有可能導致金融審慎例外異化為投資壁壘;作為資本輸入國,我國則應盡可能通過金融審慎例外安排的合理設置,在國際投資規則談判中充分保護自身合法權益。ML
參考文獻:
[1]James Thuo Gathii. The Neoliberal Turn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J].Washington Law Review,2011,86(10):425.
[2]Asif H. Qureshi. A Necessity Paradigm of “Necessity”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J].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2010,( 41):121.
[3]William W. Burke-White. The Argentine Financial Crisis:State Liability under BITs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ICSID System[J].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2008,(3):213.
[4]余勁松. 國際投資條約仲裁中投資者與東道國權益保護平衡問題研究[J].中國法學,2011,(2):137.
[5]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Investment Regarding the Draft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EB/OL].[2012-10-14].http://www.ciel.org/Publications/BIT_Subcmte_Jan3004.pdf.
[6]Sarah Anderson. Comments on the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EB/OL].[2012-12-12].http://www.ips-dc.org/reports/the_new_us_model_bilateral_investment_treaty_a_public_interest_critique.
[7]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Regarding the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EB/OL].[2012-11-30].http://www.state.gov/e/eb/rls/othr/2009/131098.htm.
[8]Bretton Wood Project. ICSID-Institutions Index[EB/OL].[2012-12-12].http://www.brettonwoodsproject.org/item.shtml?x=537853.
[9]Stephan Wilske.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J].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2010,(2):84.
[10]陳安,谷婀娜. “南北矛盾視角”應當“摒棄”嗎?——聚焦“中—加2012BIT”[J].國際經濟法學刊,2012,19(4):98.
[11]Emergency Committee for American Trade. Proposed Model BIT Substantially Weakens Protections for U.S. Investors[EB/OL].[2012-12-12].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q=cache:-FaasTS7BLsJ:media.wix.com/ugd/b13337_910c663d.
[12]佚名. 富通投資巨虧,中國平安索賠三年無果欲尋國際仲裁[EB/OL].[2012-12-12].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2/0926/c70846-19112805.html.
[13]Fortis. Additional Measures[EB/OL].[2012-12-13].http://www.belgium.be/en/news/2008/news_fortis_paribas.jsp.
[14]Allen S. Weiner. Indirect Expropriations:the Need for a Taxonomy of Legitimate Regulatory Purposes[J].International Law Forum,2003,5(3):166-168.
[15]參見:國家外匯管理局. 資本項目外匯管理[EB/OL].[2013-01-03]. http://www.safe.gov.cn/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cbw/whglgl/node_cbw_gwhgl_store/ed132100481c06779263d284909d05cd?digest=BiVl_hMs1-5pvxPUIixuMQ.
An Analysis of the Financial Prudential Exception in the Investment Treaties
CHEN Xin
(Law School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
Abstract:As a result of the financial crises since the early 1990s, especially the ongoing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riginating from the US, it has become a broadening consensu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investment treaties to specify the financial regulatory right of the host countri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vestment under such treaties. In terms of provisions for such regulatory right, arrangements for financial prudential exceptions under the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have been held up as highly exemplary and have been adopted as reference for investment treaties of China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However, existing provisions or specifications of financial prudential exceptions are still in their infancy in terms of their applicability to the conclusion of treaties or dispute resolution and hence in need of improvement. In view of this, China should, on the basis of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design its own viable and proper arrangements for financial prudential exceptions in light of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China.
Key Words: investment treaties; financial prudential exceptions; dispute resolution
本文責任編輯:邵海2013年7月第35卷 第4期Modern Law ScienceJul., 2013Vol35 No.4國際法與比較法論壇文章編號:1001-2397(2013)04-014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