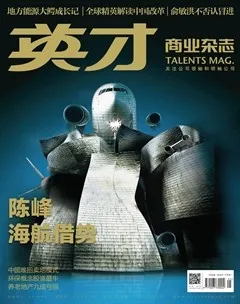銀行系投行兇猛

息差時代行將漸去,大如“恐龍”的銀行會一夜倒閉嗎?
大的好處其實也顯而易見,可以“跨界”,可以“無所不能”。就如同國泰君安董事長萬建華對《英才》記者喟嘆:“銀行都設了投行部,怎么不給券商一個商業銀行部做做?”
現在,即使在一個羸弱的市況,銀行的投行業務也會保持一副豐腴誘人的品相。從商業銀行對于投行業務的大張旗鼓,不難看出它的心思——投行業務已被視為一條重要的業務線和戰略盈利點來對待。
那么,這群來自銀行的投行家,除了讓諸如券商這樣的金融機構更加恐慌外,他們還會帶來些什么呢?銀行的投行部未來會以獨立姿態占據金融市場的一席,還是在銀行體系內繼續拱大?中國的金融混業又會復制西方金融的諸種悲劇嗎?
只是派生品?
銀行投行部可謂銀行體系內人均創造利潤最高的部門,“人均下來一年幾千萬沒問題”。曾在某國有大行投行部工作多年的汪杰告訴《英才》記者。
這并不夸張。記者不完全統計銀行業2012年報發現,四大行的投資銀行業務收入均在百億以上,其中以工行261.17億元為最。股份制銀行的這部分數字雖然沒讓人把眼睛瞪得更大一些,卻也紛紛把這項業務的牌匾擦得閃亮,掛上了各種閃亮的頭銜。
在具體的業務中,債務融資工具的承銷總額通常都在千億級別。“這也是業務中一個最大的利潤點,基本占到整個投行業務及附加中間業務收入來源的13左右。”汪杰對《英才》記者表示。
某種程度上,債務融資工具的承銷更像是被分割好的市場。
同樣是企業的直接融資,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可以通過在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注冊完成,而公司債和企業債卻是執行與IPO一樣的審批制,流程和時間更為繁瑣。
另外,二者的存量不可同日而語。據某債券分析師表示,我國短期融資和中期票據等融資工具的存量,大概在5萬億左右,遠遠大于公司債和企業債;而它們之間的規模差距甚至仍在擴大。銀行不能插手公司、企業債這件事就顯得沒那么重要了。
除了商業銀行能夠承銷短融、中票等外,這一領域多年以來僅有中金公司、中信證券兩家券商擁有聯席承銷商資格。今年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才又開放10家AA級券商的聯席主承銷商資格,而其他人只能在門口眼巴巴地看著。
因此,盡管蛋糕雖有份,卻未必能等分。
至于銀行投行業務中排名第二的利潤來源,既不是符合投行典型意義的銀團貸款,也不是大資管時代里最紅火的資產管理,而是財務顧問。
憑著與企業緊密的聯系,銀行可以為有上市融資的企業和券商搭橋牽線,靠為券商推薦項目獲取20%-30%的財務顧問費用。另外,并購貸款也會涉及到一些并購企業的資質評估,被歸在財務顧問范圍。
這還都是正常的部分。提供一些有含金量的信息、融資方案和建議,收取些許報酬也無可厚非。
不過,有一部分常年財務顧問、專項財務顧問業務的出發點壓根不在“提供智力附加值”上,往往與企業貸款綁定,強制攤派,強制服務,“象征性地給企業發一些市場信息而已。”
這部分相當富有中國特色的利潤被業內人稱為“吸血費”,最高時甚至可將貸款利率暗中提高30%。盡管讓銀監會頭疼,被市場詬病,它在投行業務的總收益中卻始終占比不少。

當然,相比之下,銀團貸款業務似乎更符合投行的本質。
“這個業務在國外非常活躍,大銀行只做牽頭方和承銷方,并不最終持有貸款,而是找一些其他中小型銀行接盤,把手中的額度轉讓出去賺差價。”汪杰認為,這才是未來投行業務發展的趨勢:“因為這是純粹的中間業務收入,并不在資產負債表里體現。”
反觀國內現狀,越過那筆稀薄的牽頭費,大家的目光仍主要聚集在后面的貸款上。牽頭行的認購份額最多,牽頭行、代理行們也往往選擇把貸款留在手中持有著。
總之,國內商業銀行的投行業務運作,與國外有著很大的差別。
固然有類似“國內銀團貸款的二級市場太青澀”這種原因,這個局面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國內各銀行對投行業務的理解。
所有略顯“非典型”的投行業務背后,不難感受到銀行通過其龐大體態散發出的強勢。在信貸還是國內主要融資方式的今天,銀行當然會投入大量精力和資源去置換息差,投行業務只是它的派生品。市場面對投行業務,需求雖然有,但尚未成為主流。
牌照不是鐵柵欄
盡管投行部很為銀行賺錢,羊毛也是出在羊身上。
“客戶資源往往來自各級分行的貢獻,它的完成也要靠公司金融、機構業務等部門方方面面的配合。”汪杰告訴《英才》記者。
畢竟,商業銀行的投行業務就是脫胎于公司金融業務的,其業務基礎也往往來自對公客戶資源:“很難想象一個對公業務做得很差的銀行,在投行業務方面會有亮點。”
和券商相比,與客戶更密切、更深入的聯系往往被視為是銀行投行業務的優勢。工商銀行副行長羅熹告訴《英才》記者:“投行一般是單筆單筆的交易,做完一筆可能就不再聯系;我們和客戶日常性的交易比較多,給客戶的服務種類也更多一些。”
不過,羅熹表示,畢竟還沒有取得境內的投行牌照,所以銀行所做的更多是進入市場前的服務工作。至于未來是否可能取得IPO牌照,他似乎也沒有抱太大期望,“要看資本市場的政策變化了”。
北京大學投資銀行與資本市場研究所副所長葛啟勝告訴《英才》記者,牌照無法成為投資銀行業務領域的門檻,決定金融機構是否能夠存活的只有它自身。“銀行在投資銀行方面的動作,絕不僅僅是一種挑戰,何嘗不是轉型的機會呢?”
畢竟,能被搶來搶去的業務,只說明大家誰都能做,而且做的差不多。于是乎,能拼關系的拼關系、能拼資源的拼資源。
金融機構們面對的,應是更廣闊層面上的交鋒。
然而無論是否混業經營,銀行都必須改變思路;更多的企業傾向于選擇直接融資的方式,傳統的信貸業務只會日益衰落。
261.17億元
根據各券商年報統計,2012 年 13 家上市券商共實現凈利潤 133.692 億元,僅相當于工行一家投行業務收入的一半。
“在利率市場化背景之下,中間業務風險低獲利高,其增長情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銀行的盈利水平。中間業務收入也將逐步成為影響銀行凈利潤的核心指標。因此,發展中間業務仍是商業銀行轉型的必經之路。”一位長期跟蹤銀行業指數的券商高級分析師指出。
什么時候,投行家才不會因為在中國的銀行工作而被同行貼上“不專業”或“中庸”的標簽,迎來職業生涯中最風光的時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