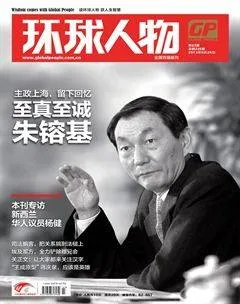電商大亨重塑《華盛頓郵報》


美國當地時間8月5日,《華盛頓郵報》董事會主席唐納德·格雷厄姆宣布,其家族已經同意將該報出售給電商巨頭亞馬遜公司的創始人貝索斯,價格為2.5億美元。這次收購結束了格雷厄姆家族 4 代人對《華盛頓郵報》的掌管,并對美國報業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讓外界好奇的是,一家是東海岸的百年老牌報業,一家是西海岸的 IT新貴精英,這兩條看似永不相交的平行線,怎么會產生了交集?
百年名報無奈易主
聲名赫赫的《華盛頓郵報》于1877 年由斯蒂爾森·哈欽斯創辦,1880年成為華盛頓特區首家日報。1946年由格雷厄姆家族接手,自此走上了繁榮發展的道路。該報的黃金時期在上世紀70年代。1971年,它刊登了記錄越戰情況的官方秘密報告,被稱為“五角大樓文件事件”;隨后又第一個揭露“水門事件”,迫使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辭職。這些獨家新聞的轟動效應,讓《華盛頓郵報》迅速建立起國際聲譽和威望。直到前不久,它還與英國《衛報》一同揭露了“棱鏡門”事件。
作為美國曾經最重要的政治類報紙之一,《華盛頓郵報》擁有800多名記者,其中不少堪稱一流的新聞人才。可惜面對新媒體的沖擊,它錯失了數字化改革的良機,報道內容上過度關注地方新聞,逐步失去了在國家和國際政治新聞報道方面的優勢。過去6年間,《華盛頓郵報》的運營收入下降了 44%;2012 年虧損 5370 萬美元,銷售額下降 7%。
格雷厄姆家族經營《華盛頓郵報》多年,對它有著深厚的感情,可是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也束手無策。為了讓報紙重獲生機,唐納德·格雷厄姆及其外甥女、負責出版事務的凱瑟琳·韋默斯開始為郵報尋找新東家。
他們今年3月聯系到了貝索斯,他一開始也表示頗有興趣。可是一度又沒有了消息。直到7月的一天,唐納德·格雷厄姆收到了一封來自貝索斯的電子郵件,說過去的幾個月自己一直在思考收購的事情。接下來,雙方在愛荷華州的太陽谷進行了兩次私人會晤,每次交談時間都將近3 小時。最終,這筆收購塵埃落定。
外界分析認為,貝索斯對郵報來說是個好買家。首先,他有強大的經濟實力。貝索斯的資產凈值高達252億美元,這次收購所花費的2.5億美元還不到他凈資產的1%。其次,貝索斯并不完全是新聞業的門外漢,他個人對新聞很感興趣,還曾經入股一家名為“商業內幕”的財經網站。據說亞馬遜的員工如果想給貝索斯提產品建議,先要寫一份新聞稿,他才愿意看。
IT精英打造電商帝國
1964年,貝索斯生于美國新墨西哥州。外界不知道他的生父是誰,4歲時,他的母親嫁給了米蓋爾·貝索斯,他便隨了繼父的姓。米蓋爾在上世紀60年代初從古巴移民到美國,曾擔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工程師。貝索斯在接受采訪時曾說:“繼父就像是我的生父一樣。只有填寫醫院表格時,我才會想起(他不是生父)這個問題。知道真相沒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為此感到尷尬。”
貝索斯的外祖父曾是一名研究火箭的科學家,退休后在得州經營著自己的大牧場。這里是貝索斯兒時的樂園。他學會了鋪設管道、修理風車。一次他通過操縱一個電子設備,把小表弟反鎖在房門內,讓家人哭笑不得。
1982年,貝索斯進入普林斯頓大學。當時他“陷入計算機不能自拔,正期待著某些革命性的突破”。由于預見到計算機將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他放棄了成為物理學家的夢想,轉而投向計算機行業。4年后,他以優異成績獲得電氣工程與計算機科學學士學位,并成為當年美國大學優秀生聯誼會會員。
畢業后的貝索斯并沒有馬上創業,而是先后在初創型科技公司、銀行信托公司和基金交易管理公司打拼了多年。直到1994年,貝索斯才在西雅圖郊區租來的車庫里,創辦了全美第一家專注于圖書網絡零售的公司,取名“亞馬遜”。他希望自己的公司能像那條著名的河流一樣奔騰不息。
網站上線僅3天,就被雅虎聯合創始人楊致遠盯上了。他寫信給貝索斯,提議把網站創意放進雅虎主頁推薦欄目。這一下讓亞馬遜聲名鵲起,訂單量飆升。為了讓亞馬遜在與傳統書店的競爭中站穩腳跟,貝索斯對網站界面進行了人性化改造,給客戶帶來了舒適的視覺效果和更加便捷的購書體驗。此外,低價是貝索斯真正的王牌。因為沒有中間商,亞馬遜銷售的圖書價格幾乎是當時最便宜的。再加上龐大的庫存量保證了豐富的品種,以及快捷的投遞服務,亞馬遜很快成長為圖書銷售行業的王者。
后來,貝索斯覺得亞馬遜的平臺和網絡可以銷售其他任何東西,于是音像制品、藥品、家庭用品都出現在亞馬遜的主頁上。同時,亞馬遜開始自主研發產品,電子書閱讀器Kindle就是最好的證明。自2007 年第一代 Kindle 誕生至今,這個產品系列不斷擴大,其平板電腦甚至可與 iPad 媲美。今天,亞馬遜是當之無愧的世界電商巨頭。其2012年銷售總額高達610億美元,是京東商城的 6 倍多。
變化必不可少,但需要試驗
很多人覺得,貝索斯涉足傳統報業意味著變革。正如《華盛頓郵報》前任編輯阿蘭·穆特所說:“貝索斯可以讓《華盛頓郵報》成為每一部Kindle上的默認應用軟件,這將賦予《華盛頓郵報》莫大的優勢。”
截至目前,貝索斯本人并沒有透露收購郵報后作何打算。在給郵報員工們的一封公開信中,他說:“變化必不可少,并且一定會發生。”可變化到底是什么?貝索斯似乎也沒有明確答案:“我們面前沒有一份地圖,指明一條前進的道路也并不容易。我們需要發明創造,這也意味著我們需要試驗。”
事實上,在這方面已經有人進行了 探索。去年3月,臉譜網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買下了雜志《新共和》,但他沒有對雜志內容做過多修補、改造,而是明確了紙媒和電子媒體的關系。在休斯看來,新聞的大部分內容應該電子化,讓讀者付費閱讀;而紙質內容的發展方向是更加精致、簡潔,并成為高端產品。在這個理念的引導下,《新共和》的讀者們開始在網上閱讀雜志文章,而紙質版的《新共和》則被更多讀者視為收藏品。
貝索斯或許會借鑒休斯的經驗,圍繞讀者的需要制作新聞內容,然后再以讀者喜歡的方式呈現出來。這對貝索斯來說并不太難。作為數字化產品的先鋒人物之一,貝索斯比報業的任何人都更懂得數字營銷與數字分析,他可以通過大數據優勢更深層地對用戶群進行追蹤分析,并預測消費者的準確需求,然后為其提供新聞資訊服務。
無論未來怎樣,貝索斯承諾將遵循媒體傳統,不計代價確保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對此他表現得十分真誠:“《華盛頓郵報》的價值觀不需要改變。這份報紙仍然是對讀者負責,而不是對擁有它的人的一己私利負責。”為了讓員工們對郵報的未來有信心,他還表示,自己不會參與《華盛頓郵報》的日常管理工作,郵報將繼續由熟知新聞業的原班人馬領導下去。
或許正如《時代周刊》網絡版評論的那樣,貝索斯和《華盛頓郵報》是一個不錯的結合。這不僅僅因為貝索斯可以給《華盛頓郵報》帶來技術上的飛躍,更是因為亞馬遜懂得如何讓人們專注地閱讀嚴肅媒體。與此同時,亞馬遜的全球化運營體系,也能幫助郵報在全世界范圍內進一步推廣。人們期待著,這份注入互聯網基因的傳統紙媒,將會獲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