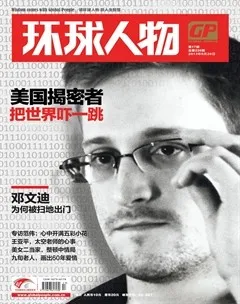陶然:“58%有網癮的孩子打過父母”


“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無法統一,人有時候就會逃避。在網絡游戲中,你只要輕輕一點鼠標,就會感覺到自己有強大的力量,所向披靡,但這一切都是虛空的。”陶然——北京軍區總醫院醫學成癮科、中國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主任,正在給50多個孩子上課。他們穿著迷彩上衣,只有十五六歲。“從前我學習很好,總是聽表揚,后來表揚的話少了,我受不了”……面對孩子們的各種發言,陶然都會說兩個字:“鼓掌”。
這是一個特殊的課堂,這些孩子們都曾沉迷網絡,無法自拔。在位于北京大興區的中國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他們正在迎來自己人生的另一次成長。
就是在這樣的課堂上,陶然總結出一套《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近日,這個標準被美國精神病協會(APA)納入第五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以下簡稱“手冊”),該手冊是許多國家在診斷精神疾病上的重要參考,中國人制定的標準首次在世界精神疾病診斷領域得到國際認可。新病種——網絡成癮疾病的確立,更為所有青少年科學戒除網癮提供了科學依據。
每個人446個指標
5月29日,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在北京軍區總醫院搜尋一番后,終于找到一棟掛著“網癮治療中心”牌子的簡易平房。約20平方米的辦公室中,靠北的墻邊放著一排桌子,上邊有電腦和腦電波檢測儀。陶然微笑著請記者就座。話題自然從網癮標準說起。“這次我們至少面臨14家國際競爭對手。之所以選用我們的,第一是我們的樣本量大,第二比較科學。”標準只有9句話,但它的形成,是一個歷時8年、從無到有的漫長過程。
2003年,在北京軍區總醫院醫學成癮科當大夫的陶然發現,來看病的人中不少人談及上癮的原因,總會說到兩個字——網絡,網絡聊天、網絡游戲等等。與煙癮、酒癮、毒癮等對某種物質上癮不同,網癮看不見、摸不著,在當時算新鮮事物。它是不是病,能不能治,怎么治……當時的陶然還拿不準,但有一點毋庸置疑,為此來就診的人越來越多。
經過兩年學習摸索,2005年,陶然團隊收治了200多個沉迷網絡的孩子。通過臨床實踐,他們慢慢發現這是一種病。“很多孩子玩網絡游戲不上學,這在生物學叫做社會功能受損,是一種疾病。最嚴重的是不上學,不工作,友誼、人際交往也沒有;還有就是給自己或他人帶來痛苦。”
一個孩子3年不出家門,頭發1米多長,爸爸用過很多辦法讓他離開電腦房,煙熏、連續餓他幾天……都不見成效;一個孩子因為媽媽不讓上網,居然剪掉了媽媽的耳朵;還有的孩子把家人肋骨砍斷……“有網癮的孩子當中,58%的人因為父母不讓上網,動手打過父母,我還遇見過10幾個穿尿不濕的。”
從2005年開始,陶然全面投入了網癮的研究。當時國內外有一些機構和個人也開始收治網癮患者。荷蘭成立了歐洲首家網癮診治所;在國內,電擊、中藥、軍事訓練……各種療法相繼問世。陶然則把工作的重點放到了臨床數據的統計上,這個工作量非常之大,但他認為,數據統計是一項研究工作的基礎,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確定診斷標準,進而制定治療方案。“每名患者都要統計446個臨床數據,包括說年齡、性別、血型、第幾胎等等。針對1200多個病人,我們用6臺電腦對這些數據統計分析了半年之久。”
網上得知自己的標準被采用
2008年,APA修訂第四版手冊,距上次修訂已有14年。陶然忐忑地提交了自己制定的網癮治療標準。說到當時承受的巨大壓力,陶然仍唏噓不已。當時手冊里沒有“非物質成癮”這一章,更沒網癮這個提法,能不能被接受,他心里完全沒底;另外,“我們得到醫院不小的支持,但也沒獲個獎啥的,不少人說我們整天瞎忽悠。”
當年11月,APA主席來到北京,考察陶然團隊試驗的可靠性,與患兒交談。此后幾年,陶然參加了15次APA大會,還去美國進行了兩次答辯。“面對著那些專家,我好像又回到了學生時代。”
2009年,陶然首次到美國參加APA大會。35名成癮界頂級專家就“網絡成癮是否為疾病”展開激辯。而陶然只能在門外等結果,因為他被告知“沒有參會資格”。“里面都是金發碧眼的外國人,沒有一個亞洲人。”結果,10票贊成,25票反對,陶然的研究最終沒有通過。但他沒想過放棄。“不管國際社會認不認可,我們還是得做自己的研究。沒現成的帽子也沒關系,我們就自己命名為‘網絡游戲成癮’,或叫‘網癮’。”
同年,世界成癮醫學界第二次投票,17票贊成,17票反對。這讓陶然看到了希望,“已經有很多人開始贊同我們的研究了。”2013年,APA第166屆年會上全票通過,“網癮”正式納入疾病范疇。
陶然說:“能制定標準,這個榮譽僅次于得諾貝爾獎。”記者和他開玩笑:“那有獎金嗎?”“哪有獎金啊!就是個榮譽。”對陶然而言,最實際的好處就是:APA送了他4本他們印發的手冊,每本定價160美元,他還可以以69美元一本的價格再買4本。
“大腦用則進,不用則廢”
怎么治網癮呢?陶然的答案是:心理治療、藥物治療和教育相結合。“前20天,我們主要解決的是孩子的情緒問題。心理學上有句話叫‘情緒不消除,理性出不來’。只有先消除了他的抑郁情緒,才能讓他冷靜下來,再根據自身情況進一步治療。有時候,我們讓他和室友交流,同齡人的話更容易聽進去。”
在成長基地,還有不少家長。“我們也要給家長上課,現在很多家長也不合格,總是在說教,而不是和孩子平等溝通。”在陶然看來,家長應該在規范孩子行為習慣方面嚴格要求,在培養興趣之類的事上民主,“但很多家長搞反了”。
陶然告訴記者,目前網癮出現向農村留守兒童、低齡兒童蔓延的現象,而且非常嚴重。有一次,陶然回山東老家,發現他的母校居然關閉了。一問才知道,不少學生沉迷于網游,不好好上課,最終學校辦不下去了,而一個有幾百臺電腦的網吧里從早到晚熱火朝天。
“我親戚家也有個七八歲的孩子,玩手機、玩游戲,比很多大人還靈光。這種情況不在少數,這是在為我們中心培養孩子呀。”說到這,陶然無奈地苦笑著。“大腦用則進,不用則廢。玩游戲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大腦只要興奮一個區就夠用了,如果一個孩子長期沉迷于網絡,會導致大腦的社會功能喪失。一句話,他的社會化的大腦就被廢了。”
2012年中國青少年網絡協會網癮調研報告顯示,城市青少年網民中,12.7%有網癮傾向,人數約為1858萬;網癮青少年約占14.1%,人數約為2404萬。北京公安部門也曾統計,青少年犯罪中76%的人都有網癮。雖然陶然不是在救死扶傷,但他的治療可以使一個個對社會沒有價值甚至有害的少年改邪歸正,這比救死扶傷更有價值。